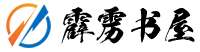马尼拉的风带有烹制肉品的香气与烧焦塑料的灼味,昼夜吹卷不息。它卷过由屋棚堆成的山峦、吹得那些用帆布和编织袋扎出的先祖或神灵们猎猎作响。传闻在这些层层交叠的方块状居所下埋藏着一座旧时代的道宫,像是被藤壶彻底掩盖的礁石——至于这隐秘的真假,大多数吕宋的市民并没有太多兴趣探究。他们只是在棚屋和街道中穿行,一如蚁巢中的群蚁。
这座人工山城不存在高耸的楼宇或大厦,只有胎海连锁的阴池与母河高悬于空,两相对立、在白昼或黑夜中取代日月,释放着本应由它们照耀的暖光。
此刻子时已到,正值母河大亮、唤醒了那些仅有权生存在午夜的市民;蒙在绿蒙蒙浑浊夜色中的马尼拉则延续着白天时的内容:或工作,或进食,或诛人满门。
而蜷缩在角落中的女孩,刚刚恍然惊觉——自己正经历着马尼拉日常的最后一项。
她周围散落着被切下的手脚,来自于正躺倒于地、抽搐不已的亲人们:父亲、母亲与弟弟。他们上个月才刚刚迁居到同一具躯干上,其乐融融。
肩膊上并列生长的三颗脑袋,加上被斩落肢体、而显得光秃的躯壳,倒像是刚刚被修剪过的植物。
迁居手术带来的顽强生体机能使得这“植物”还有力气用各自的后脑或下巴撑住地面,左右扭动。可由于头部设置的太过对称,脑袋的动静再大也只能在原地挣扎、并不能逃到哪里去。
作为家中待嫁的长姊,原本下个月也该动上手术、和亲人们相依相伴;此时却仅能和壁上高挂的慈悲妈祖像,一同注视着棚屋中发生的惨剧:而凯萨赛妈祖只是带着永不更改的祥和笑容、高声重复着家庭作坊应当遵循的工作守则。
“啊——”
刚刚还在用西语和汉语咆哮咒骂的父亲在惨叫中沉默下去,陷入呛咳、喘息里。一位身穿蓝白条纹衣裳的男人从属于父亲的脑袋旁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手里提着钝刀与刚割下的舌头——这个男人,便是一切的凶手。
女孩撑住地面,往后缩了缩双腿、避开快要漫到脚边的血洼。这是她唯一一双还没烂开的好鞋。
母亲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只能从喉咙里挤出嗬嗬的呜咽、被黑红色糊满的五官看不出神情。
弟弟的头颅朝向与父母相反,脸朝着地面、因此口鼻淹进血水:他在片刻前便不再动弹了。原本父母总说要为弟弟看好后背,此时却成了他最早离开人世的原因之一。
女孩动了动因保持微张而有些发酸的嘴,终究不知该做出什么回应。泪水混着鼻涕从嘴角滑进口腔,既苦又咸。
在血水被踩动的扑哧声中,提着钝刀的男人贴近到她的身旁。男人的眼白布满血丝,像是从未睡过一次好觉,眉形却是纤长且弯起的半圆、如同正在嬉笑而挑起,乱蓬蓬的发丝则盖在额前;还有身上穿着蓝白相间的条纹衣裤——这是女孩今夜之前从未见过的款式。
她出神地望着男人胸前歪斜挂着的胸牌。飞溅的血迹盖住了部分文字:
“……医科大……附属第一……是什么?”
女孩努力地想着这从未见过的词语组合,但有限的知识让她难以认出这来自于旧时代的机构。
这份思索并没有持续多久。
男人倒转过钝刀,递到女孩的眼前。他咧起嘴,除了双眼外满脸都展示着和煦的笑容:
“你不是说想好好活下去吗?嗯?来啊。”
这呼唤沙哑且温和,汉语口音要比吕宋本地人来得纯正。
女孩望着钝刀上的锈痕与齿缺,咽下流入口里的涕泪和血滴,终究还是伸出了手。
跟想象中不同,钝刀握在手中十分轻盈:于是她在茫然中,竟多了一丝惊喜。
……
“……!”
雪鬼从噩梦中惊醒,本能地检查了颈下枕着的长剑;接着握紧胸前的“凯萨赛妈祖”像,长出了一口气:自从更换过没有汗腺的人工皮肤,也就不用担心梦醒后的冷汗会沾湿衣物了。她撑起身子,跪倒在业已干涸的下水道中、将妈祖像贴住满布接合纹路的前额:
“万福林默娘,满被圣宠者!大慈大悲,志节至贞;圣德祥云光普照,母性奥旨唤人醒……”
《天上圣母真经》诵念完毕后,她以一声“阿门”作为祷告的结尾,将妈祖像小心翼翼地吞入嘴里、咽进食道外侧的储存袋。数十余年过去了,童年时的幽影依旧会在每次入眠时找上自己,像是长在灵魂表面的牛皮癣。
她默默跪坐,等待汹涌的思潮与痉挛的胃部回归平静,便继续向着管道系统的更深处走去。
用祷告驱散梦魇带来的惊骇后,该做正事了。
今日是雪鬼在马尼拉追踪天使的第十七天,终于将它的踪迹锁定在废弃的排水系统中。无论这次追猎成功与否,她都要回返山门、向掌座老祖报告。
原本未曾遵行过“一人法”的雪鬼,就是吕宋群岛上的异类;也习惯了隐藏在那些无人问津的角落:要如何在马尼拉找到这样的地方,是一门学问。
马尼拉弯曲盘绕的下水道犹如魔鬼的肚肠,但也是雪鬼从小成长的地方。她穿过那些决意自灭而走进地下的鳏寡孤独留下的枯骨,避开胎海连锁正巡逻中的保育员,沿着天使留下的痕迹向深处迈进:
离群的天使都会分泌踪迹信息素,以此来作为道标、指引他们的羔羊;而雪鬼的猎物此时离家万里之遥,信息素的强烈程度已经到了连异信者的副嗅球都能感知到的地步。
雪鬼能感到三位一体的费洛蒙如火炬般闪耀,远比前几天更加显眼——这说明天使对信仰的坚定、或称狂信,竟忽然跨越了一个层次。
“发生了什么?”
她忽地停下脚步——因为问题的答案,或许就在眼前了。前方的弯角、下水道中一处封死的凹槽里,充盈着信息素的光焰;连雪鬼的副嗅球也隐隐作痛起来。
雪鬼继续向前,脚下没有一丝声响——这十余日的追猎,要比预想中来得轻松。她并不感到意外:这自然来自妈祖的福佑,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妈祖的安排。
她于静寂中转进凹槽:天使背对着她,跪在下水道粗糙肮脏的地面上,一动不动。
那是个有着干瘪羽翼的家伙,一边翅膀上的羽毛已蜕尽,没有第二性征、看不出性别;不着衣物的身躯上满是褶皱和老人斑、四只手臂蜷在胸前;光秃秃的头顶周围长着稀疏的白发。
雪鬼静立半晌,才在静默中走近:她可以确定,天使已经死去了。若是平时的她,还要割下目标的首级才会靠近;但此时更重要的、则是天使忽然死去的缘由。
那是未曾为受洗而欢呼、也不曾拥有圣痕的天使,因此还保持着类人形的外貌——
当然,是相对而言。
人脸上生着鸟类的长喙,无力地垂在胸前。它跪倒着、蜷缩着身子,一双手十指交叠、握紧,放在嘴边,摆出祈祷的姿态;另一双手臂却笔直地指向前方。金白相间的泪痕从天使的三对眼睛中漫出,一直延伸到脖颈。
虽然这是雪鬼第一次亲眼目睹“羽人”、也就是掌座老祖口中“天使”的真容;但这具尸骸上的异状显然与过往听闻相差甚远:
在左侧半身、以及羽毛蜕尽的那边翅膀上,此时鼓冒起张张面容,盖满躯干和肢体;其中有些突起得更加高些、带着稀疏的淡金毛发,能让人分辨得出这是尚未成型的头颅。
每张脸孔的神情都略有不同,大多眼睑微闭、显得宁静安详,剩下的也有狰狞痛苦和迷茫呆滞混合其中。只是它们都有着一般无二的五官:清丽中带着英气,明显不是天使自身的外貌。
除此之外,天使的尸身上并无其他显眼的外伤了。
雪鬼从未见过如此怪异的景象:这是某种新近流入吕宋的神通吗?
她蹲下身,把利剑拄在身侧,顺着天使淌着蜜色鲜血的食指所指的方向望去;视觉模式的切换间、幽深昏暗的下水道在她眼中点亮——
于存在的最后时刻,天使似乎放弃了躲藏与逃亡、转而在下水道的角落搭建起了一座粗糙且细小的礼拜堂。
下水道的混凝土成了画布,天使将自己由奶和蜜构成的鲜血作为颜料、绘满了整幅墙面;居中的则是它用利爪刻出的浮雕、栩栩如生:
那是颗孤零零的人头、摆放在一具无色的棺材上。模糊不清的五官中,只能分辨出几几咧开到耳根的巨大口部。天使垂落的头颅正对着浮雕——看来,这便是它死前所礼拜的对象。
围绕着人首浮雕,则是整个涂鸦中唯一的文字、是在吕宋也并不常见的英文:“The Seventh Messiah。”
“第七弥赛亚?”
雪鬼思索着这个称谓,却一无所得。但她认出了浮雕所刻画的形象——短短月间,关于棺上之首的传闻早就浸透了马尼拉。
她站起身,用眼中内置的相机反复拍摄着眼前的一幕,喃喃低语出人头在吕宋更广为人知的名姓:
“九子鬼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