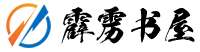没多久,第二场仗就在西北打了起来。
勃律领军迎击,上战场的除却狼师,还有东越兵马及苏俞率领的部分昌王军。他们与穆格勒正面在往西不到十里外处交战,每封注着战况的军报隔一天一夜才会传回来一次。
令人焦心。
祁牧安和余老将军退居后方驻守营地,日日似是都能感觉到有亡灵源源不断飘过苍茫的上空,夹着血腥气一起弥漫着西北和营地。
祁牧安昨夜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耳畔仿佛始终能听见遥远方兵戈相向的厮杀声,闭上眼睛都是勃律身披兵甲倒在血泊中的场景。
他浑身冷汗涔涔,一梦如回到了三年前。在榻上躺了小半夜后终于无心继续睡下去,于是便小心起身,披着衣衫走出帐外。
外面夜空灰蒙,透不出一丝月色光亮,如一整块绸布压盖在众人头顶,闷着人喘不过气。
祁牧安扶着帐帘站在帐口处,瞧着闷沉的夜色只觉前胸膛上的箭伤在隐隐作痛,似是有预感般一阵一阵的鼓着他难安乱跳的心。
自打上次见到勃律,还是多日前。勃律那些日子一直住在狼师内,他们二人分开几月还没顾得上过多的诉说情意,这仗就突如其来地打响了,勃律便出兵直至今日。
祁牧安独自站了一会儿,突觉身旁有人,转头看去,不知段筠何时站在了他的身边。
他默了两息,在寂静的军营中轻声问段筠:“小余夫人有传回消息吗?”
“还没有。”段筠答。
祁牧安点点头,若有所思地垂下头。钟云晗领了一支小队从西南悄悄出发,与正面迎敌的勃律对其敌军左右夹缝。前方战报连连,这位女将却迟迟未朝后方传来消息,难免让人担忧。
“余老将军如何说?”祁牧安问。
段筠如实回答:“余老将军已经在议事帐内坐了两天了,未曾对此事开过口。”
祁牧安再次垂头,重重吐出一口气,说:“我知道了。”
长夜漫漫,空中的硝烟味儿久留不散。勃律站在燃着火光的树下,皱着眉挥手朝天上使劲挥了挥,像是想驱散这股子难闻的味道。
挥了会儿,勃律便放下手不再动,盯着远处的一抹光亮,突然开口问:“几时了?”
他身旁跟着一个少年一直算着时辰,此时听到勃律的声音,嘴唇动了动,吐出一句话:“殿下,已经寅时了。”
勃律点头,抱臂回首看了眼少年,吩咐下去:“乌力吉那仁,让人去给符燚传消息,告诉他小王要行动了。”
名叫乌力吉那仁的少年正是之前扬言要跟随勃律殿下一辈子在狼师征战的少年,此刻他已然穿上了沉重的兵甲配上了上好的佩刀,站在勃律身边气宇轩昂,眸中亮着意气风扬的光,对远处即将到来的危险和刀刃毫不畏惧。
他就像是草原上被燎火烧尽后从一片焦土中顽强新生的嫩草,从他身上勃律总能瞧见自己昔日的影子。
乌力吉那仁郑重应下殿下的话,转身就要去寻人传信,却在抬脚的时候被勃律重新唤住。
他回头看着勃律,不解:“殿下,还有何吩咐?”
勃律瞅着他愣了愣,随后闭上嘴,似是咽下了什么,一息后再张开,对少年沉声嘱咐道:“一会儿跟在我身边,一切小心。”
乌力吉那仁先是跟着一愣,随后反应过来,笑着对勃律重重点头:“是,殿下。”
“去吧。”勃律冲少年扬起下巴示意他赶紧去传达命令,看着乌力吉那仁快步跑远的背影,勃律盯着黑暗许久,才把头缓缓扭回来。
他右手搭在腰间悬挂着的佩刀刀柄上,两指顺着刀柄的弧度无意识的缓慢摩挲。他的佩刀刀鞘上还溅着方才被斩杀的敌方哨兵早已干涸的血迹,刀鞘内的刀刃若是抽出来,定能瞧见已经长年累月印在上面一片盖过一片的血浪红光。
勃律又在原处站了须臾,等了几息,在乌力吉那仁回来的前一瞬,似有预感般动了脚跟。他踹灭燃了一晚上的火苗,一步步往战马的方向走,边走边单手晃动着略微僵硬的手腕。
他此次出兵的这些时日一直居于最后方未出手,始终在观察敌情,了解现今对面的兵力到底是如何的一个状态。他让符燚他们一路边追边打,将穆格勒和大庆的兵马赶到了牙沟后,便下令分散兵马,造成无力追赶兵马人散的假象,而他则趁机带着一众将士快速来到牙沟外围,欲要借此机会趁敌军放松警惕,等待蓄力一击,首当其冲一举攻入牙沟。
勃律刚在马上坐稳,乌力吉那仁便回来跑到马下,向他俯身汇报:“殿下,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勃律颔首,随即勒紧马绳,目视前方,昂首高声大喝:“出发!”
他一声令下,所领的这一队人马闻风而动,齐齐勒马向着牙沟冲去。他们的战马飞驰在黑暗中的沙土之上,荡起的不只是碎石尘埃,还有埋没在泥土之下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无数亡魂,和人人征伐诛敌的心切。
不远处的牙沟,赵长辉率领的大庆兵马正坐在地上休憩。他们被追赶了一天一夜,早就已经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幸得身后那些穷追不舍的人没了力气追不动了,不然他们难免又是一场耗力的苦战。
若是不给将士充沛的调整时间,迟早有一时他们会败在耗尽的体力上。
方才他们争论过接下来的对策,追赶他们的军队已经无力前行,派出去的哨兵回报,说有许多兵马已经四散,要做回营的打算。
于是他们决定,于明早修整过后,化被动为主动,追咬对方残剩的兵力,尽量将他们困在沙地上。
赵长辉坐在石头上垂首闭眸养了养精神,继而睁开眼张望了一圈自己卒下已然没了力气东倒西歪的士兵,哼了一声。他眯眼偏头看向不远处躲在阴暗里的人,突然面露凶相,脸上横肉挤皱,咬牙切齿。
——这群该死的草原人!跑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快,竟让他的兵垫尾,为此折损了不少人。
赵长辉坐了会儿,盯着暗处的一名穆格勒的将领许久,才起身大步沉沉地走过去。
走近了,借着地上燃起的火光会发现,这人正是原本应该坐于后方营地中看着沙盘谋算的延枭。
谁也想不到此次延枭亲自拔刀上了战场,他被兵马绕于军队中央,一直以来都未暴露在对方兵马的注视下,藏匿了真正领将的身份。本想着借此机会亲自打击敌军阵营他找了好几日的破绽,好好打对方个片甲不留,却没料到他被那些人追着退了好几里地。
此次对面就像是背后换了个人一样,作战手法变了个花样,不像之前那些中原人,又不像草原,让他一时半会儿摸不透,不敢贸然入阵。
延枭气的握在身侧的拳头都在轻微颤抖。
赵长辉站住脚跟,瞧着延枭在那里又是跺脚又是张着嘴臭骂,叽里呱啦说了一堆草原话他一个都听不懂,但明眼的都知道他在发脾气,而且是大发雷霆。
“缩头乌龟。”赵长辉对延枭一直被兵马护于中心的做法实在鄙夷不屑,冲着人小声骂了一句,继而才抬起脚继续朝他那方走。
延枭身边的人缩在旁边一动不动,惊恐地听头上的可汗指着他们大骂,但男子越骂越气,瞪着一双红眼,狰狞着面孔扫视一圈他们,突然抽出身后跟随的吉达手上毕恭毕敬一直双手捧上的佩刀,作势就要向他们这群人砍去。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越离越近,变相的制止了延枭的动作。
“你要杀人?”
延枭停下刀子,怒不可遏地飞快扭头,盯着赵长辉走过来。
赵长辉站在他们一众人几步远外,讥笑着说:“杀得好,把你的人杀完了你在把自己捅死,这样我就不用和一个蠢货在这儿坐等天明。”
延枭怒视赵长辉,抬高声音:“小王现在和你们皇帝的地位相当,你们太子都要低三下四地求我,你就这般同我讲话?”
“哼。”赵长辉轻笑一声,语气里分明带着轻蔑,延枭只一个耳朵就听懂了。
“如今小王一声令下,你的脑袋就会分家,像挂在你们皇宫里巴特尔的头颅一样挂在我穆格勒的营地中。”延枭冷笑,“你要不要试试?”
赵长辉嘴角的笑渐渐变成怒容:“你真以为这次太子殿下是在求你?就你这样的,连给殿下提鞋都不配,宫中的太监都比你强!”
这话刚撂下,还不待延枭怒气冲到手上挥刀真的向赵长辉的脖子砍去,忽然自不远处狂奔来一个哨兵,边跑嘴上边喊着:“不好了!”
赵长辉不耐烦地偏头,大声斥骂:“嚷嚷什么!”
“将军,攻过来了,攻过来了!”来的哨兵急忙在他面前刹住脚跟,指着一个方位惊慌失措,语无伦次。
“谁攻过来了?”赵长辉蹙眉。
“是挂着狼师旗子的军队!”
赵长辉的脸色当即难看至极:“有多少人!”
“少说也有一万。”
延枭听到后在旁边嘲笑他:“才区区一万,就让你怕成这样?”
然而他这番话音落下,从右手方又跑来一个哨兵,嘴上也是喊着:“攻过来了!攻过来了!”
赵长辉转头对这姗姗来迟的哨兵劈头盖脸地嚷:“军队不是从东南来的吗!何时又变成西南了!”
“西南也有,将军,西南也有!”哨兵扑通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西南有什么?”
“狼师啊,将军,西南是狼师!足足有两万!”
“西南的是狼师,那为何东南也是狼师?难不成他们劈成了两半会飞不成!”赵长辉刷的把目光钻到提前一步跑来的哨兵身上,目光刁钻,盯得人浑身直哆嗦。
“将军,东南方分明挂着狼师的旗帜啊!”
“将军,西南也是狼师的旗帜!”
前方的赵长辉正急得辩不得真假,后方的延枭反倒蓦然沉了瞳色,沉思下来。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男人,男人是曾经舒利可汗手下的兵,如今跟随延枭行军作战。
他将这些话尽听耳中,略一思索后睁大眼瞳,迟疑几番上前半步来到延枭手侧,附耳道:“可汗,这手法像极了三殿下……”
“什么三殿下!穆格勒何时来的三殿下!”延枭扬音斥声打断他的话,说完又飞快扭回了头。
他此时心里鼓鼓剧烈的跳动,是惧怕,是不甘,是愤怒。他不敢承认,在听到这句话后,他仍然对勃律这个名字有着不小的悚意。
——这个人绝对不会出现在这里。
延枭深吸一口气,手一挥而下,叫人继续去探实情,又叫一人去探路,从何方撤军最为保险。
“你要逃?”赵长辉转身看他,“你要一直逃到哪里?”
“注意你的措辞,小王不是逃。”延枭不再和赵长辉理论,转身合上刀子,吩咐人抓紧收拾东西上马。
就在他们纷纷动身准备迎敌的时候,不知从哪出传来一阵杂乱的马蹄声,惊扰了营地中的所有人。
“是谁在乱马!”延枭伸长脖子高喊,却无一人回答,反而这马蹄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仿佛快要骑到他身边一样。
延枭狠狠皱眉,刚要再次重新问一遍的时候,突然从他的正前方诸多人身后的黑暗中,由极远的方向从高空直直射下一只羽箭,竟是从他的头顶飞过,一箭插入他身后走过的一名小兵的身上。
延枭一愣,就在这一瞬的功夫,他们暂时驻扎的营地便惊声纷扰了起来,马蹄声缭乱,伴随着刀子斩入皮肉的撕裂声,他面前的无数人一个接一个溅出滚烫的血液。
——是谁?
延枭连连后退,睁大眼睛瞪着对面不知为何悄无声息贴近他们、又是从何处现身的马背上的人。然而这越看,他越心惊。
闯入的人他有些很面熟,有些早年草草或许见过一面,而还有一个人,在这些兵马的最后方冲入、与他对上直线的人,却是他一辈子怀恨在心永生难忘的人。
他看到了本不该出现在这西北战场上的身影。
——不,是本不该再出现在这世上的身影。
延枭呼吸急促,耳畔尽是来不及抵抗就被砍杀的人,瞬间鼻下就充斥了浓重的血腥味,熏着他的整个人的神经都在颤跳。
“勃律……竟是勃律!”
他低吼一声,从新抽出吉达捧着的佩刀,不顾任何人的阻拦,在一片混乱和瞬间成血海的牙沟里,随手抢过一匹马跨上去,直冲勃律的那张脸直冲。
他在看见勃律的一瞬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便是杀了那个人,杀他第二次!这次让他永生永世都埋入黄土里永远翻不了身!
勃律率兵冲进来后本没看见延枭,也不知是不是兄弟之间真的存在牵绊的原因,竟让他鬼使神差地往那方扫了一眼,而就这一眼,就让他看到了几年不见的延枭的面孔。
他顿时迷住眼睛,果不其然,下刻延枭就策马朝他奔了过来。
勃律面不改色,坐于马上并未多做思考,便果断冲着延枭笔直而冲。二人都是奔着对方的脖子而去,手上的刀均泛着银光,在黑夜下灼着人的眼睛。
两人的刀子于马背上相撞又很快分开。延枭拽着马绳后退了一步,看着勃律执刀的手眼神飘忽不定,若有所思。
他分明听说哈尔巴拉把勃律搞废了,就算现在人还活着,那也不应该能有力的挡下他这一招。
难不成哈尔巴拉当时心软了?
延枭皱起面孔,恶狠狠凝着对面人。正当他审视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勃律的时候,对面的男子忽地开了口。
“没想到,我运气这么好。追了你们这么久,竟把你活生生的追了出来。”
“看来你一直都跟在军中,只是不敢露面罢了。”
勃律打量着延枭的穿着打扮,低嘲:“延枭,瞧瞧你,你现在就算挂上了可汗令,穿的人模人样,到底是一只早就被父汗放弃的丧家犬。”
延枭猛然攥紧马绳,传进耳中的是让他万分熟悉的嗓音。
——面前这个男人当真是勃律,是一个完好无损的勃律。
——哈尔巴拉是怎么回事!
延枭觉得自己被骗了,被人骗了三年,更加气愤。他手上的刀不断颤抖,可他看不见整个牙沟都是刀光剑影,他的眼中现下只有对面的男人。
若是他现在抬起头往左右看去,会发现牙沟上空一箭接着一箭在射出带着火光的哨箭,随着箭支撕破长夜,便再会有大批人马从四面八方涌进,包裹着他们,将他们困于牙沟内,翻不了身的会是他们。
延枭再次挥刀与勃律打了起来:“整个穆格勒就数你最肮脏!不过是大漠的贱姬所出,父汗对你只是假面重任慈爱,实则你最该是那个丧家犬!”
他用力抵住勃律的招式,刀子在他手中灵活转了一个圈,将对方的刀柄硬碰硬地怼开。
“不过这种人,我替你杀了他,你不应该感谢我吗!”
打了十个来回,勃律的额头渐渐浮现汗珠,有些略微吃力了起来。他的手肘沉寂了三年,重新运用却感到了几丝陌生僵硬,挥武的招式速度也下降了许多。
他只能凭借昔日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惯性竭尽全力去接下延枭的招式,但并不是长久之法。于是勃律忽地勾起嘴角笑了一声,破天荒地乐意接从延枭那张嘴里喊出来的臭话。
“父汗对我到底如何,还轮不到你一个从始至终都不曾被重用过的废物评头论足。”勃律一个腾空从马背上起身,一掌拍开延枭的手臂,刀子堪堪划着对方的发丝跃过,险些就将延枭的耳朵挥下来。
延枭急忙反手,扯着马绳避开勃律的刀尖。
勃律在对面仍旧一句句讥他:“不论父汗揣着什么心思,利用我也好真的受宠我也好,好歹父汗还重用过我,认可过我,而你呢?你却一直如老鼠一般缩在穆格勒的犄角旮旯里,连吱都不敢吱一声!”
“勃律!你也就是长得好,跟那个歌姬一样下贱,去一趟乌兰巴尔,哈尔巴拉就这么多年都对你念念不忘,父汗为了攻下乌兰巴尔,把什么都愿意交到你这个筹码手上!”
这次,换延枭的刀贴着勃律的手臂擦过,带出一抹血珠。
勃律吃痛,面上却眼睛都不眨一下,心中怒火直烧,冲上了头顶,正打在他激起的兴头上。
可延枭的眸中却渐渐亮起得意亢奋的光芒,他这时竟能从勃律的刀子上察出无数破绽,这若是放在年少是绝对不曾出现过的。
看来哈尔巴拉做的一番功夫并没有白白浪费。
他找到了勃律弱点,就像是拿捏住命脉一样,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起来。
“勃律,你的手是怎么了?怎么颤成这样?难不成真的废了?”
勃律狠狠稳住手的动作,不让手腕跟随刀子相碰后遗留下来的震晃一起颤抖。他深深喘气,忽地积蓄起力量,刀朝着延枭扫去的时候带着强劲的风声,好似一股风就能将对面人斩于无形之下。
他低吼:“延枭,你这辈子弑兄弑父,天下丧尽天良的事儿全被你做了,剩下的话,你留着去地下和父汗说吧!”
延枭大惊,未料到勃律还有未释放的力量,这股刀力比方才要沉上无数倍,他的刀子撞在勃律的刀刃上,竟是反向让他震得手麻了一瞬间。
他眼睁睁瞅着重新积蓄了爆发力的刀子飞快转到他的鼻子下眼睛下,他却只能惊险狼狈地从刀下拽回一条命。他气急败坏怒视着勃律,何曾想此人的刀力明显不及以往甚至深算下来还不及他,可他就是如论如何何时何地都无法从勃律刀下讨到好处。
年少时是,三年前是,如今更是。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正当延枭乱了心神的时刻,勃律的刀子已经稳稳地朝着他的面门扫来。延枭来不及后撤,马上就要镶入勃律的刀中时,突然从身侧被人扔来一个浑身是血的身影,用身体挡在了他的面前,也挡住了勃律的招式。
人影痛呼哀嚎,惨叫一声后断了气。
“可汗快走!”吉达不知从哪冒了出来,方才的人就是他扔来替延枭挡刀招的。他从马上重重拽了下延枭,替他拍了马,让马快速奔了起来,二人一前一后飞快冲出了刀光漫天的牙沟。
“吉达!为什么要跑!”回过神后,延枭坐在马上怒吼身旁马背上的人。
“可汗,来日方长,这次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吉达示意延枭看看四周,又回头看了看在后面已经甩了刀上的血水步步紧追的勃律。
吉达看着死而复生的勃律皱起眉,随后不再多想,马驾得快了些,马不停蹄地要护送延枭逃出牙沟,逃回属于他们的领地上。
勃律在后快马加鞭,没两步就追上了落后一截的吉达。他攥紧马绳,身子在马上略微倾斜,手上的刀子猛然往左一挥,直取对方的命脉。
然而谁知吉达的身手十分敏捷,与平日里跟在延枭身边畏畏缩缩的模样全然不同。他翻身躲开勃律的刀尖,还来得及腾出一只手推上勃律的手臂,愣是将人生生震于马下。
勃律大为吃惊,手脱了缰,从马上腾空跃到了地上。他勉强稳住身形,再抬头看去时,那马上的二人已经奔出了五六步远了。
一直听命跟在勃律身边替他挡下背后刀子的乌力吉那仁快马赶来,嘴上担忧呼喊:“殿下!”
“拿弓箭!”勃律死死盯住延枭逃跑的背影,把佩刀利落插回刀鞘内,右手高高抬起,声音刚刚扬下,乌力吉那仁便把他马侧勃律的弓箭取下递给了他。
勃律拿到弓箭后并没有急着拉弓,而是突然身形向上一跃,踩着乌力吉那仁身下的马腾空飞起,在半空中搭箭拉弓一气呵成,臂力张开把弓拉到极限,瞄准远处两道背影其中的一道,蓦然放开了手,使两只箭羽快速从弓弦上飞出!
正在策马狂奔的吉达闻声听的身后传来呼啸声,不用看都知道是什么东西。他急忙大喊:“可汗趴下!”说着,他往前加速了几步,用手拦住延枭的后背,硬是把人摁在了马背上。
两只箭贴着延枭的背脊飞出扎在前方的草地上,并没有射穿男人的胸膛。
男人一愣,随机大声狂笑,边笑边扭头朝后望。勃律仍旧站在地上,只是此时一动不动,目光如利刃般从远处直射过来。
“哈哈哈!天注定你杀不了我,勃律,你杀不了我!”
延枭大笑的声音自远处传来:“哈尔巴拉听到你还活着的消息,一定很高兴!他会高兴到发疯,高兴到立刻来找你!”
“等着吧勃律,你快活不了几日!”
勃律站在原地喘着粗气,耳边回荡着延枭逃跑直至消失掉身影前说的最后一句话,闭了闭眼,骂了自己一句无能没用。
他五指死死攥在掌心,指甲深陷在皮肉中。他鼻腔间环绕的不知是手掌上的血痕,还是战场上厮杀过后留下的血腥气,总之格外腥气。
天开始蒙亮,微弱的晨光直射在这片流着血和残缺不堪的大地上,照耀出地上诸多散横的尸体。
大庆的兵马在前一刻呼喊:“撤!快撤!”
“快撤军!”
等乌力吉那仁替勃律找回跑远的战马时,牙沟上已经没有大庆或是穆格勒活着的兵马了,留下的都是拼杀过后要埋于沙土下的亡魂。
“让赵长辉给跑了。”符燚挠着头,懊恼地走到勃律身边,汇报着情况。他们在勃律传来命令的时候便赶了过来,听到牙沟内勃律的人放出的哨箭,才一齐涌入牙沟,打的敌军措手不及。
勃律深吸一口气平复胸腔内的热火,睁开眼睛四周看了看,看到小余夫人钟云晗正皱着脸给自己草率地包扎伤口。
他一顿,问:“往哪跑了?”
符燚指了一个方向。
勃律点点头,视线从钟云晗身上挪回来,看着身边男人命令道:“符燚,你们回去,我带人去追。”
“什么?”符燚不同意,“勃律,我去追吧!”
“赶紧带她回去。”勃律坐上马背前朝钟云晗的方向扬扬下巴,“赵长辉跑不远,我带人去追就行。”
符燚拗不过勃律,几句下来只好勉强点头应下,就眼睁睁看着勃律带着从狼师里分出的一部分精锐朝着赵长辉跑走的西南方向没了踪影。
符燚在原地叹了好几口气,嫌弃地瞧着四周尸横遍野的牙沟,走到钟云晗面前,说:“殿下让我们先回去。”
钟云晗支着枪斜着眼睛瞅她一眼。她的人是绕了最远的路线,在前几里地与勃律的兵马左右夹缝才把敌军逼到牙沟,没想到除却勃律王子率领的兵马,最先进入牙沟的竟是她和手下的人。
钟云晗瞬间看不起符燚了,嗤笑一声,理也不理他,将手臂上被砍伤的部位胡乱扎好后,起身拎着枪头也不回话也不说的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