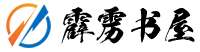外面夜色仍旧浓重,屋中只点亮了一台小烛,微弱的映在纸窗上跃动。瑞炉升起袅袅香烟,在静谧的屋中宛转。
祁牧安已经穿戴整齐,坐在榻边无声端详着勃律的睡颜,呼吸极低极低,生怕把榻上好不容易睡下的人吵醒。
他不知坐了多久,又或许并没有坐多久。他挪开目光,看了看天色,外面仍旧瞧不见熹微。
他折回头,替勃律掖了掖被角,便要起身。
可榻上的人不知是被惊醒了还是并没有睡沉,勃律在他离身的那一刻深吸一口气,随之微眯着眼睛睁开一条缝,朦胧中瞧见榻边晃动的人影。
祁牧安见状坐了回去。
勃律神思浑噩,喉咙喑哑,嘴唇开开合合了半天,才嗓音带着将醒的沙哑,气声唤了句“阿隼”。
“我在。”祁牧安的声音放的很轻很轻,在勃律听来就犹如黑夜中沉眠的白檀:“天色还早,你且继续睡。”
勃律的呼吸渐渐悠长,再次沉沉睡了过去。
祁牧安又坐了会儿,起身走出屋子。悄无声息地合上门,他看向早已在外等候多时的纪峥。
“将军,马已经备好了。”纪峥小声道,“苏俞那边传来消息,营中也已整装妥当,随时都能出发。”
祁牧安点头,再三嘱咐他:“我不在的这期间,你守好他。”
“是,将军。”纪峥拱手一礼,看着祁牧安走出院子。
马已经等在了府外,可祁牧安却并没有急于上马出发,而是拽过马绳,一个人牵着马先来到了神医住处的院外。
隔着窄小的院门,里面静悄悄的,瞧不见一丝烛光,像是人早已熟睡。
祁牧安悄无人声地在神医门外站了小半个时辰,晨曦初露,大门依旧紧闭。眼看着快到时候了,他缓缓叹口气,朝木门施施行礼,转身上马离开。
勃律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身边的榻已经凉透了。
阿隼走了。
他坐在榻上恍惚了许久,才重聚意识,堪堪下了榻。
院中阳光透过青天暖洋洋的洒在地上存留的雪面上,晶莹的棉雪堆积在树下,时不时飞来一两只鸟埋在雪地里啄啊啄。
勃律披着外衫站在门口,呆楞了许久,就这样跨出了门,来到院中的石桌旁坐下。
他半阖眼睛,微微扬起头,任凭阳光惬意地落在他的身上。
这一刻,他竟是从无知无觉中感受到了一丝暖意。
纪峥端着一盘果子从长廊的一头走来,脚步极轻,似是害怕打扰到屋中人的休憩。然而等他抬眼见到屋门大敞,里头的人披着单薄的衣衫就这样坐在雪地中露在冬日下,登时吓得赶忙跑过来,再也顾不上什么步调。
他着急忙慌地来到勃律身边,催促道:“公子,快些进屋,外面冷。”
勃律收回晾在石桌面上的手,淡道:“我想在外面坐坐,烦你帮我把手炉和氅衣取来吧。”
这府上就没人拗的过这位主子,就连他家将军在的时候也时常对此没办法,更别说他了。纪峥愁眉苦脸地劝了好几声眼前的青年都不为所动,只好把果子放在桌子上后,转身去为他取加了厚毛的衣裳。
回来的时候,后面跟了两个小丫鬟,毕恭毕敬地端了一壶茶水,举了一个冒着热气的雕花炉,过来后一声不吭地都摆在离勃律近的地方,之后退到三四步远外站定。
勃律瞥了这俩丫头一眼,一个比一个头垂得低。他抬帘看向纪峥,点着那俩婢女道:“让她们下去。”
纪峥回首瞅一眼,这回死活不同意,好歹这身份尊贵的公子身边得留人捧在手里好生照顾。
勃律不耐烦地啧了声,深吸一口气懒得和他吵,索性扭回头自顾自地赏自己的雪景。谁知这男人把东西取来后也不走了,直板地挺在他身侧,叫勃律如何都忽略不了他的存在。
勃律头才撇了还没过三息,就又扭回来,没好气地质问纪峥:“你没事做吗?”
“啊?”纪峥先是一愣,而后挠挠头恍然大悟,上前帮他把果子摆好,又替他斟了杯热茶。
勃律眉毛一抖,满脸不满,看他跟看傻子似的。
“你为何还站在这?”
纪峥倒茶的手不停,眼睛扫了这青年一眼,很快又回神落回杯盏上。
“将军吩咐我要照顾好公子。”他直起身子离开勃律,手贴在身子两侧搓了搓,拘谨地后退了一步。
勃律舌头抵着腮帮,过了会儿转了话题,问:“你家主子什么时候走的?”
“将军天未亮就走了。”纪峥声音压低了几分,“公子,虽然没有限制您的行动,但近日您最好不要出府。过了这几天,您要是想上街走走,就来唤我。”
“为何?”勃律尝了口果子。
纪峥挠挠头:“这是将军的意思。”
勃律眼睛一转,瞟眼院外:“常衡已经站在外面了?”
纪峥又是一声“啊”,反应过来明白勃律说的是哪件事后,道:“常将军应该今日午时带人来。”
勃律差点噎着:“午时?他难不成还要在我们这吃个饭?”
纪峥支吾半天,看这位半个主子的态度,像是不欢迎常将军,但人家要是想进来蹭个桌,他也不好意思把人赶出去。
怎料勃律脸一垮,原本就冷的脸更冷了。
他交代纪峥:“他要是敢进来,你们就放狗咬他。”
纪峥咧咧嘴,兢兢业业道:“公子,府里没有狗。”
“那就去抓一只回来。”勃律瞪着他,“抓一只大的,回来看门,看见常衡就让它逮着常衡的腿咬。”
纪峥为难,他跟在祁牧安身边这么久,还从来没遇到被交代去做这种事。
“怎么?还不去?”勃律的视线从纪峥的身上慢腾腾移到后面婢女的身上,而后又慢腾腾移回来。
纪峥一个头两个大,转身忙招呼着两个小婢女,压声道:“快去市上,给公子买只狗回来。”
两个丫鬟面面相觑,最后提着裙子迈出院子买狗去了。
等人走了,身后一下子空荡了许多。没人再看着他,勃律一身轻松,裹着厚毛裘对纪峥怪道:“你家主子出征,你怎么没跟着?”
纪峥笑的殷勤:“我要留在府里保护公子啊。”
勃律狐疑地看着他。
纪峥“嘿嘿”再笑,笑过自己都觉得尴尬,道出事实:“其实……真正的昌王军六里面几乎都是跟随王爷征战下来的,严格来说是王爷的亲兵,只是王爷不在了,才随着转到将军的手里,而我们府里的几个从头到尾都是属于将军的人。”
“况且……”一个大男人抓了抓衣角又松开,“说来我不完全算亲兵里的人,苏俞在军中替将军行事,我就贴身跟在将军身边处理些琐事。当年是将军看纪家就剩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了,才让我跟在他身边。”
“你弟弟?”勃律诧异:“你弟弟如今身在何处?”
“在大庆。”纪峥道。
勃律蹙眉:“你在这,你弟弟却在大庆?”
纪峥再笑:“在那边有位熟人相照料,总比跟着我到处跑的强。”
勃律咀嚼的动作慢下来,沉默半响后问他:“你就不想他吗?”
纪峥回神,睁着眼睛点点头:“想啊,当然想了……等仗打完,我就能跟着将军回去见他了。”
勃律无声看了他会儿,叫纪峥被瞧得一头雾水。等他觉得浑身不自在想开口问缘由的时候,青年就把目光飘走了,静静坐在桌边忽地出声:
“会的,过不了多久你一定能回去见他。”
纪峥糊里糊涂地点头,还没等他再次开口,有人快速跑来,打断了二人之间接下去的对话。
来人是府上传消息的小厮,到了地儿给二位俯身行了礼,道:“公子,十一殿下回来了。”
话音将落,一道小身影出现在院口处,瞧见石桌边的身影,突然没憋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边哭还边朝勃律这方向走。
勃律无奈,将人上下打量了一遍发现好端端的,这才问他:“为何一见到我就哭鼻子?”
“我……我……”元澈哭的稀里哗啦,抽的一个完整的字都蹦不出来。
“行了行了。”勃律被他看着哭的大喘口气,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已经死了。
青年脑子稍稍一转就知道这小子为什么哭,他往元澈混着泪的嘴里塞了个果子,堵上嚎啕大哭的哭腔。
“我没怨你,你不用愧疚,更不用自责。我对自己的身子有数,那点程度我死不了。”
“你骗人。”元澈指着他含糊不清道,“我师父说了,你就是心里没数,还非要逞能,才天天把自己作成这样,要不是你命大你早就死了。”
勃律额角气的一跳:“我那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这个没良心的?”
元澈哭的更大声了。
“我既然说出口,答应你了,那就一定会做到。”勃律捂住耳朵,“再说了,现在快死的人是我,你哭什么哭。”
“你真的要死了?”元澈眨巴着还泡着泪的眼睛,听到这句话哭声停了一息,紧接着长音跟奚琴拉鸣似的,哭声更响了。
“你真的要死了啊,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师父怎么办啊!”
少年这哭声把旁边院子厢房里前夜喝酒睡到日上三竿的符燚都吵醒了,惺忪着眼睛打开屋门往外张望。
勃律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实在是受不了他定在自己身前哭嚎,连连对一旁不知所措的纪峥招手:“快给他拉走!关屋里别让他出来!”
纪峥听言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元澈从原地拔起来扛回屋,这才让勃律耳根子清静。
元澈这一嗓子,让勃律三天避着没敢见他。然而三日后,他却在榻上等来了意想不到的一人。
胤承帝在常衡的陪同下迈入祁府大门,纪峥往里通传了不下四声,才见到窝在榻椅上,半梦半醒的人。
听见声响,勃律睁开眸子,甩开手里的话本,打了个哈欠。
“看来勃律王子这几日过的很顺心。”元胤居高临下道。
勃律没答话,目光半阖着在这两人之间来回转,最后想起什么,落在常衡的腿上,似是在看他有没有被狗咬。
府上的人利索,那日他才吩咐下去,就从外抱回来一只狗,听说是在市上花了几枚铜板买回来的。
勃律一直以为这种大街上逮一只就行了,谁曾想还需要花银子。但既然买都买了,他就勉为其难叫人抱来看看,这狗威不威风,骇人不骇人。
待府上下人抱了一只奶声奶气的小狗过来,勃律沉默了数刻,一人一狗大眼瞪小眼。
买都买了,银子都花了,总不能扔了不管吧?小狗也是狗,他随即大手一挥,让人在离大门近的地方圈了片地,开始放养。
他的目光从常衡的腿上收回来,心里把纪峥和其他人全骂了一遍。
元胤以为勃律是顾忌有常衡在不好开口,思索之下觉得有理,便叫人退了出去。
屋中只剩下二人。元胤坐在对面的椅子上,自己给自己动手倒了杯茶,润润嗓子。
勃律怪看他,率先打破双方间的安静:“祁牧安可到西北了?”
“还在路上。”元胤道,“西北偏远,还需用些时间。”
勃律舔了下唇,还是没等来元胤开口,不耐烦地主动再道:“你今日来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些?”他皱起眉,“你一个皇帝,屈尊来我这,应该不止说这些吧。”
元胤放下杯盏,冷不丁出声:“已经打起来了。”
勃律眼皮一颤。
元胤续道:“对面领兵的是你们穆格勒部的可汗。”
勃律掀起眼皮,望向他。
元胤看着青年,问:“这仗,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勃律不屑嗤道,“打一个没脑子的,你还问我怎么看?你们的兵不会连一个废物都打不过吧。”
“看来你这几年当真是对战事一点都没了解。”元胤肃起面孔,与勃律年纪相仿的他看上去却更加老练。
“你们可汗的打仗手法和排兵布阵,上一次让我们吃了一亏。”元胤往后靠住椅背,“不过那次我们还是赢了,但损失很大。”
“他不是我可汗。”勃律向前俯了俯身,冷眼视他,一个字一个字强调。
元胤闭上嘴,两手外摊,头微微一颔,算是道歉。
“那是因为你们之前从来没对上他,不清楚他的能力有多大,更不了解他的头脑,这才觉得他难缠,况且你们不清楚他背后支招的都是些什么人。”勃律冷道,“他是狐假虎威,背后最主要的还是哈尔巴拉。若单他一人,在我眼里屁都不是。”
青年回靠,嘶口气,疑道:“我同你们打了那么多长仗,你们竟然处理个延枭就这么费劲?那么些年的仗白练你们了。”
元胤没气,只沉声拎出了自己的话:“所以这才是朕今日找你的目的。”
勃律的眉头拧的更狠,一股不妙的感觉涌上心头。他谨慎道:“你到底要说什么?”
元胤目不斜视地盯着他:“你知道你在跑马场废的人是谁吗?”
勃律先一怔,扯动僵硬的嘴角,偏头冷笑:“我管他是谁。”
“是凉阳王的世子,是凉阳王唯一的儿子,以后会承袭凉阳王爵位的人。”元胤越说声线越冷,“凉阳王于我朝有大功,他在朝堂上有无数拥护者,地位堪比容太傅。凉阳世子从小跟随凉阳王习武,踌躇满志,前程似锦,然而你却把他的手废了,废的还是右手!”
“你那一刀下去,他以后就再也拿不起剑了!你这是断了他的官路!”
“那不是还有左手?”勃律漠视,“再不济,你们朝廷不还有文官?”
“凉阳王是武官,行的是行军打仗的路,你让他儿子走文官?那是要让凉阳王的爵位断送于此!”
“没嘴的小兔崽子。”勃律先嘀咕一句,后不屑一顾:“那你应该感谢我没直接杀了他,让你的朝廷将来少了一个逆臣。”
“你到底清不清楚现在的情形!”元胤噌的站了起来,来到勃律的面前:“现在满朝文武都知道朕的上京庇护了一个草原人,还是与东越为敌的穆格勒王子!”
“他们一个个都要你死!撞柱子都撞到朕的早朝上了!”
“凉阳王在朕的殿外闹了有一月有余,讨着要朕给个说法,这事儿都闹到几个太妃的耳中了!”
“要不是朕拦着,祁牧安挡着,你以为你还能安生地坐在这里?”
“你早就被凉阳王拉去给他儿子偿手了!”
勃律的怒火也腾的升了上来。他怒视元胤:“他那样羞辱我,只废了一只手不为过!”
元胤猛然屏息,慢慢吁出来,揣摩着到时候了,他再次开口,提出条件——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一,和朕合作,征伐大庆,以此来让朝中闭嘴,让你在东越来去自由。”
“二,朕会看在祁牧安的面子上,留你一命,但你这辈子都不能离开东越,朕会让人严加监视你。”
勃律沉着脸。
元胤本以为他开口会拒绝,又或者跟他再提别的条件,谁知青年一句话把他一时问懵了。
勃律缓道:“你让祁牧安给你卖命多少年?”
元胤沉思良久勃律话中的意思,却没忖量出他到底是何意。
于是他如实道:“十年。”
勃律听后沉默很久,低声言语。:“我活不到那时候……我连能不能活着等他回来都不知道。”
这话不知是对他自己说的,还是在对元胤说
趁着元胤没反应过来,怔愣的时候,勃律抬头平静道:“劳你费心一直打我狼师的主意。”
“你让人看押我吧,现在杀了我你得不偿失,他会把你东越拱手让给草原亦或是大庆,让你们所有人都捞不到一丁点好处。”
“于此,还不如让我自己死,这样过不了多久你就能拿我首级给你那些大臣交差了,安置好我后他也能继续为你所用。”
元胤心中吃惊。他脸色变了又变,没想到他话都说到这份上,勃律竟还能无动于衷,一丁点为天下安宁结盟的想法都没有。
难道他手上真的没有任何价值了吗?曾经辉煌的狼师,真的连一兵一卒也没有了吗?
元胤坐回椅子上,思量之后深吸一口气:“你知道他是为了什么才和朕做的交易吗?”
“因为我……”勃律垂首小声先念了一句,接下来音量大了几分,像是说给元胤听的:“是因为我。”
元胤一气之下再次起身:“你既然知道他自始至终都仅仅是因为你才背叛大庆来找朕,为何不争取给他一点希望?”
元胤激动到胸膛起伏:“在朕看来,你不是个自私自利之人。你对中原的战况不在乎,那你草原的子民呢?若大庆或是其他人争得这天下,你敢说你的子民一定能获得太平盛世?”
勃律冷声打断:“皇帝,不要把自己吹的天花乱坠。我一个随时都能躺进棺材的人,要如何相信你东越就是那个正确的选择?”
元胤冷哼:“是也不是,朕知道你心里清楚的很。”
勃律默言。
元胤再度问:“你当真要弃之不顾?祁牧安呢?你就不担心你死了,他给你殉葬?”
“他不会。”勃律说,“三年前他没有,三年后就更不会。”
“他属于我,更属于天下。他割舍不了你们的黎民百姓,割舍不了海晏河清的清平世界。”
“他割舍不了的太多,而我除了他,早已孑然一身,踽踽独行,了无牵挂。”
“天下和百姓对他,更为重要——这是他自小骨子里的道理,是他的命。”
“而我好像阻了他走下去的道路,我心疼他不该如此。”
勃律看看已然鸦雀无声的元胤,说:“我珍惜这偷来的几年岁月同他相逢。但天命如此,同天抗争,只是最后无用的挣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