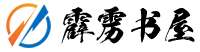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艺术、科学离你而去,似乎为了幸福,你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的时候野人说,“你还失去了什么?”
“当然,还有宗教,”元首回答说,“过去——我是说九年战争之前,存在一种叫上帝的东西,但我早已经忘记了,我猜你对上帝无所不知吧。”
“这个……”野人犹豫了,他倒很想说说孤独、夜晚、月光下静卧的白色台地、悬崖、几乎朝着黑暗中阴影那一跃,以及死亡。他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语塞了,甚至连莎士比亚都救不了他了。
而元首此时穿过房间,走到书架旁,在一堵墙上打开一个保险柜。看着沉重的门缓缓打开,又见领袖在暗黑的柜子里摸索。“这里有个东西,”他说,“曾经让我极感兴趣。”只见他拿出一本砖头一样厚的黑皮装订的书。“恐怕你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
野人接过来一看。“《圣经·新旧约全书》。”他大声地读着书名页。
“这本恐怕也没有见过?”
野人一看,是一本小书,封皮都掉了。
“《师主篇》[1]。”
“或者这本?”元首又递过来一本书。
“《宗教经验之种种》,作者威廉·詹姆斯[2]。”
“我还有更多,”穆斯塔法·蒙德继续说道,又坐回了自己的椅子。“我的情色旧书收藏的可是全套,上帝躲在保险柜里,主福特则蹲在架子上。”他指着自己那个所谓的图书馆,笑着说,书架上都是书、阅读器梭芯和录音胶卷。
“如果你知道上帝,为什么不告诉众人?”野人愠怒地问道,“为什么你不把这些有关上帝的书籍给大家看?”
“原因和我们不开放《奥赛罗》给人民看是一样的:它们都太旧了,里面谈及的上帝乃是数百年前的上帝,不是我们现在的上帝。”
“可是上帝是永恒不变的呀!”
“但人在变化。”
“那又有什么不同?”
“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都没有,”穆斯塔法·蒙德说,他站起来,又一次走到保险柜前。“过去有一个人,号称枢机主教纽曼[3],是一个红衣主教,”他补充说明道,“很像是现在的社群首席歌唱家。”
“我在莎士比亚的书里读到过红衣主教这个词,‘我,潘多夫,来自可爱的米兰,一个响当当的红衣主教。’[4]”
“不错,你肯定读过。刚才,我说过有一个人叫红衣主教纽曼,这里是他的书。”他抽出一本书来,“既然谈到纽曼的书了,这本书也拿出来吧。作者是一个叫曼恩·德·比朗[5]的哲学家,如果你知道哲学家是什么意思的话。”
“哲学家是一类人,此辈梦想,包囊天堂与尘世。”野人冒冒失失地说。
“说得不错。我给你读一段这个哲学家某次梦到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们再听听这位过去时代的社群首席歌唱家说过些什么。”元首打开夹着纸条的那一页书,开始读起来:
吾辈不再是吾辈自己,因吾辈所占有的物质更多地主宰了吾辈。吾辈已不能建构自我,也已不能超越自我。吾辈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因吾辈实乃上帝的财富。从此角度考虑,难道不给予吾辈幸福?一旦思及吾辈非自我之主人,难道不心生幸福之感、愉悦之感?或许春风得意之辈会作此想:拥有一切便是至大,如他们所假想,他们甚至是完全独立,不靠他人得到此等成就;此辈亦会想,眼不见则心不烦,也无需考虑那琐碎的感恩、祈祷,或老是提及受人之命所做的事。然而,时间流逝,他们一如众人,终将发现,独立实非世人所能成就——独立本是超越之境,或许他们所谓的“独立”能起一时作用,却终于不能导人安全抵达终点……
穆斯塔法·蒙德停下来,放下第一本书,拿起另一本书,翻着书页。“我们就读读这一段。”他说,于是,他那深沉的嗓音又开始响起来:
人将老朽,他便感到自身彻底虚弱无力、萎靡不振、身体不适,此等现象,必然伴随年老而来。因此之故,他幻想自身所患不过小病,自欺欺人以抵抗恐惧,便生此想:此等窘境,其来有因,既然疾病可治,他也能从衰老中恢复。此辈实在妄想!衰老实乃疾病,实乃可怕之恶疾。有此种说法:人渐衰老,便生出对于死亡之恐惧,以及对于死后之害怕,故此转而信教。但鄙人之经验,却可下此结论:吾辈年纪渐长,信教之心自然萌发,绝非源自彼等所谓恐惧、幻象,实源自激情淡化,心性渐定,胡思乱想、多愁善感不再那般令人激动,吾辈理性运转更加妥当,也更少受假相、欲望、分心之物遮蔽——过去吾辈倒是容易被它们诱入歧途,如此一来,上帝显灵,譬如拨云见日;吾辈灵魂乃能感知、看见,并膜拜此万光之源。此等转变,信为自然,且属必然。只因既然给予感官世界以鲜活与魅力之物已然离吾等而去,既然吾辈身心内外之印象均不再支持那现象之存在,则吾辈自然要依赖某物,可寄托,亦不欺瞒吾辈。此物非它,实在是真正之现实,乃一完全、永恒之真理。如其所是,吾辈必然转而信仰上帝,因这信仰情感,品质纯粹,感知此信仰之灵魂充满愉悦,吾辈所失去,由此信仰,尽皆弥补。
穆斯塔法·蒙德合上书页,靠着椅子坐下,说道:“哲学家梦想天堂与尘世,有万万千千的事物,而有一个是他们梦想不到的,”他摇了摇自己的手,“那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的世界。只有破除对上帝的依赖,你才能青春不老、繁荣昌盛。‘独立终于不能导人安全抵达终点,’不过,我们依赖青春不老、繁荣昌盛,却终于将世人一直带到终点。结果是什么?毫无疑问,结果就是我们独立于上帝了。‘吾辈所失去,由此信仰,尽皆弥补。’可是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或需要弥补的,宗教情感纯属多余。当青春的欲望都能实现,难道还需要去寻找替代品?当我们能享受自古以来所有的游玩把戏,难道还需要寻找其他分心之物?当我们身心始终因运动而快活,难道还需要什么静养休息?当我们拥有了索玛,难道还需要别的安慰?当社会已然秩序井然,难道还需要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
“那么你是说并没有上帝?”
“不,我倒是以为很有可能有这么一位上帝。”
“那么为什么?……”
穆斯塔法·蒙德止住了野人。“可是上帝向世人显灵,针对不同人,便会有不同的方式。在旧时代,他的显灵就像这些书里所描述的那样。而现在……”
“他现在怎么显灵的?”野人问。
“他现在显灵,是作为一个缺席者,似乎他根本不存在。”
“这都是你的错。”
“应该说这是文明的错。上帝与机器、科学医疗、普遍幸福是无法相容的。你必须做出选择。而我们的社会选择了机器、医疗、幸福。因此,我不得不把这些书锁在保险柜里,它们是些污言秽语,人们看了会震惊的……”
野人打断了他。“可是,感觉到上帝的存在,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吗?”
“你也可以问问,裤子装上拉链是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元首嘲讽地说道,“你这么一说,倒是让我想起了过去一个叫布拉德利[6]的人,他这么定义哲学,说哲学是为人类依据本能而信仰的事物寻找糟糕的解释,似乎人是因为本能才产生信仰!其实人是因为经过驯化才对事物产生信仰。哲学,我看倒是应该这么定义:因为某些糟糕的理由信仰某物,于是用另一些理由来为其开脱。需知,人们信仰上帝,也是因为被驯化的结果。”
“即使如此,”野人固执地说道,“当你孤独、非常孤独的时候,在黑夜里,或当你想到死亡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去信仰上帝,……”
“可是现在人们再也不会孤独了,”穆斯塔法·蒙德说,“我们已经驯化他们,使所有人都憎恨孤独,而且经过安排,他们的人生中绝没有可能碰到孤独。”
野人阴郁地点点头。在玛尔普村,他曾经很痛苦,因为他把自己与村子里的集体活动隔离开了,而在文明的伦敦,他也感到痛苦,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躲开那些集体活动,所以从来不会真正的孤独。
“还记得《李尔王》中那段台词吗?”野人说,“‘神灵们乃是公正,他们以我等风流浪荡所酿苦果,痛惩我等。如此,出生于暗黑淫亵之地的你,结果是以你生父的眼睛作为代价。’对此,埃德蒙回答说——你应该记得,这时他已经受伤,命不久矣——‘你所言不错,确实如此。大道循环如车轮,已经一圈,我活该自作自受。’[7]这段台词如何?这不是说明存在一个上帝,他掌控万物、惩戒众生、回馈善人吗?”
“是吗?果真如此吗?”轮到元首发问,“与一个自由马丁,你可以大干各种各样的淫亵风流的勾当,可绝不会担心你的眼睛会被你儿子的情妇挖出来。‘大道循环如车轮,已经一圈,我活该自作自受。’可是时至今日,埃德蒙会在哪里?他会坐在一把充气椅子上,搂着某个姑娘的腰肢,大嚼性激素口香糖,看着感官电影。神灵确实公正,这点毫无疑问,不过到最后逼不得已,他们的律法之密码还是由人间的统治者来宣读,所以也可以说,上帝也是在接受人的指令。”
“你真这么想?”野人问道,“你真的以为埃德蒙坐在充气椅子上,就不是在受严厉的惩罚?这种惩罚与他受伤流血至死的惩罚,难道不是一样严厉?神灵确实公正,他们难道不是以埃德蒙风流浪荡所酿的苦果来羞辱他吗?”
“从什么境地羞辱他?作为一个快乐、勤奋、消费商品的公民,他是完美无缺的。当然,如果你采用你的标准,或者你会说他被羞辱了。但在这里,我们还是坚持同一套标准吧,你总不能用离心球比赛的规则来玩电磁高尔夫的游戏吧?”
“可是价值并不取决于个人喜好,”野人说,“它既取决于人之判断,也取决于其自身宝贵与否。[8]”
“少来了,少来了,”穆斯塔法·蒙德反驳道,“你扯得也太远了,对吗?”
“如果你容许自己想到上帝,你是不会让你自己因风流淫亵的勾当而沉沦的,相反,你会有理由耐心地容忍万物,充满勇气地处理事情。在印第安人中,我就看到了这一点。”
“我肯定你确实看过,”穆斯塔法·蒙德说,“可是这里的人并不是印第安人啊,在这里,一个文明人没有任何必要去忍受那些极其扫兴的事物。至于‘做事情’嘛,我主福特早就禁止人们头脑里有这个概念了。如果人们各行其是,大做事情,这个社会的秩序就会被颠覆。”
“那么自我克制又怎么说?如果你有一个上帝可以信仰,你不就有理由自我克制了吗?”
“但是工业文明的前提是,人们不会自我克制。医药和经济的发达要求人的放纵达到社会可以容忍的顶点,否则,社会的车轮将会停止旋转。”
“你总得为贞节保留一个理由吧!”野人说,当他说这话的时候,脸都有点红了。
“可是贞节意味着激情,意味着神经衰弱;而激情和神经衰弱则意味着不稳定;不稳定又意味着文明的结束。为了持久的文明,必须要让民众充分享受风流快活。”
“可是上帝是所有高贵、美好、英雄的事物存在的理由啊,如果你信仰上帝……”
“我亲爱的小老弟,”穆斯塔法·蒙德说,“文明世界是根本不需要什么高贵品质和英雄主义的。只有当政治缺乏效能的时代,这些东西才存在,而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组织良善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人有机会显示出高贵和英雄主义。当我们的社会驯化工作完全不顺畅时,这些东西倒会冒出来。比如,战争发生的时候、党派纷争的时候、抵抗诱惑的时候、争夺或保卫所爱之物的时候,这样的情形之下,很显然,容易滋生高贵品质和英雄主义。但是当今社会天下太平;而且我们已经付出巨大努力,阻止狂热恋爱的发生;党派纷争也不存在;每个人都经过了驯化,他们顺其自然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这些自然而然做的事情总体上来说都是令人愉悦的。当一个人诸多的自然冲动都可以任意发泄,还存在什么诱惑需要我们抵抗呢?然而一旦不幸的情况发生,人们遭遇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又何必去抵抗烦恼呢,因为有索玛,可以让人们一下子远离糟糕的境况,等于去度假了。索玛会平息一个人的愤怒,使你与敌人握手言和,使你忍耐力增强,可以抵御长久的折磨。过去,拥有这样的自我控制力需要巨大的努力,需要经历长期而艰苦的道德训练,而现在,只需吞上两三粒半克大小的药片,你就万事大吉了。现在,所有人都可以是正直无畏的。只需随身携带一个索玛药瓶,你就携带了至少一半的道德性。无畏无惧的基督精神,不就是索玛提供的吗?”
“可是眼泪怎么能缺少。你忘记奥赛罗所说的了吗?‘倘若狂风暴雨之后必然跟随海清河晏,那便一任狂风呼啸,直到吹醒死者吧。[9]’曾经有一个印第安老人告诉我这么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玛萨琪的姑娘,想娶她的人需要在她的花园里耕耘一个早晨,事情听来容易,但是花园里到处飞着富有魔力的苍蝇和蚊子,绝大部分年轻人都不能忍受蚊虫的叮咬,只有一个人忍受这些痛苦,就是他,最后获得了姑娘的芳心。”
“迷人的故事!可是在文明国家里,”元首说,“你想要姑娘的话,可不需要给她们耕耘土地,也绝无苍蝇蚊子来叮咬你,几个世纪以前,文明就将这些蚊虫悉数消灭干净了。”
野人点头承认,却还是皱眉,他说:“你们消灭了蚊虫,不错,你们正是干这号事的人。你们会消灭任何令人不悦的东西,而不是学会忍受它们。‘无论是在精神上忍受狂暴命运投掷的石头和箭羽,或者全副武装抵抗无数的困苦,以反抗终结它们……[10]’可是你们什么都不做,既不忍受,也不抵抗,你们只是让投石和箭羽消失。这未免太容易了。”
他突然间沉默了,想起了母亲。在三十七层公寓她的卧室里,琳达漂浮在一个声光色香俱全的海洋里,越漂越远,远离时空,远离她记忆的牢笼,远离她的习惯,远离她衰老浮肿的身体。而托马亲,这个孵化场及驯化中心的前主管,仍在度他的索玛假期,以此远离屈辱和痛苦,在他的索玛世界里,他不必听到那些闲言碎语、嘲笑之声,多么美丽的世界啊……
“你们需要的,”野人继续说,“是某种带眼泪的东西,可是,我看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与眼泪的价值相匹配。”(先前野人也讲过这个观点,当时亨利·福斯特反驳说:“价值?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够吗?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啊,这就是我们新的驯化中心的造价,一分钱都不能少。”)
“‘纵使为一个蛋壳,也敢于挺身而出,以凡人无望之身,抗拒命运、死亡、危险。’[11]这句话里不是深有意义吗?”他抬头看着穆斯塔法·蒙德问道,“虽然上帝遥远,但上帝必定是这精神的源泉。难道冒险而活就没有价值?”
“其实有很高的价值,”元首回答说,“男男女女必须时不时地刺激一下肾上腺素嘛。”
“什么?”野人不解地问道。
“这是保证完全健康的条件之一。因此我们强制规定所有人都要进行V.P.S.治疗。”
“V.P.S.?”
“就是激情替代治疗,基本上是一个月一次。治疗时,我们让人体整个系统都充满了肾上腺素,从生理上说,这就等同于让人经历恐惧、愤怒等极端情绪。于是,我们感受到杀死苔丝狄蒙娜或被奥赛罗杀死的刺激,却无需承担真正的折磨。”
“可是我喜欢折磨。”
“但我们不喜欢,”元首说,“我们更喜欢舒舒服服地完成事情。”
“但是我不喜欢舒服。我想要上帝,我想要诗歌,我想要冒险,我想要自由,我想要慈悲,我也想要罪孽。”
“其实,”穆斯塔法·蒙德说,“你要求的,不就是痛苦的权利吗?”
“不仅是痛苦的权利,我还想要变得老丑无能的权利,患上梅毒癌症的权利,食不果腹的权利,败衣破絮的权利,朝不保夕恐惧不安的权利,患上伤寒的权利,还有被所有其他难以言尽的痛苦折磨的权利!”话音落下,屋内陷入长久的沉默。
“我申请这所有的权利。”野人最后说道。
穆斯塔法·蒙德耸耸肩。“你会如愿以偿的。”他说。
* * *
[1]《师主篇》,中世纪著名的天主教灵修书籍。
[2]《宗教经验之种种》是威廉·詹姆斯出版于1902年的著作。
[3]枢机主教纽曼,即约翰·亨利·纽曼(1801—1890),十九世纪英国重要的宗教人物,牛津运动(英国基督教圣公会重整教义礼仪的一场运动,起源于1833年牛津大学,故而得名)的领导者,并创建了爱尔兰天主教大学。
[4]语出莎士比亚悲剧《约翰王》第三幕。
[5]曼恩·德·比朗(1766—1824),法国哲学家,神秘主义的神智论者。
[6]弗朗西斯·赫伯特·布拉德利(1846—1924),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代表人。
[7]语见《李尔王》第五幕。此处对话,情节背景如下:格劳斯特伯爵之长子埃德加与伯爵私生子埃德蒙对话,埃德蒙陷害其父,其情妇里根(李尔王次女)使其眼瞎。
[8]语见《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二幕。
[9]语见《奥赛罗》第二幕。
[10]见《哈姆雷特》第三幕。
[11]见《哈姆雷特》第四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