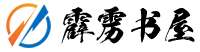花园弄弥留医院是一座六十层的高楼,贴着樱草色的瓷砖。野人踏出出租直升机时,看见一列花枝招展的空中灵车,盘旋着离开天台,向公园方向,朝西飞过去,目的地是羽化火葬场。在电梯门处,值日的门房给了他所需的消息,于是,他坐着电梯到第八十一号病房(门房说那是急性衰老病区),是在第七层楼上。
八十一号病房很宽阔,里面布满了阳光,粉刷成黄色,有二十个床位,所有床位上都有人躺着。琳达正与别人一起等待死亡到来,她不孤单,而且这里设施都是现代化的。欢快的合成乐使室内氛围始终活跃,每张床的床脚都有一台电视机,正对着这些将死之人。电视机始终开着,好像拧开的水龙头,从早到晚播放着节目。每隔十五分钟,室内的香水就要换一种味道。在门口接待野人的护士解释说:“我们试着在室内制造一种完全舒适的氛围,介于第一流的宾馆和感官影院之间,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
“她在哪里?”野人问道,对护士礼貌的解释无动于衷。
护士感觉被冒犯了,“你很忙吧。”她说。
“还有希望吗?”他问。
“你是说,指望她不死?”(他点点头。)“不,绝无可能。只要送过来的人,没有希望……”但是看到野人苍白的脸上那副痛苦的表情,护士一惊,没有顺着说下去。“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她问道。在来客中,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呢。(其实倒不是说这里有很多访客,或者说这里本来就没有理由出现很多访客。)“你是不是感觉生病了?”
他摇摇头。“只是她是我的母亲。”他说话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到。
护士用震惊、恐惧的眼神瞄了他一眼,赶紧转移了视线。
从脖子到太阳穴,她的皮肤全部变得通红。
“带我去找她。”野人说,竭力想用平常的语调说话。
虽然满脸通红,护士还是沿着病房往前带路。他们一路走,一路看见许多娇嫩、未见任何衰老的面庞(因为衰老是如此急性、突然,故此只有心脏和大脑衰老了,而面颊还没有来得及变老)。又看见了处于第二度婴儿期的人,他们那空洞、对万事不感兴趣的眼神目送着二人前行,看到这眼神,野人打了个寒战。
琳达躺在那一长溜靠墙的病床的最后一张上。她背靠着堆起来的枕头,正看着床脚电视里直播的南美洲黎曼曲面网球冠军赛半决赛,却只有图像,没有声音。电视里的人全部缩小了,他们在明亮的玻璃的方形球场上,沉默着跑来跑去,好似鱼缸里的鱼——这些另一个世界的居民啊,它们一面沉默,一面却焦虑不安地游来游去。
琳达观看着,茫然并不明所以地微笑着。她那苍白浮肿的脸庞上浮现着无知者才有的那种开心的表情。她的眼睑不时闭上,有那么几秒钟,她似乎在假寐。但是突然一机灵,她又醒过来了,似乎是被网球冠军们小鱼一样的滑稽动作所唤醒,又似乎被超高音歌唱家吴丽翠琳娜的名曲表演《甜心,抱紧我,你让我迷醉》所唤醒,又似乎被她头上换气扇里吹出的马鞭草的温暖的气流所唤醒——总之,这些事物皆能使她醒来。但是,如果更精确地描述的话,她或许更像是被一个梦唤醒,在这个梦里,所有这些事物,在她血液中索玛的影响下,变形了,美化了,成为妙不可言的世界的一部分。她再一次微笑,那支离褪色的微笑啊,像一个婴儿一般满足了。
“你看,我得走了,”护士说,“我那帮孩子们马上要过来,此外,三号床上那位随时会翘辫子,”她朝病房上边一指,“那就请你自便吧。”
她欢快地走开了。
野人在床边坐下来。
“琳达。”他握住她的手,轻声呼唤着。
听到自己的名字,琳达转过了身子。因为认出他,她迷蒙的双眼乍然一亮。她捏着他的手,她微笑着,她的双唇在蠕动。突然,她头一歪,睡着了。他坐在那里,看着她,看着这倦极的躯壳,渴盼着穿越时光,找回那张年轻、明亮的面庞。在玛尔普村,这面庞曾照耀着他的童年。闭上眼睛,他忆起她的声音,她的动作,和他们共度的所有好时光。“雄鸡粘上链球菌啊,右拐跑进班伯里T,有啥稀奇瞧一瞧啊?……”她那歌声曾经何等动听啊!那童谣的韵律,是何等魔幻、陌生而神秘啊!
“A,B,C,维生素D,脂肪存在于肝脏,鳕鱼存在于大海。”
当他回忆其那些词语,还有琳达的声音,他泪如泉涌,那滚烫的泪水啊。还有,还有那阅读课:“小孩在盆里”,“猫在垫子上”,“胚胎商店β员工基本操作说明书”。还有那冬夜火堆旁的漫漫长夜,或者盛夏之时在小屋的楼顶,当她讲述关于远在保留地之外的“它世界”的故事,“它世界”是那般美丽,那般美丽哟,在她的回忆里,那里就是天堂,是善与美的天堂,即使他已经接触了这真实的伦敦城,这里真实的男男女女的文明人,但那天堂般的“它世界”在他心中依然洁白无瑕、纯粹唯一、无可撼动。
突然间,一阵尖叫使他睁开了双眼,匆忙擦去泪水,他抬头张望。只见一支长长的队伍走来,都是一模一样的孪生男孩,八岁大小,他们鱼贯而入,似乎没有尽头。两人一组,两人一组,依次跟随。噩梦啊!他们的脸,那不断重复的脸——因为这么多脸其实只是一个模子——慢吞吞地盯着前面,那完全一致的鼻子,那完全一致的灰白的瞪着的眼睛。他们的衣服是统一的卡其装。他们的嘴巴全部张开。叽叽喳喳,不时叫唤,他们就这样进来了。一时之间,整个房间似乎布满了蛆虫,这些蛆虫,挪动到床间,或者爬到床上,或者钻到床下,或者把头往电视机柜子里伸,或者朝将死者们做鬼脸。
但是琳达吓坏了他们。一群小孩站在她的床脚,仿佛一群野兽忽然遭遇未知之物,怀着那种又恐惧又愚蠢的好奇之心,他们盯着琳达看。
“哎呀,快看,快看!”他们低声说着,显得很害怕,“她是怎么了?她为什么这么肥胖?”
他们从未见过一张脸会像琳达那样,这张脸既不青春,皮肤也不紧致,她的身体也不再苗条、笔挺。可是,其他所有那些六十多岁的人,都已经在等死了,却还保持着宛如幼女的容貌。与之相比,四十四岁的琳达,看起来像是一个松松垮垮、歪歪扭扭的老妖婆。
“她不是很可怕吗?”他们低声评论着,“看看她那牙齿!”
突然,从床下钻出来一个,哈巴狗一般的脸,钻到约翰的椅子和墙之间,站起来,便凝视着琳达熟睡的脸。“喂,我说……”他话还没说完整,就发出一声尖叫,原来野人抓住他的衣领子,一把拎起来,给了他一耳光,他便尖叫着溜走了。他的尖叫声引来了护士长匆忙过来护犊。
“你对这孩子做了什么?”她严厉地问道,“我不允许你攻击孩子们。”
“可以,那就让他们滚远些。”野人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这些脏兮兮的小屁孩究竟在干什么?简直丢人现眼!”
“丢人现眼?你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在对他们进行死亡驯化。我告诉你,”她凶恶地警告他,“如果我听说你又干扰了他们的驯化,我就叫人来把你扔出去。”
野人站起来,向她走过去几步。他的举动,还有他脸上那种表情,是那么吓人,护士长畏惧地后退了。
他竭力控制住自己,一言不发,转身还是坐在了床边。
护士长松了一口气,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只是略显犹豫,声音尖利:“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已经告诉过你,请你记住。”然后,她不说话了,领着那些好奇心十足的孪生子们走开,去做“找拉链”游戏——她的一个同事在另一个房间里已经布置好了。
“走吧,亲爱的,去喝杯咖啡吧。”她对另一个同事说,说话间又恢复了领导的自信,这使她舒服多了。“好了,孩子们!”她叫道。
琳达心神不安地在床上动着,睁开双眼,茫然四望了片刻,然后再一次睡着了。在她旁边坐着,野人努力找回几分钟之前那种情绪。“A,B,C,维生素D。”他向自己念叨,似乎这些词语就像一段符咒,可以将过去重现。但这符咒不起作用。那些美好的记忆很顽固,它们拒绝浮现,他所唤起的,不过是妒忌、丑陋、痛苦和那令人憎恶的回忆。珀毗受伤的肩膀流下血来,琳达昏睡,苍蝇围着洒在床边地上的龙舌兰酒渍嗡嗡而飞,男孩们当着琳达的面喊叫那些肮脏的称呼……啊,不,绝不!他闭上眼睛,摇着头,拼命驱赶这些回忆。“A,B,C,维生素D……”他努力回想当年坐在琳达腿上的时光,那时琳达会抱着他,一遍又一遍地为他哼唱,摇着他,摇着他啊,直到入眠。“A,B,C,维生素D……”
超高音歌唱家吴丽翠琳娜的歌声渐渐强化,如泣如诉。忽而,马鞭草的香味散去,芳香循环系统自动替换为强烈的广藿香。琳达又动了动,睁开眼睛,朦朦胧胧地盯着半决赛的选手们,看了几秒,然后抬起头,就着那崭新的芳香空气,深深呼吸了一两口。她突然笑了。那是童真的欢喜的笑容。
“珀毗!”她喃喃叫道,闭上了眼睛。“啊,我如此喜欢那酒,真的,如此喜欢……”她叹了口气,然后头又陷进枕头里。
“可是,琳达!”野人哀求着说,“你就认不出我了吗?”他尽了全力,可是为什么她还是提醒他过去的存在?他抓紧她那虚弱的手,几乎是粗暴的,仿佛他要强迫她从那低俗的欢乐之梦中苏醒,从那下贱可憎的回忆中脱身,让她回到当下,回到现实。这当下或许令人惊惧,这现实或许令人害怕,但它们毕竟是崇高的、有价值的、极其重要的,因为当下和现实意味着我们的存在,而死亡却已迫在眉睫,存在的消失不令他们感到恐惧吗?“琳达,你就认不出我了吗?”
他感到她手上的力量微微增强,似乎在做回答。他的眼睛再度充溢泪水。他弯下腰,最后亲吻了她。
她的嘴唇在蠕动。“珀毗!”她轻声呼唤,这声呼唤就像一桶屎尿泼在他脸上。
他内心深处忽然爆发出熊熊怒火。再次被忽视,使他那悲伤之情忽而找到了另一条发泄的途径:转化为了强烈的痛愤之情。
“见鬼,我是约翰!”他吼道,“我是约翰!”在一片愤怒与痛苦中,他竟抓住她的肩膀,猛烈摇晃她。
琳达眼睛眨了几下,终于睁开了。她看见了他,认出了他?“约翰!”可却像是在一个迷梦般的世界里认出了约翰那真实的脸,那真实的粗野的双手。这迷梦般的世界存在于她的内心,由那广藿香、超高音乐、变形的记忆、错位的感官组成。她认出对面的是约翰,是她的儿子,却把他想象成一个误入玛尔普天堂的人,在玛尔普天堂里,她正和珀毗一起度着索玛假日呢。他怒火中烧,因为她更喜欢珀毗。他仍然在摇晃她,因为珀毗现在就在那张床上——这或许是个错误,因为一个文明人不会这么做。“每个人都属于别……”她说着,但声音却突然虚化,无法听清,仿佛喘不过气的人发出那种咯咯的声音。她的嘴张开了,她最后一次拼命呼吸空气,但她似乎却忘了究竟该如何呼吸。她试图哭出来,但只是无声。只有那双瞪着的眼睛中透露的恐惧,才显露出她身心的痛苦。她的手摸向自己的脖子,又伸手要去抓空气——那是她再也无法呼吸的了。对她来说,空气其实已经不再存在。
野人跳起来,弯腰看着她。“什么,琳达?你在找什么?”他的声音是恳切的,似乎乞求琳达能让他安心。
可是她回过来的眼神却满含一种难以言表的恐惧,这恐惧对他来说,就是谴责。
她试图从床上坐起来,却又跌回到枕头上去。她的脸扭曲得可怕,她的嘴唇一片铁青。
野人转身跑到病房外面。
“快,快!”他吼叫着,“快啊!”
站在一圈做着“找拉链”游戏的孪生子的中间,那护士长抬头观望。她最初的震惊迅速转为反感。“别大吼大叫!想想看,这里还有小孩子,”她皱着眉头说,“你会破坏他们的驯化过程……你想干什么?”原来野人冲破了游戏圈。“你小心!”但一个孩子已经哭叫开来。
“快,快!”他抓着护士长的袖子,拖着她走,“快!出事了,我杀了她。”
当他们到达病房最后面时,琳达已经死去。
野人沉默了,像被冰冻住一样孤立无援。他跪在床边,双手捂住脸,再也克制不住,啜泣起来。
护士站在一边,犹豫不定。看着跪在床边的那个人(这场景实在无耻),而此时那些停止游戏的孩子们(天啊,可怜的孩子们)正从病房门外往里看呢,他们的双眼、鼻子都朝着发生在第二十床床边的这令人震惊的一幕。她是不是要告诉他?让他表现得像个体面人士?提醒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或者告诉他这样做对这些无辜的孩子们会造成多么致命的伤害?他们所受的死亡驯化就因为他恶心的鬼哭狼嚎而全盘失效,孩子们会以为死亡是可怕的事情,认为人会在乎死亡到这样的程度!这不就让孩子们对死亡产生最灾难性的想法了吗?是否会让他们从此完全背离正确的行为方式,甚至走上反社会的道路?
她走上前,敲敲他的肩膀。“你就不能行为正派点?”她低声说,语带愤怒。但是一回头,她却看到有六个小孩子已经向病房这边走过来。游戏圈已经破裂了,只要再过一会儿……不行,这样风险太高了,如果队伍解散,这个波氏胚胎组的驯化将推迟六到七个月。她立刻跑向自己那摇摇欲坠的工作岗位。
“好吧,谁又想要一块巧克力泡芙呢?”她问,声音响亮,充满了欢乐。
“我要!”这个波氏胚胎组所有的孩子齐声叫道。于是,发生在第二十号床的事被彻底遗忘了。
“啊,上帝,上帝,上帝……”野人一遍又一遍地呼喊。此刻他的心中一片凌乱,悲伤、懊恨交集,只能发出这一个清晰的词语。“上帝啊!”他的低语声提高了,“上帝……”
“他究竟在说什么?”一个声音说,近在咫尺,发音清晰,有些刺耳,穿过超高音乐那婉转的歌声,到了他耳边。
野人猛地一惊,他放下手,抬头一看,只见五个穿卡其衣服的孪生子,每人右手都拿着一根吃剩的长泡芙,那一模一样的脸庞上,巧克力汁却沾在不同的位置。他们站成一排,哈巴狗一般直愣愣地看着他。
双方眼神一交汇,孩子们就同时傻笑起来。其中一个用泡芙的一头指着琳达问:“她死了吗?”
野人看着他们,沉默了一会。在沉默中,他站起来。在沉默中,他慢慢走向大门。
“她死了吗?”那个好奇的小孩一路小跑跟着他,追着问。
野人低头看着他,一言不发,把小孩推开。那孩子跌倒在地,立刻就号叫起来。野人对此却看都没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