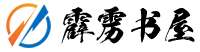一
古怪,古怪,古怪,这是列宁娜对伯纳德·马克思的评价。古怪之极,以致在其后的几周时间里,她不止一次琢磨,是否要取消与伯纳德前往新墨西哥度假的约定,选择与贝尼托·胡佛去北极。问题是,就在上个夏天,她曾与乔治·埃德赛去过北极,更糟糕的是,她觉得北极冰寒无趣,无事可做,而且宾馆非常破败,令人极其失望,卧室里甚至都没有电视机,也无芳香乐器,只有极其过时的合成乐,电梯壁球场地也只有二十五个,客人倒是超过了二百人。不,她果断地想,不能再去北极了。更何况,美洲她只去过一次呢,而且印象几无,她都想不起来是跟让-雅克·哈比布拉[1]还是波卡诺夫斯基·琼斯一起去的纽约了,那实在是极其简单的一次周末度假。不管怎样,总之那次纽约之旅无足轻重。而这次就不同,想想看,再次飞向西半球,而且度假时间长达一个星期,实在诱人极了。更诱人的是,他们还要在野人保留地待上三天呢!算起来,驯化中心里去过野人保留地的人寥寥无几,不超过六人。身为增α族人又是心理专家的伯纳德,是她所知少数有权去那里的人中的一个。对于她来说,这个机会实在是天赐的。可是,伯纳德的古怪也是常见的,以致她对是否把握这个机会犹豫不决,也曾认真想过是否和风趣的贝尼托老兄再度冒险去去北极,毕竟,贝尼托算是个正常人。可是,伯纳德呢,他啊……
“血液替代品中掺入了酒精。”范妮的这个解释可以说明伯纳德为何处处透着古怪。可是,某次她和亨利同床共枕时,有些焦虑地与亨利讨论起她这个新情人,亨利却把可怜的伯纳德比作一头犀牛。
“你别指望能教会一头犀牛,”他解释说,一如既往的简洁、富有激情,“有些人真的就像是犀牛,他们无法正确接受驯化。这些可怜的鬼崽子!伯纳德就是其中一个,幸运的是,他倒是擅长自己的工作,否则主管早就将他扫地出门了。不过,”他用安慰的口吻说,“他这个人倒也不怎么坏。”
或许是不怎么坏吧,可是却着实令人不安。首先就是他那股私底下神神秘秘干事情的狂热模样,照直了说,也就是这个人什么事都不干,因为人怎么可能私下里做自己的事情呢(当然,私下里他们上床了,不过不能总是卧在床上啊)?
再说了,美洲有什么好东西?几乎就没有。抵达的第一个下午,他们外出,情况还相当不错。列宁娜建议他们一起到托基乡村俱乐部游泳,然后到牛津学联晚餐,但是伯纳德却认为那里人太多。她又提议去圣安得烈电磁高尔夫球场打一轮高尔夫,伯纳德又一次否决了,他认为打电磁高尔夫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那么我们怎么度假?”列宁娜很惊奇地问。
结果,他的提议是,去滨湖区漫步,然后爬到斯基多峰顶上,并在石南花丛中走上个把小时。“只有我和你,列宁娜。”他说。
“可是,伯纳德,这不就是说,我们要整晚都远离人群。”
伯纳德脸红了,目光躲闪。“我是说,我想和你一个人说说话。”他咕哝着。
“说话?说什么?”散步、说话,如此就耗费掉一个下午?实在太古怪了。
最后,在列宁娜的坚持下,伯纳德让步了,他们飞往阿姆斯特丹,观看了女子重量级摔跤锦标赛半决赛。“深处人群之中啊,”他咕哝着说,“一如往常。”于是一整个下午,他固执地阴沉着脸,拒绝与列宁娜的朋友们说话(在摔跤比赛暂停的间歇,他们在冰激凌索玛吧台前碰到了好几十个这样的朋友),并坚决不吃她递过来的覆盆子圣代冰激凌(内有半克索玛)——其实吃不到圣代他也很痛苦呢。“我宁愿一人,即使下流腌臜;也不愿成为别人,即使欢乐幸福。”
“一克索玛及时喂,胜过十克同时服。”列宁娜说,她引用了睡眠教材里的至理名言。伯纳德却不耐烦地推开了玻璃杯。
“好吧,千万别发脾气,”她说,“一立方厘米的药量可以治好十次情绪低沉呢。”
“见鬼,看在主福特的面子上,请你安静点!”他叫道。
列宁娜晃晃肩膀,“一克药总比见鬼好。”她最后说,一脸傲然高贵之貌,独自吃完圣代冰激凌。
返回路上,飞过海峡时,伯纳德非要把飞机停住,于是,直升机就在波浪一百英尺之上的地方盘旋着。天气正变得糟糕,一阵西南风陡然兴起,天空阴云密布。
“你看。”他强调说。
“可是天气太糟糕了。”列宁娜说,从窗户旁缩回了身子。夜色中涌动的空虚感、身下不停起伏的黑色的泡沫、苍白的月光(在加速涌集的乌云掩映之下,这月光显得如此憔悴与散乱),实在令她惊骇。“快点开广播,快点!”她急切地伸手够到仪表板,扭动广播调频,随意打开了一个频道。
“……天空照影在你心间,蓝色而忧伤,”乃是十六个颤抖的假声歌手,“天气永远是那么……”
突然咯嗒一声,然后一片寂静。原来伯纳德关掉了调频。
“我想在安静中欣赏大海,”他说,“但耳边响着野兽般的噪音,又怎么有心思去欣赏?”
“可是这音乐很动人,而且我也不想往下面看。”
“可是,我想看,”他坚持说,“大海让我感到,似乎……”他犹豫了下,想寻找词语表达此刻的想法,“似乎我原本可以是一个更像我的人,但愿你明白我的意思。一个更纯粹的自己,而不是彻底成为别的事物的一部分,更不是社会肌体内一个小小的细胞。列宁娜,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列宁娜哭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一遍遍重复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一个人怎么可能不想成为社会大集体的一部分?更何况,每个人都为别人工作,没有他人我们将一事无成。即使ε族人……”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伯纳德嘲弄道,“你会说:即使ε族人也是有用的!对吗?我也是有用的,对吗?我真他妈希望自己是没用的。”
他渎神一般的粗鲁吓坏了列宁娜。“伯纳德!”她谴责他了,声音听起来既惊奇又悲痛,“你怎么可以这样!”
伯纳德的回答却用了另一种声调,“我怎么可以这样?”他沉思着重复她的话,“不,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我不能这样的原因何在?或者换种说法——因为毕竟我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假如我曾自由过,并不曾被驯化,思想也不曾被奴役,那么我是否可以这样,这样做又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伯纳德,你说的这些都是最大逆不道的啊!”
“列宁娜,难道你不希望自己是自由之身?”
“你说的话我一点不懂。我是自由的呀。我很自由,可以尽情享受最美好的时光呀,而且如今人人都快乐。”
他忍不住笑起来,“你说的妙极了:如今人人都快乐。所有儿童在五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他们快乐了。可是,列宁娜,你不想体验另一种形式的自由和快乐吗?比如,以你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别人的方式?”
“你说的话我一点不懂,”她重复着刚才的话,然后转身对伯纳德说,“行了,伯纳德,我们回去吧,”她恳求道,“我痛恨现在这个地方。”
“那么你是不喜欢和我在一起?”
“当然不是,伯纳德。我只是说这个地方糟糕透了。”
“我本以为,在这里,我们会更亲密,因为这里只有大海与月光。我们本应比在人群中感到更多的亲密,甚至比在我的房间里更亲密。你明白我的话吗?”
“我什么也不明白。”她坚定地说。她不否认,她真的是完全不理解他。“真的一点都不明白,尤其是,”她换了副腔调,“当你头脑里竟是这些可怕的胡思乱想时。你为什么不吃点索玛?吃点索玛,你会忘记这糟糕的一切,你也不会再感到痛苦,相反你会快乐,极其快乐。”她重复着快乐这个单词,微笑着,露出她诱人、放荡的谄媚姿态,虽然在她眼中困惑与焦虑不曾散去。
他沉默地望着她,面无表情,甚为严肃。他是那样一心一意地看着她呀。几秒钟后,列宁娜躲避了他的目光。她很紧张,却仍微微一笑,试图说些什么,却无话可说。沉默便自行弥漫开来。
终于还是伯纳德开口,声音很低,很疲惫。“那就这样吧,”他说,“我们将返回。”他狠命踩着油门,驾驶着飞机直冲云霄。到达四千英尺的高空,他打开了螺旋桨。在沉默中,他们飞行了一两分钟。突然,伯纳德笑起来。
实在太古怪了,列宁娜想,可是,这真的是他的笑声。
“感觉好些了?”她鼓起勇气问。
作为回答,他只是从控制器上抬起一只手,搂住她的肩膀,开始爱抚她的胸脯。
“感谢主福特,”她暗自想,“他终于正常了。”
半小时之后,他们回到了他的房间。伯纳德一口气吞下四片索玛,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开始脱衣服。
“喂,”第二天下午,当他们在天台碰面时,列宁娜刻意用淘气的语调问道,“你觉得昨天如何,是不是玩得尽兴?”
伯纳德点点头。他们爬进飞机。短暂颠簸一会,飞机起飞了。
“大家都说,我很丰满。”列宁娜自省一般地说道,一面轻轻拍着自己的双腿。
“确实丰满。”伯纳德说,可是在他眼中却有一丝痛苦。像是肥肉,他想。
她抬头看着他,似有些焦虑。“可是,你不会认为我过于肥胖了吧?”
他摇摇头。你只是像许多许多的肥肉。
“你真的认为我很棒?”
他再次点头。
“每个地方都很棒?”
“你完美无缺。”他大声回答。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却告诉自己:“她就是这么自我理解的,她并不介意自己只是一堆肥肉。”
列宁娜笑起来,像一个胜利者一般。可是,她自我满足的太早了。
“只是,”伯纳德犹豫一会,继续说道,“我仍然希望,事情会以不同的结局出现。”
“不同的?”会有不同的结局吗?
“其实,我本不希望我们最后会同床共枕。”他终于挑明了。
列宁娜极其震惊了。
“我是说,我不想立刻和你上床,至少不是第一天。”
“那么到底是什么……”
他又开始长篇大论,她完全不懂,都是些危险的胡说八道。列宁娜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思维的双耳堵住,可是没用。时不时地,一个句子就强迫她去听。“……我想看看控制自己的冲动会有什么结果。”她听到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些词语似乎触碰了她思维上的某根弦。
“行乐当及时,何必推来日?”她冷峻地说。
“从十四岁到十六岁半的时间里,每两周一次,每次重复二百遍。”这就是他的评论。然后他继续他的风言风语。“我想知道,何为激情,”她又听到这句话,“我想强烈地体验某些事物。”
“当个体自作主张,社群将蹒跚混乱。”列宁娜指出。
“不错,可是,为什么社群就不能混乱一些?”
“伯纳德!”她抗议了。
可是伯纳德毫无羞耻。
“智力上、工作时,本是成人;表达情感、欲望,却蠢如婴儿。”
“主福特热爱婴儿。”
伯纳德不顾她的插话。“不久前某天,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可以从始至终都像一个成年人。”
“我根本不明白。”列宁娜的声音都快僵硬了。
“我知道。因此昨晚我们才会上床,就像婴儿一样。若是成年人,我们不会这么匆忙,我们更愿意多些期待。”
“可我们不是很快乐吗?”列宁娜固执地说。
“是啊,那是至乐的境界。”他回答道,可是,他的声音如此悲伤,他的表情充满如此深沉的痛苦,列宁娜感觉到了,于是,她短暂的胜利情绪随即挥发殆尽。
或许,他终于还是发现,她过于丰满了。
当她后来向范妮吐露心声时,范妮就说了一句话:“我早就告诉过你,他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人家给他的血液替代品里掺杂了酒精。”
“不管如何,”列宁娜固执地说,“我倒真喜欢他。他的手非常优雅,而且当他晃动他的肩膀时,别提有多迷人了,”她叹了口气,“可是,真希望他不是这么古怪的人。”
二
在主管办公室门前,伯纳德略微停顿,深呼吸,挺胸,迫使自己能抵抗即将到来的厌恶感。他知道,在主管办公室里,他一定会感受到这种厌恶感。他敲门,走进去。
“主管先生,请您签字。”他尽量轻快地说,把请示公文放在主管的写字台上。
主管狐疑地看着他。但是世界元首办公室的印章敲在公文天头,穆斯塔法·蒙德的签名粗而黑,横过公文的地脚,程序无误。主管只能签字,他拿起铅笔,写下他名字的首字母,两个又小又灰白的字母,孤苦伶仃地屈居穆斯塔法·蒙德签名之下。他不发评论,也无意亲切问候,正准备将请示公文返还给伯纳德时,突然被请示文字中的某些内容吸引住了。
“到新墨西哥野人保留地?”他说,他的音调和他抬起来望着伯纳德的脸色,皆显出一种焦虑与不安。
主管的惊讶让伯纳德也感到惊讶,他只能点点头。两人都沉默了。
主管靠着椅背,皱起眉头。“多久之前的事情了?”这话更像是自言自语,不像是对伯纳德说的。“我猜是二十年前,或者二十五年之前,那时,我肯定像你这样的年纪……”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伯纳德感到非常不快。身为主管,此君一贯循规蹈矩,谨慎为人,从不出错,现在说出来的话,却有些颠三倒四。这使他渴望把自己的脸藏起来,或者直接跑出房间。并不是他对旁人谈及遥远的旧事一定就反感——对过去的反感本来就是他已经去除(他认为是这样)的睡眠教材中的偏见之一。令他选择回避的原因在于,主管本来是反对忆旧的,可是现在,他倒自己犯贱,谈论起犯禁的事情来。主管内心被什么冲动控制了?纵使不快,伯纳德还是很热切地听主管忆旧下去。
“那时,我也有和你一样的想法,”主管说道,“想去看看野人。于是,我得到了允许,前往新墨西哥,去度过我的暑假,当时正约会的女孩陪我一起去。她是一个副β族人,我想,”这时他闭上了眼睛,“我想,她的头发是黄色的,她很丰满,非常丰满,我仍然记得这点。我们到了那里,也看到了野人,我们骑在马背上,我们把该玩的都玩了。然后,几乎就在我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天……她失踪了。当时我们骑马往一座险恶的山上去,天气酷热,令人窒息,午饭后,我们睡觉了,至少我是睡着了。她肯定是独自一人出去走一走,不管真实情况如何,最后的情况是,我一醒来,发现她人不在。与此同时,雷电交加,劈头盖脸而来,这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恐怖的暴风雨。雨水倾泻而下,风雷在咆哮,闪电剪切着天空。马匹受惊,挣脱缰索而去。我扑过去,本想把马拦住,却只弄伤了膝盖,以至寸步难行。即使如此,我仍然四处搜寻,呼喊她,寻找她。可是到处都看不到她的身影。当时我想,她恐怕是独自回休养所去了,所以,我就沿原路返回,连滚带爬,下到山谷。我的膝盖疼痛极了,索玛也被我弄丢了。到达山谷,我花了很长时间,直到后半夜,我才终于到达休养所。而她并不在那里。她不在那里。”主管重复着这句话。
两人都沉默了。
直到主管继续讲他的过去。“第二天,大家都去寻找,但是没人发现她的踪迹。她肯定是摔倒在某处水沟里,或者被一头美洲狮吃掉了。只有主福特知道。这件事实在太可怕了,那时的我极其痛苦,我敢说,恐怕有些过度痛苦了。因为,毕竟这是有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意外,再说了,不管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如何变化,社会肌体本身将青春永驻。”可是,看样子这句睡眠教材里的安慰话并不起明显的效果,主管还是摇着头,“有时我真的会做噩梦,想到这件事,”他低声说道,“梦到自己被雷鸣惊醒,发现她一去无踪影;又梦见自己在树林里,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她。”他深深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沉默再次降临。
伯纳德几乎带着嫉妒心评论说,“那么你一定非常震惊。”
他的声音使主管立刻意识到自己目前身在何处,他意识到自己在犯罪,便扫了伯纳德一眼,又立刻转移了目光,脸色煞红,却一脸阴沉。他再次看了伯纳德一眼,心头陡然起了疑心,自尊心的作用使他怒火中烧。“千万不要以为,我和那女孩有什么苟且之事,我们之间绝无情感,绝无牵挂,我们之间关系非常健康,非常正常。”他随手将请示公文递给伯纳德。
因为将如此不堪的秘密泄露给别人,他对自己也很恼火,并将怒火发泄在伯纳德身上。现在他的眼神中袒露无遗的,都是怨恨。“现在,马克思先生,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告诉你,有关你工作之余时间里的行为报告,我看了极其不满意,你会说这与我无关,但是我告诉你,这跟我有关系。在中心里我名声很好,我的手下都必须是无可挑剔的,尤其是那些高级种姓的人。α族人驯化已然到位,他们在情感行为中无需表现出婴儿之心,但是正因如此,他们更需刻意遵从社会规范;情感行为婴儿化,是他们的责任,即使这会违背他们的习性。所以,马克思先生,我善意地告诫你,”说着说着,主管的声音由义愤填膺转而变为纯粹的客观公正——这等态度代表了社会对马克思行为的否决,“假如我再听说你有任何违背婴儿化标准礼仪的倒退行为,我将会把你调到中心的下属机构去——最好是冰岛。行了,请便吧。”他一边旋转着椅子,一边拈起铅笔,开始写什么东西。“足够教训这小子了。”他心想,但他想错了。
实际上,伯纳德离开房间时,可以说是大摇大摆、趾高气扬的呢,他显得非常高兴,砰一声关上门,满心都以为他在这世上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俨然在对世界秩序发出“挑衅”。他因自己地位的重要而欣喜、迷醉,即使主管的威吓亦不能使他泄气沮丧,反倒更像是在鼓舞他的气势。他深感自己足够强悍,可以面对迫害且克服困难,即使面对流放冰岛的危险也并无恐惧。而他一生从不真正相信会有人要求他“挑战”任何事物,想到这里,他的自信更加爆棚。要知道,从没有人仅仅因为类似的“挑战”而被下放——冰岛只不过是个威胁的借口罢了,这威胁甚至是极其振奋人心,令人提神的呢。沿着走廊独自走着的时候,他居然吹起了口哨。
随后他在评论此次与主管的会面时,把自己描述得像个英雄一样。“于是,我不屑地对他说:到你自己记忆的深渊里捡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吃吧,然后昂然出了大门。事情就是如此。”他说完,定睛看着亥姆霍兹·华生,期待他的首肯、鼓励、崇敬。结果,亥姆霍兹·华生单单静坐着,看着地板,一言不发。
他喜爱伯纳德。在他认识的人中,当他想倾诉自以为重要的事情时,伯纳德是唯一的听众,对此他很是感激。虽然如此,但在伯纳德言行之中,他亦发现有些东西是他深恶痛绝的,比如类似方才这样的炫耀,以及随之而来的间歇性的自怜自艾;又比如伯纳德事后逞英雄的可悲习惯,以及人不在现场却惯于显摆他无穷的高见。他憎恶这些,其实是因为他真的喜爱伯纳德。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亥姆霍兹仍然静静望着地板,突然,伯纳德脸红了,悄然离开。
三
旅途风平浪静。“蓝色太平洋”号火箭在新奥尔良提前两分半钟起飞,在德克萨斯半空因龙卷风延误了四分钟,但在西经九十五度区域,进入平滑气流层,飞行顺畅,因此,到达圣菲[2]时,只晚点四十秒。
“行程六个半小时,却只晚点四十秒,已经相当不错了。”列宁娜说。
当晚,他们即在圣菲入睡。旅店极佳(与其他某些旅店相比更是无与伦比得好,比如,上个夏天列宁娜曾入住其中却备受折磨的极光博拉宫):湿润的空气、电视、真空震动按摩机、收音机、滚热的速溶咖啡、催情的避孕剂,还有每个房间都安装的八种香精。当他们一走进大堂,合成乐播放器即开始工作,一切看来都完美无缺。电梯旁边贴的告示写道,在酒店里,有多达六十个电梯壁球比赛场,在公园里,还可以玩电磁高尔夫、障碍高尔夫。
“啊,听起来棒极了,”列宁娜叫道,“我真喜欢我们可以在此常住。有六十个电梯壁球比赛场呢……”
“在野人保留地,一个都不会有,”伯纳德提醒她,“也没有香精、电视,甚至连热水都没有。假如你感觉忍受不了,你就在这里待着,等我回来。”
列宁娜感觉受辱,反驳道:“我当然可以忍受,我只是说这里很棒,因为……因为进步让生活更美好,不是吗?”
“这句话,从十三岁到十七岁,每周五百次重复。”伯纳德无奈地说,有点像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
“我说进步让生活更美好,因此你不是一定要去野人保留地,除非你真的想去。”
“我当然想去。”
“那很好。”伯纳德说,听起来倒像是在威胁似的。
他们进入保留地需要保留地监守长的签字。第二天早上,他们前往监守长的办公室,以做说明。一个副ε族黑人门房接过伯纳德的名片,很快,监守长就请他们进来,此人是副α族人,白肤、碧眼、金发、头颅很短、个矮、红润、圆脸、宽肩膀,说话时嗓门洪亮,睡眠教材中的名言张口就出。他那肚子里,还有无数多余信息、谠言忠论,你不用说,他就主动告白。一旦开口,他便口若悬河,隆隆隆隆地响个不停。
“……五六万平方公里,四个分区,每个分区都建了一圈高压铁丝网。”
此时,伯纳德忽然无来由地想起来,旅馆淋浴间里的古龙香水水龙头忘记关了,香水白白流淌。
“……利用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水流进行水力发电。”
“在我返回之前,我要损失一大笔钱了。”伯纳德想,冥冥中似乎能看见香水流量表上的指针,像蚂蚁一样不知疲倦地一圈又一圈地慢慢爬行。
“快点打电话给亥姆霍兹·华生。”
“……超过五千公里的铁丝网都通了六万伏的高压电。”
“不要吓我哦。”列宁娜礼貌地说,其实对监守长所言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只是在监守长夸张的停顿时下意识地回应一句。监守长刚开始说话,她就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吞服了半克索玛,结果她就坐下来了,很是安静,其实不但耳朵听不到人声,大脑也是一片空白,单单将自己那双湛蓝的大眼睛盯着监守长的脸看,表情倒像是全神贯注呢。
“倘若碰到铁丝网,立刻就死翘翘了,”监守长郑重地说,“保留地里的野人,谁都别想逃出来。”
逃这个字眼令人浮想万千。“或许,”伯纳德半立半坐的样子,说道,“我们该走了。”想象中香水流量表上的那个指针已经一路小跑,像一个虫子,一步步咀嚼着时间,吞噬着他的钱。
“绝无逃亡,”监守长重复道,挥手请伯纳德坐回椅子上。既然监守长还没有在参观申请单上签字,他别无选择,只得听命。
“出生在保留地里的人——记住,亲爱的小姐,”他补充说,一面色眯眯地看着列宁娜,声音变得像是在跟人窃窃私语,“一定记住,在保留地里,小崽子们仍然是生出来的,是的,是母体直接生产,这种恶心的事情看起来似乎……”他本来指望提及这种下流的事情会让列宁娜脸红起来,不料列宁娜只是微笑,假装明白他在说什么,还来了一句:“不要吓我哦。”监守长失望了,只得继续说道:“那些在保留地里出生的人,注定也要死在那里。”
注定死去……每分钟可是十分之一公升的古龙香水在流淌呀。一个小时可就是六公升呢!
“或许……”伯纳德再次试着打断,“我们必须……”
身体前倾,监守长用食指敲打着桌子,“你们问我,保留地里住了多少人,我的回答是,”说到这里,他显出得意的神情来,“我们不知道准确数字,我们只是猜猜。”
“不要吓我哦。”
“我亲爱的小姐,我说的可是真的。”
六乘上二十四,不,应该是六乘上三十六更贴近。伯纳德脸都白了,他因不耐烦而颤抖。但是监守长叽里呱啦依然冷酷无情地继续说着。
“……大约是六万个印第安人或混血儿……纯粹的野人……我们的巡查员定期拜访……否则,他们将毫无机会与文明世界接触……他们仍然保留着令人恶心的风俗习惯……比如婚姻——假如小姐知道这个词,家庭……他们没有被驯化……超级迷信……基督教、图腾崇拜、祖先信仰……某些消失的语言还在使用,比如祖尼语[3]、西班牙语、阿萨巴斯卡语[4]……美洲豹、豪猪还有其他一些残忍的野兽……传染病……神父……毒蜥蜴……”
“不要吓我哦。”
他们终于离开了。伯纳德冲到电话机前。急啊,急啊,他居然花了近三分钟才转接到亥姆霍兹·华生的房间。“我们倒像是已经来到野人中间了,”他抱怨说,“见鬼了,真他妈的无能!”
“要不来一克?”列宁娜建议说。
他拒绝了,他宁愿自己处于愤怒之中。
感谢主福特,电话终于接通了,真的是亥姆霍兹在接电话。他向亥姆霍兹解释了自己客房里淋浴间的问题,亥姆霍兹答应立刻去把香水龙头关掉,但在离开话机之前,亥姆霍兹还是抓紧时间告诉伯纳德,昨天晚上主管当着众人的面说了伯纳德的坏话。
“什么?他想找人顶替我的位置?”伯纳德恼火地说,“他已经决定了?他有没有提到冰岛?你真的听到他说了?主福特啊!冰岛……”他挂掉电话,转过来看着列宁娜,他脸色苍白,神情极其沮丧。
“你怎么了?”她问道。
“怎么了?”他沉重地坐到椅子上,“我要被派到冰岛去了。”
曾经,他时常遐想,倘若遭受巨大的考验(既无索玛也无其他可以依赖,只有自身内在的力量可以依托),或痛苦,或惩罚,他甚至渴望被折磨。早在一周前,在主管先生的办公室,他曾想象自己可以勇敢地抵抗,也可以坚忍地接受苦难,一句怨言都无,主管的威吓其实反令他高兴,使他感觉自己宛如英雄。现在他知道了,这仅仅是因为他不曾认真考虑这些威吓,他本不相信事情会真的发展到那一步,主管先生真的会把威吓付诸行动。而现在,威吓即将成真,伯纳德终于惊恐了,他那幻想的坚忍、他那理论上的勇气,转瞬烟散。
他恨自己。你真是一个蠢货!还想与主管作对!可是为什么不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不公平。再给他一次机会啊,他坚信,他本来就打算采取行动取悦主管的。而现在是冰岛,冰岛啊……
列宁娜摇摇头,引用道:“过去未来令我恶心,一克索玛令我存在当下。”
最终,她说服伯纳德吃了四片索玛。果然,五分钟之后,种子般的过去、果实般的未来皆从头脑中消失,单单那玫瑰色的花朵怒放当下。
门房通知他们,根据监守长的意见,一名保留地护卫已经驾驶飞机过来,正在宾馆天台恭候他们。他们立刻上到天台。护卫有八分之一的黑人血统,身着γ族绿色的制服,向二人致意,并当即背诵起当日上午的行程安排:首先空中鸟瞰十或十二个主要的印第安村庄,然后在玛尔普山谷[5]降落吃午餐,此山谷里的休养所相当不错,山谷之上,玛尔普村子里正是野人庆祝夏日丰收的时候,他们或许能亲眼目睹,因此,在此过夜实在是最佳的方案。
他们上了飞机,十分钟之后,他们越过了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的分界线,地势上下起伏,经过盐碱地、沙漠、森林,飞进紫罗兰遍布的峡谷,飞过峭壁、山峰、桌面一般平整的台地,到处都可见到笔直蔓延的栅栏,无可阻挡,那是人定胜天的象征。栅栏之下,随处皆能看到白骨森森。一具尚未腐烂的尸体已经焦黑,躺在褐色土地上,尸体所在之地招来鹿、牛、美洲狮、箭猪、郊狼,或贪婪的美洲鹫,它们被腐肉的味道吸引,却因过于靠近这致命的栅栏,遭致高压电流之击。贪婪者必受灭顶之灾,这倒像是诗歌里描述的公正审判呢。
“它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身着绿色制服的飞行员指着地上的骨架说道,“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重复了这句话,不觉大笑起来,似乎在与这些被电击而亡的畜生的较量中他取得了某种胜利。
伯纳德也笑了。吃完两克索玛,不知何故,他感觉飞行员的笑话真的很好笑。刚一笑完,他就昏然睡去,在睡眠中一路经过陶斯、特斯阙、南比、皮库瑞丝、婆鸠阙、西亚、奇蒂、拉古纳、阿科马、恩长美萨、祖尼、西波拉、欧荷卡勒真泰[6],醒来时,发现飞机已经着陆,列宁娜拎着手提箱,正走进一间方形的屋子,而身着绿色制服的飞行员正与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说话,咕咕哝哝,不知所云为何。
“玛尔普已到,”当伯纳德从飞机里下来时,飞行员解释说,“这里是休养所,今天下午在印第安村庄里,会有舞蹈表演,这个人会带你去。”于是指着那个一脸阴郁的年轻野人。
“我希望会很有趣,”飞行员撇嘴一笑,“好在这些家伙做什么都很有趣。”说完他就爬进飞机,开动引擎。“我明天过来接你们,记住,”他安慰列宁娜说,“野人其实都很温顺,他们不会伤害你们,毒气弹给了他们足够的教训,他们不敢耍什么花样。”说完他又笑起来,然后启动直升机的螺旋桨,飞机加速,一飞而去。
* * *
[1]让-雅克·哈比布拉,原文Jean-Jacques Habibullah,此处暗指两人。一个是指启蒙时代的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一个是指塔吉克族的阿富汗国王哈比布拉·卡拉卡尼(Habibullah Kalakani),他在位仅九个月。
[2]圣菲,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州府。
[3]祖尼语,居住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西部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所用语言。
[4]阿萨巴斯卡语,北美大陆一系列原住民语言的统称。
[5]玛尔普山谷,位于美国西南部的熔岩区。
[6]上述均为印第安村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