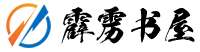这片台地好似一艘大船,稳稳停泊于金黄的尘土构造的海峡之中。峡谷蜿蜒,两岸形势险峻:沿着整个山谷,从这边的岩壁到那边的岩壁,一片一片的绿色倾泻而下,乃是田地和河流。海峡正中的这艘石头大船,船首之上,有一大片裸露的岩层,玛尔普印第安村落即建筑于此。此地住宅挨次从下往上建,每一层楼都比下面一层小,使得那些房子断续相连,好似可以一级一级攀爬,仿佛直插蓝天的金字塔。金字塔下方,还有一些零星分散的低矮的平房,以及十字一样交叉的围墙;村落三面皆是峭壁,峭壁垂落,至底居然还有一大片平地。
他们看见好几条烟柱,因为无风,垂直上升,却终于在半空散尽。
“诡异,好诡异。”列宁娜说。她责备时好用这个词。“我不喜欢这里,也不喜欢这个人。”她指着印第安导游说。这个导游受命要带他们到村庄里去呢,显然,他的感受与列宁娜相比也一般无二,就看他在前面带路,整个后背都表现出敌意。他是阴郁的,而且对两人的来访很是轻蔑。
“此外,”她低声说,“他有一股难闻的味道。”
伯纳德无意否认。
他们便跟着走。
突然,他们感到整个空气似乎都变得充满活力,连带着他们的脉搏也因血液永不疲倦地流动而加速。远远听到上面的玛尔普村庄里,鼓声隆隆作响。他们的双脚感应着这片神秘的土地心跳的节奏,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道路通往一处悬崖的山脚,头顶之上是那巨大的台地,像船体一样高耸,两地相距有三百英尺的距离。
“真希望我们坐飞机过来。”列宁娜说。她抬着头,怨恨地看着岩壁上悬垂着的苍白的岩石立面,“我讨厌步行。而且头上有座山,人却站在山脚,你会变得很渺小。”
在头顶台地巨大的阴影之中,他们继续前行,绕过一处凸起的岩石,他们看到一个山涧,乃是被水流冲刷出来的,山涧旁,乃是一架升降梯。他们朝上面爬。此路非常陡峭,梯子在岩沟两边“之”字形曲折上升。
有时,鼓声的节奏几乎要听不见了,其他时候,鼓声却似乎就在身边奏响。
他们爬到了半山腰,这时一只鹰从他们身边飞过,它如此靠近他们,其翅膀的扇动使他们脸上感到了一阵寒冷。在一处岩石的裂缝中,他们看到了一对白骨。这一切都太诡异,令他们倍感压抑,而印第安导游身上的味道也越来越难闻。终于,他们走出了山涧。满目都是阳光。此时去看那台地,其顶部就像是石头制成的一块甲板。
“就像是碳化T塔。”列宁娜评论道。看见似曾相识的事物实在令人安心,但是她还来不及多欣赏,就听到一阵轻盈的脚步声。他们回头一看,两个印第安人正沿路跑过来。这两个印第安人,从脖子到肚脐都是赤裸的,棕黑色的身体上涂抹着白色的线条(列宁娜后来描述说,“像沥青网球场”),其面部因涂上猩红色、黑色、赭色而显出残忍,黑色的头发则用狐皮和红色的法兰绒布条编成辫子,火鸡羽毛织成的斗篷在肩膀后面飘动,巨大的羽毛王冠在他们头顶俗丽地颠动,伴随着每一步,他们的银手镯、沉重的项链(乃是由骨头和绿松石串成)都在叮当作响。他们跑过来,一言不发,脚下的鹿皮软鞋无声无息。其中一人手持羽毛刷子,另一人远看每只手上都握着三四根很粗的绳子,其中有一根绳子不安地扭动着。突然,列宁娜看清了,那不是绳子,是蛇。
这两人渐渐靠近,他们黑色的双眸看着列宁娜,却似乎又当她不存在。只见扭动的蛇松软地垂下来,像其他的蛇一样。
他们就这样跑过去了。
“我不喜欢这一切,”列宁娜说,“我不喜欢这一切。”
当他们到达村子入口时,她更不高兴了,因为他们的导游把他们扔在门口,自己到村子里打探消息。眼见的是烂泥、堆积的垃圾、尘土、狗、苍蝇。她的脸因厌恶而扭曲,一脸苦相。她拿出手帕遮住了自己的鼻子。
“他们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她义愤填膺地指责道,声音中满是怀疑。(这不可能!)
伯纳德耸耸肩,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无所谓。“无论如何,”他说,“在过去的五六千年里,他们一直就是这样生活。所以,我猜他们早就习惯了。”
“但是,清洁之人才能靠近主福特啊。”她固执地说。
“是的,还有一句呢:文明就是消毒,”伯纳德语带嘲讽,接着他的话又引用了睡眠教材中《初级卫生学》里的格言,“不过,这些人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主福特,他们可不是文明人,所以,讨论他们清洁与否毫无意义……”
“啊,”她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臂,“快看。”
只见一个近乎全裸的印第安人,正从附近一处房子的一楼的阳台沿着梯子往下爬,他的动作缓慢,一个横档一个横档地下降,极其小心。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脸上皱纹深深密布,肤色炭黑,这张衰老的脸就像是一个黑曜石面具。他的牙齿全部掉光了,嘴深深凹陷。唇角边上,两颊处各有几根长长的白色的鬃毛,在黑色的皮肤上微微闪光。他的长头发披散着,一缕缕灰白的发丝挂在他的脸上。他的身体是驼着的,瘦得皮包骨,几乎看不到一丁点肉。他极其缓慢地下了梯子,在每一级横档他都要停一下才敢踏出下一步。
“这个人什么毛病?”列宁娜低声说。她的眼睛因恐惧和惊奇而睁大了。
“不过是年纪大了。”伯纳德回答说,尽量显得平静。其实,他自己也吓得够呛,但是还是努力显出不为所动的态度。
“年纪大?”列宁娜重复着,“但是主管先生年纪也大了,其他许多人年纪也大了,却没有人像这个人这样。”
“那是因为,我们的文明世界不允许人变得这样衰老。我们让人们远离疾病,我们让所有人的内分泌系统始终处于年轻人才有的那种平衡状态,我们不允许人们身体内的镁钙比例低于三十岁时的水平,我们给人们换上年轻的血液,我们确保人们的新陈代谢系统永远活跃。正因如此,我们谁都不会像这个人那样老。或许也有可能,”伯纳德补充说,“在我们的文明世界里,绝大多数人在到达这个老家伙的岁数之前就死去了。我们的人六十岁之前几乎永葆青春,然后,咔嚓!生命就消失了。”
但是列宁娜根本没有在听。她一直看着那个老人,他往下爬,缓慢地,缓慢地。他的脚终于着地,然后慢慢转身。只见他深深凹陷的眼窝里,两只眼睛依然格外明亮。他看着列宁娜,长久地看着,脸上平静,毫不惊讶,似乎她并不存在。然后,缓慢地,这驼背的老人蹒跚着经过他们,不见了。
“可是这太可怕了,”列宁娜低声说,“简直是恐怖。我们不应该来这里的。”她手伸进口袋,寻找着索玛,结果发现,因为疏忽(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她居然把索玛药瓶落在休养所了。伯纳德的口袋里一样空空如也。
列宁娜不得不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直面玛尔普村的种种恐怖。这些可怖的事物频频朝她涌来。
她看见了两个年轻的妇女,正在给她们的孩子喂奶,她的脸立刻通红,便转过脸去。在她的人生中,她从没有见过如此下流的事情。让她感觉更糟糕的是,看到此情此景,伯纳德不仅没有机智地视而不见,相反却公然讨论这胎生的场景,实在是太恶心了。索玛的效力已然衰竭,想到早晨他在旅馆表现出来的软弱,伯纳德感到了羞耻,于是,他刻意表现出强硬、蔑视正统的一面。
“看啊,这是多么温馨亲密的关系啊,”他说,有意用一种粗暴的语气,“如此会造成何等强烈的情感!我常常想,因为没有母亲,一个人到底失去了多少东西啊!列宁娜,也许因为没有机会做母亲,你也损失了好多东西呢!想想看,你坐在那里,怀抱着自己的小宝贝……”
“伯纳德!你怎么敢这样说话!”列宁娜愤怒地叫道。但是,一个患有眼疾和某种皮肤病的老妇人恰好经过,吸引了列宁娜的注意力。
“我们走吧,”她乞求道,“我不喜欢这一切。”
但是就在此时,导游过来了,招手让他们跟上,于是引着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街道前行,街道两旁都是房子。他们拐过一个街角,看见垃圾堆上有一条死狗,一个甲状腺肿大的妇人正忙于在一个小女孩的头发里寻觅虱子。导游停在一架梯子旁,举起手,直指着梯子。他们听从了导游的手语,爬上梯子,穿过门洞,进入一个窄而长的房间,内里黑暗,烟、煮着的油脂、破旧而长期不洗的衣服,氤氲着某种味道。房间另一头,还有一个门洞,穿过门洞,见到一束阳光射进来,响亮的鼓声近在耳边。
他们跨过门槛,来到一个宽阔的阳台,阳台下是村寨的广场,被周边较高的房子围住。此时,广场上挤满了印第安人。满目皆是:鲜艳的毛毯、黑发上的毛羽、闪烁的绿松石、汗津津的黑肤。列宁娜再次用手帕捂住了鼻子。在广场中央开阔之地,有两个圆形的平台,用石头和黏土混筑而成,这两个圆台明显是地下室的屋顶,因为每个圆台的中央,皆有一个天窗,其中各有一架梯子从黑暗的地下伸出来。隐隐能听到地下有长笛演奏的声音传来,却几乎被那持续不断的鼓声所遮蔽。
列宁娜爱那鼓声。闭上眼睛,她听任自己被那温柔重复的鼓声包围,使自己的意识越来越彻底地被鼓声牵引,以致最终世上只有一种东西存在,即是那深沉、脉搏一样跳动的鼓声。这鼓声使她欣慰地联想到在“团结仪式日”和“主福特纪念日”上奏响的合成乐(因二者节奏近乎一样),“咬兮炮兮”,她喃喃自语。
突然爆发出一阵歌声,乃是成百个男性的嗓音,以重金属一样的和声,猛烈地歌叫,忽而又哼唱着几个长长的音符,忽而又是沉默,鼓亦停歇,好似雷霆蓄势之前的安静。然后,尖叫声响起,像马嘶一样,高声汹涌而来,这是女性的嗓音应和了。于是,鼓声重又响起。然后又是男性深沉的歌声,他们以最粗野的声音认证着自己雄性的力量。
诡异吗?是的。这地方就诡异,这音乐也诡异,众人的衣服一般诡异,甲状腺肿大、皮肤病、老人都诡异。但是这表演本身,却毫无诡异可言。
“这场表演让我想起低等种姓搞的社群合唱。”列宁娜告诉伯纳德。
可是一会儿之后,她就不想再将这场演出与“社群合唱”这种无伤大雅的功能联系在一起了。因为,突然之间,从圆形的地下室里爬出来一支鬼怪的队伍,戴着骇人的面具,涂着妖异的色彩,看不出一丝人性。这队伍围绕着广场踩着,跳着,像是跛子的舞蹈,一遍又一遍地转着圈,一边跳,一边唱着歌。转圈的速度越来越快,鼓声也随之变化,节奏越来越快,致使耳朵内像有一股热流在不断冲击。观众们已经开始跟着舞蹈者一起歌唱,声音也越来越大。接着,听到第一个女人尖叫的声音,然后一个又一个女人都开始尖叫起来,仿佛她们就要被人杀死了一样。突然,领舞者离开了舞蹈圈,跑到广场顶头一个木柜子处,打开盖子,拎出两条黑蛇。人群中爆发出尖叫,其他所有舞者于是全部跑到领舞者身边,他们的手皆张开着。领舞者将蛇扔给最先跑过来的舞者,然后伸手到柜子里,拎出越来越多的蛇,有黑的,有棕色的,有花斑的,他把它们全扔了出去。
然后,舞蹈的音乐节奏变化了。舞者们抓着蛇,一圈一圈地旋转。就像蛇一样,他们的膝盖、屁股上下起伏。一圈又一圈。突然,领舞者给出信号,于是,舞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把蛇甩到广场中央。一个老人从地下室爬出来,向蛇撒播玉米粉;另一个地下室天窗处,爬出来一个妇人,抓着一口黑罐,向蛇群中洒水。老人于是举起手,只听万籁俱寂,世界恐惧。鼓声停止,生命似乎走到尽头。老人的手又指向两个通往地下室的天窗,于是,从一个天窗里缓慢地举出一只彩绘的鹰,乃是被地下室里看不见的手所举;从另一个天窗里,则出来一个人的形象,此人赤裸,被钉在十字架上。两幅形象于是立在那里,好似独立支撑,仿佛在观望。老人开始鼓掌,只见一个十八岁左右的男孩从人群中跳出来,除了一块棉质的遮羞白布,他近乎赤裸,这男孩走到老人身边,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头深深弯下。老人在男孩头顶做了一个十字架的手势,然后走开了。于是,这男孩慢慢地,慢慢地围着广场上纠缠成一堆的蛇群步行,他走完了一圈半的时候,从舞者中出来一个高个的男人,此人戴着一张郊狼的面具,手上抓着一条鞭子——是用编织的皮革做的——向男孩走来。
但男孩却无视他的存在,依然自行其道。带着郊狼面具的男人举起他的鞭子,众人屏息期待,许久之后,他迅速抽动,鞭子的尖啸声、抽打在身体之上那响亮却沉闷的回音,流传在人群之中。男孩的身体开始颤抖,但他依然沉默,依然保持方才缓慢、平稳的步伐绕着圈子。于是,带着郊狼面具的男人一鞭又一鞭,每一鞭都令众人先倒吸一口气,然后深深叹息。男孩继续绕着圈子,两圈、三圈、四圈。
血液流淌。
五圈、六圈。
突然,列宁娜捂住自己的脸,开始啜泣。“啊,停住吧,停住吧。”她哭泣着,恳求着。但是鞭子却无情地甩下。第七圈了。突然,男孩步履蹒跚起来,他一言不发,一头栽倒在地。老人弯下腰,用一根很长的白色羽毛碰触男孩的背部,等了一会儿,羽毛变红,此情此景大众都能见到。然后,老人将这羽毛三次在蛇群上方挥过,有几滴血跌落。突然之间,鼓声再次大响,节奏迅疾,仿佛恐怖;随之有人高声呼喊。舞者们冲上前,将蛇捡起,然后跑出广场。男人、女人、孩子,所有的人,皆尾随着舞者们狂奔而去。一分钟之后,整个广场已经空无一人,单单留着那个男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从一处房子里走过来三个老妇人,她们竭力将这男孩抬起,运到房子里去。此时只有鹰和十字架上的男人还在守卫这空荡荡的村庄,然后,或者是因为已经看够这场景,它们皆缓慢下降,退入天窗,终至不见,没入暗黑世界。
列宁娜仍在啜泣。“太可怕了。”她不停地说。无论伯纳德如何安慰,皆属无用。“太可怕了!那是血啊!”她身体在颤抖,“天啊,要是有索玛多好。”
此时,室内深处有脚步的声音。
列宁娜一动不动,单是坐着把脸埋在双手里。她不愿意看周遭,宁愿置身事外。
伯纳德转过了身。
走进阳台的年轻人从穿着来看是一个印第安人。但他梳成小辫的头发却是淡黄色的,他的眼睛则是一种淡蓝色,他的皮肤则是浅白的,但被晒成了古铜色。
“喂好,早好。”这陌生人说,其所用的英语语意无误,但措辞怪异。“你们是文明的,对吗?你们来自‘它世界’,我听说,是从保留地外面进来?”
“你究竟是谁……”伯纳德惊讶地问。
年轻人叹一口气,摇摇头。“一个非常不开心的绅士。”然后指着广场中央的血迹,说道,“你们看见那见鬼的场景了?”他问话时,情绪激动,声音颤抖。
“一克药总比见鬼好,”列宁娜机械地回应道——乃是从双手里发出的声音,“要有索玛多好。”
“本应该我干那事,”年轻人继续说道,“但他们竟不让我做牺牲?为何?我曾经能走个十圈,十二圈,甚至十五圈,帕罗维塔才走了七圈嘛。他们要选我,我身上出的血都要比他多一倍,‘像红色海洋滚滚’[1]。”他甩着手臂,幅度夸张,却很快就沮丧地放下了,“但是,他们就不让我干那事,我肤色他们究竟不喜欢的。总是这个样子。总是。”这年轻人眼眶已经湿润,他感到耻辱,试图走开。
事出突然,列宁娜竟因诧异而忘记缺少索玛这回事了。她挪开手,头一次打量这个年轻人。“你刚才是说,你希望被人鞭打?”她问。
年轻人虽然在远离列宁娜,却还是给出了肯定的示意。“自然,是为了村庄,为了使甘雨降临,玉米丰收,为使普公和耶稣欢悦。而且,我便展示给人看,我可以承受痛苦,连哭都要不得。”此时,他的声音变化,共振感加强,便傲然挺起胸膛,下巴骄傲地扬起,“终于证明我乃是一个男人……哇。”他突然喘了一口气,大张着口,沉默起来。
原来,这是他一生中初次见到一个巧克力色皮肤的女人,还不是狗皮模样;其头发并非赤褐色,也不是自来卷;其表情竟是一种关切(实在惊奇,前所未见!)。列宁娜对他微笑,这男孩漂亮极了,她心想,真的很漂亮。年轻人的脸却迅速红了,他低下眉目,却忍不住抬起来又看她,看她是否仍在对他微笑,但又不得不强迫自己把视线转到广场的一角,装作在看什么东西一样。
伯纳德的问题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你是谁,怎么过来的,什么时候过来的,从哪里来?
年轻人盯着伯纳德的脸(因为他如此热烈地渴盼着看到列宁娜对他微笑,却转而不敢看她一眼),试图解释自己的来历。琳达——他的妈妈(列宁娜听到这个词非常不舒服)——和他在保留地是陌生人,琳达多年以前和一个男人是从“它世界”来到了保留地的,那时他还没有出生,那男人是他的父亲。(听到这里伯纳德竖起了耳朵。)琳达早年有一次在群山里独自漫步,一直往北边走,却滑下一个陡坡,伤了她的脑子。(“继续说啊,继续说。”伯纳德激动地说。)玛尔普村的几个猎人发现了她,把她带回了村子。至于那个男人也就是他的父亲,琳达此后再没有见到过,他的父亲名叫“托马亲”。(正确发音是托马斯,正是主管先生的姓呀。)他一定飞走了,飞到“它世界”去,丢下琳达不管,所以,“托马亲”是一个坏人,无情、反常。
“我就是这样出生在玛尔普,”年轻人说,“就是此地的玛尔普。”他摇了摇头。却是住在村庄边缘一个又小又脏的房子里,这房子与村庄隔着一堆尘土和垃圾。两条饥肠辘辘的狗嗅着门口的垃圾,一副猥琐模样。当他们进入房子时,看到屋内光线暗淡,闻到一股恶臭,苍蝇群飞。
“琳达!”年轻人叫道。
从里屋传来一个非常嘶哑的女性的声音,“来了。”
他们等待着。
地上有几个碗,碗里还有一些剩饭,也许是好几顿剩下来的。
门开了。一个矮胖的白肤金发妇人踏过门槛,站住了,一脸怀疑地看着来访的陌生人,她的嘴大张着。列宁娜嫌恶地发现,这妇人两颗门牙已经掉了,剩下的牙齿,那颜色……她吓得发抖,这简直比刚才所见的老人还要糟糕。她是那么肥。而且她脸上的线条,那么的松弛、发皱。看她下垂的双颊,遍布着紫色的斑点;还有那鼻子上红色的静脉、充血的眼睛;更别提她的脖子了,那脖子啊。还有,还有她裹着头的毯子,又粗糙又肮脏;至于她那用麻袋一样的束腰外衣包裹的是何等的肥乳啊;肚子鼓凸;还有那肥硕的屁股!天啊,糟糕透顶!突然,这造孽般的妇人却口若悬河起来,她伸出双臂,冲向列宁娜。主福特啊!这简直令人反胃,倘在另一种情况下,她必定要恶心了。现在,这妇人竟抱住她,她不得不忍受那鼓凸的肚子、硕大的胸脯。她甚至要亲吻列宁娜!主福特啊!她要来亲吻人!她还流着涎水呢,身上一股馊味,明显从不洗澡,她浑身可都散发着δ族、ε族人的臭味(他们在胚胎瓶中吃多了兽食才有这味道,那明显是酒精的恶臭——现在可以明确了,伯纳德在胚胎瓶中绝对没有泡在酒精里过)。列宁娜立刻逃到旁边。
这时,列宁娜看到,这妇人号啕大哭起来,一张痛苦扭曲的脸正对着她。
“哦,亲爱的,亲爱的人啊。”伴随着啜泣,妇人语若悬流地说起来,“你们知道我有多么高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终于见到了一个文明人的脸孔。还有,体面的衣裳。我还以为今生连一块醋酸丝布都再不能见到了呢!”她轻抚着列宁娜衬衫的衣袖,那指甲却是乌黑的。“啊,还有那仿天鹅绒的短裤,令人羡煞!亲爱的,你可知道,我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衣服,当时我穿着它来,如今它却躺在箱子里。待会儿我拿给你们看,不过,醋酸丝衣服免不了会有太多的破洞。我还有一条白色的裤带很漂亮,但是我要说,你那绿色的摩洛哥皮带更漂亮。……”说着说着,她眼泪流了出来,“我想,约翰告诉过你们了,这么多年我受了多大的苦啊,连一克索玛都没有,只能时不时地喝上一杯龙舌兰,那是珀毗[2]过去常常送我的——他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男孩。可是,喝这种酒,过后会非常难受。真的,龙舌兰酒不好喝,你会因为那股仙人掌味犯恶心的。更何况,喝了之后,第二天你常常感到更加羞愧。一直以来,我都感到羞愧。想想看:我,一个β族人,生了一个孩子!你们试试处在我这样的局面!(仅仅想象这样的场景,就足够让列宁娜颤抖了。)
“但我发誓,这并非我的错。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我可是一直坚持做马尔萨斯避孕操的呀,一直按照程序,一、二、三、四。我发誓,真的一直都按照程序。可我还是怀孕了,而且这里更不可能有流产中心。顺便问一句,流产中心还是在切尔西,对吗?”她问列宁娜,列宁娜点头表示肯定。“啊,那粉红色的漂亮的玻璃塔啊!”可怜的琳达抬起头,闭上眼,心醉神迷地回想记忆中那明亮的建筑。“还有那夜色中的河流,”她喃喃自语,大滴大滴的泪珠从她紧闭的眼睑慢慢流出,“还有乘着夜色从斯托克波吉斯飞回,然后一次热水澡,真空震动按摩机,啊……但是这里……”她深深一呼吸,摇摇头,睁开了眼睛,吸一两口气,擤了擤鼻子,擦在长袍的边缘。列宁娜不知不觉露出厌恶的表情。“啊,我很抱歉,”琳达说道,“我不应该这样的,真的抱歉,但是我没有手帕,还能怎样?过去,这样做也会令我反感。还有那些灰尘,那些肮脏不净的一切。但当印第安人把我带到这里时,我的头部裂了个大口子,你们能想象他们用什么来敷我的伤口吗?是烂泥巴,仅仅是烂泥巴。我告诉他们说,文明就是消毒,还唱给他们儿歌听:雄鸡粘上链球菌啊,右拐跑进班伯里T,有啥稀奇瞧一瞧啊?漂亮浴室外加WC。只当他们是小孩,可是他们当然不理解。他们又怎么可能理解呢?最后,我不得不适应这里。想想看,没有热水,怎么能保持清洁?再看看这些衣物,像这件羊毛衫,用畜生的毛做的,只会越穿越大,再怎么也不能像醋酸丝衣服始终笔挺。衣服开裂了,你还得缝缝补补,可我是一个β族人,过去都是在受精室工作,哪里学过做这种事?这可不是我该做的事。此外,过去我从没必要缝补衣服,衣服有了洞,扔掉就是,立马买新的。扔掉旧衣好于缝缝补补。难道不是吗?缝缝补补实在是反社会的呀。可是这里完全相反,我像是在跟疯子一起生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疯狂的。”
她四处看看,见约翰和伯纳德已经到屋外去了,正在尘土和垃圾中走来走去,却仍然刻意低下声音,欲跟列宁娜推心置腹地说话。她向列宁娜靠过来,列宁娜却身体僵硬地回避了,但她们还是很靠近,以至于琳达口中的酒气都吹动了列宁娜双颊上的汗毛(酒啊,你这罪恶的胚胎液中的毒药啊)。
“比如,”琳达嘶哑地低语道,“就说说他们男女如何在一起吧。疯了,我告诉你,简直是疯了。每个人都属于别人。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吗?”她固执地自问,还扯着列宁娜的袖子。
列宁娜头虽扭到一边,却仍点点头。她长出一口气,又试图再吸进一口清新的空气。
琳达继续说:“然而,这里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只能属于另外一个人。假如照我们正确的方式与男人交往,他们就会认为你邪恶、反社会,他们会恨你、蔑视你。有一次,许多女人跑到我这里来,大吵大闹,因为他们的男人来和我约会。可是,为什么不能约会呢?那时她们全部扑向了我……啊,那实在是太可怕了,我都无法跟你描述。”琳达掩住自己的面庞,双肩颤抖。“这里的女人,她们充满仇恨。她们是疯了,疯了,而且残忍。她们当然不知道世上还有马尔萨斯避孕操、胚胎瓶、倒瓶一说,或类似的事情。所以,他们不停生小孩,就像狗一样——实在是太令人恶心了,我一想到这种事就……啊,主福特啊,主福特,主福特!幸亏约翰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安慰,若没有他,我可怎么过日子啊。可是,一看见男人来找我,他就变得心烦意乱,甚至在他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如此了。有一次,那时他已经长大许多了,他居然想杀死可怜的维乎西瓦——也可能是珀毗吧,仅仅因为我偶尔会跟他们约会。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向约翰解释清楚,文明人男女之间,本来就应该这样相处。我相信,疯狂是可以传染的,而约翰从印第安人那里感染了疯狂,因为他免不了常跟他们在一起鬼混,虽然他们都排挤他、野蛮地对待他,其他男孩可以做的事情,他们也都禁止约翰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倒是个好事,如此一来,我驯化约翰会更容易些,虽然你们想象不到驯化约翰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此外,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我不知道,了解这些事也并非我的职责,我是说,譬如小孩问你直升机如何工作,或者谁创造了宇宙这样的问题,假如你是一个β族人,而且一直在受精室工作,你又从何知道这种问题的答案?你能怎么回答?”
* * *
[1]语见《麦克白》第二幕。按:本书中所有引用莎士比亚的字句,皆出自译者新译,特此说明。
[2]珀毗,原文Popé,此处暗指一位印第安英雄。1680年,为反抗西班牙移民定居,一个名为Popé的印第安原住民在后来的新墨西哥州一带发起了一场起义,将外来殖民者赶出了十二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