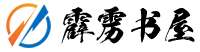三人被带到了元首的书房。γ管家让他们自行待着,说:“元首阁下很快下来。”
亥姆霍兹放声大笑。“这更像是个咖啡派对,哪像是审判?”说着,他坐进那顶级奢靡的充气靠椅。“快活点,伯纳德。”他鼓励伯纳德,因为看见了这位朋友那张愁闷的脸,可是铁青铁青的呢。
可是伯纳德高兴不起来,他一言不发,看都不看亥姆霍兹一眼,便走到房间里那张最不舒服的椅子坐下来,这倒是他精挑细选的,暗暗期望如此一来可以减轻元首的怒火。
野人则在房间里不安地徘徊,他模模糊糊地有那么一点好奇心,一会儿盯着书橱里的书看,一会儿看着录音胶卷,一会儿又看看编号的分类箱里装着的阅读器梭芯。窗下那张桌子上摆放着一本巨书,用柔软的黑色人造皮装订,上面烫金贴着大大的T字。他拿起来,打开一看,乃是《我的一生与工作》,作者是“我主福特”。这书乃是福特知识宣传协会于底特律出版的,他随手翻翻,这里读一句,那里看一段,最后得出结论,这书一点都不好玩。此时,门打开了,西欧常任世界元首脚步轻快地走了进来。
穆斯塔法·蒙德与三人握手,特意与野人打了个招呼。“那么你不太喜欢文明世界,野人先生?”
野人看着他,他本想撒谎、怒号,或者一言不发沉默以对,但是元首那张愉快而富理解力的脸鼓舞他说出真相,直截了当地说吧。“是不喜欢。”说完他摇了摇头。
伯纳德诚惶诚恐。元首会怎么想呢?他现在已经被认定为这人的朋友,而这人竟说他不喜欢文明世界,而且是公然地说,更可怕的是他不跟别人说反而向元首说。这实在太糟糕了。“可是,约翰。”他试图提醒野人。但是元首瞄了他一眼,使他可怜巴巴地沉默了。
“当然,”野人继续承认,“这里有一些事物非常好,比如:空气中的音乐……”
“在我的耳边有时环绕着成千的弦乐之声,有时则是动听的歌声。[1]”
野人的脸因突然的快乐而发亮,“怎么你也读过那本书?”他问元首,“我还以为在英格兰,没有别人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
“几乎没有人,我只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你们清楚,这是严行禁止的,但我既然是法律的制定者,自然可以不遵守,而且还不受惩罚。但是马克思先生,”他加了一句,朝伯纳德看去,“我想你恐怕不可以。”
伯纳德立刻陷入更深的无望与痛苦之中。
“可是为什么要禁止这本书?”野人问道,遇见一个读过莎士比亚的人,使他兴奋已极,暂时忘记了其他事情。
元首耸耸肩,“因为太过时了,这是主要的原因。在这里,旧的东西都没有什么用。”
“即使这些旧东西非常美丽?”
“特别是当它们很美丽的时候,更要禁止。美是会蛊惑人的,所以,我们不愿意人民被旧的东西迷住,我们希望人民喜欢全新的事物。”
“但是这些新事物既蠢又可怕。比如那些电影,明明内容空洞,只有直升机飞来飞去,或者人们可以感受到电影里亲吻的感觉,”他一脸苦相,“不过是山羊和猴子的把戏![2]”仿佛只有引用《奥赛罗》里的词语才能准确描述他的轻蔑与憎恶。
“其实,它们倒是温顺的动物。”元首喃喃地插了一句。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让人们去阅读《奥赛罗》?”
“我已经告诉过你,过时了,此外,人民也看不懂这本书。”
这倒是千真万确。他记起来,当时亥姆霍兹是如何嘲笑《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他顿了顿,继续问道:“那么,类似《奥赛罗》的新书,人们能够看懂的?”
亥姆霍兹突然开口——之前他一直都在沉默:“我们所有人都期待写出这样的书。”
“这样的书你永远写不出来,”元首断然说道,“因为,如果这书真的像《奥赛罗》,就无人能读懂,不管它写多么新的东西。而如果它写新的东西,它也根本不可能像《奥赛罗》。”
“为什么不能?”
“是啊,为什么不能?”亥姆霍兹重复了野人的话。他也忘记了自己身处的是何等糟糕的环境,只有那脸色铁青的伯纳德,因为忧惧尚记得,但大家都忽视了他。“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不像《奥赛罗》描述的世界,制造小汽车必须要有钢铁,写作悲剧怎么能没有社会的动荡呢?但目今的世界是安稳的。人民快乐,要什么有什么,对于得不到的东西,他们也从来不去想。他们富足,他们安全,他们从不生病,他们不必害怕死亡,他们终日愉悦,不知激情与衰老为何物。他们不必被父母所困扰,他们无妻无子无爱人,所以不受强烈的情感摆布。他们被驯化得如此到位,以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忍不住要按照规范的要求。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出问题,那就是索玛,野人先生,就是你以自由的名义抛出窗外的药片。你说自由,野人先生!”元首忽然大笑起来。
“指望δ人知道什么是自由!现在又指望他们去读懂《奥赛罗》!我的好孩子,你可真幼稚!”
野人沉默了一会儿,但仍然固执地坚持说:“不管如何,《奥赛罗》是好的,比那些感官电影好得多。”
“这是当然的,”元首表示同意,“可是为了稳定,我们只能牺牲《奥赛罗》了。在幸福快乐与人们过去常称的高级艺术之间,你必须做出选择。因此,我们牺牲了高级艺术。我们于是拥有了感官电影、芳香乐器。”
“可是它们毫无价值啊。”
“它们自有价值,它们提供许多令人愉悦的感觉。”
“但是它们……它们都是些‘白痴说出的东西’[3]。”
元首又笑了。“你对你的朋友华生可不是那么礼貌,他可是我们最棒的情绪管理员之一……”
“但是他说的很对。”亥姆霍兹沮丧地说,“它们确实是白痴一样的东西,因为无话可说,便胡乱编写……”
“不错。但那也需要极大的独创性,就像你用最少的钢材却制造出了小汽车,或许本来并无一物但却成了充满纯粹感官享受的艺术佳作。”
野人大摇其头。“对我来说,它们就是糟糕。”
“当然很糟糕。真正的幸福快乐,与作为痛苦的过度补偿的那种快乐,两者比较起来,前者是要污秽得多。而且,稳定当然也绝没有动乱那么气势壮观。对抗不幸命运的伟大斗争何等迷人,抵制诱惑的心灵挣扎何等栩栩如生,为了激情与怀疑而颠覆命运又何等如诗如画,身处安逸满足自然是享受不到一点点这样的荣光,要知道,幸福从来都不是宏伟壮阔的。”
野人略一沉默,回复说:“我想你这么说是对的,但你所谓的幸福是要让所有人都像那些孪生子一样吗?”他伸出手挡住眼睛,似乎要抹去那些记忆中的形象:排在医院门厅处的那些一长溜一模一样的侏儒、宾福特单轨电车站旁那些排队的孪生子、围绕在琳达临终时病床边的蛆虫一般的孩童,还有那些攻击他的无穷无尽的同样的脸。他看了看包扎着的左手,浑身发颤。“太可怕了!”
“可是他们多有用啊,我看得出来,你并不喜欢我们的波氏胚胎组,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是建构这个世界的根基。他们是陀螺仪,确保喷气飞机始终飞翔在稳定的轨道上。”他深沉的声音如此洪亮,令人发抖,他的手势像在说明空间、模拟那不可抗拒的飞行器的冲刺。穆斯塔法·蒙德,你的雄辩术已然升级到美妙如合成乐的水平。
“我很好奇,”野人说,“你又是为了什么,非要造出五种人,既然你对那些胚胎瓶可以予取予求,为什么不把所有人都制作为增增α族?”
穆斯塔法·蒙德又笑了,“因为我们都不想被人割喉,我们信仰的是幸福与稳定,每一个成员都是α人的社会却难免动乱、痛苦。一个工厂里全是α人,就是说,他们全部遗传良好,经过驯化能够在限定的范围内自由抉择,并承担责任,而且可以独立为生、互不相关。想想看,会出什么事?”他强调说。
野人努力去想象,但想象不出什么东西。
“那得有多荒谬!一个出自α专用胚胎瓶、经过α驯化的人,倘若要去做ε人——半个白痴——的工作,他们不要发疯吗?即使不发疯,他们也会把所有东西都砸烂。α人能彻底社会化,但前提是他们只能干α人的工作。而ε人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也只有ε人自己能承担,因为对ε人来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其实不叫贡献,仅仅是他们接受驯化后所适应的人生之路,他们可以顺顺当当地干那些事。所有人的命运都已经规划好了,他们情不自禁要走规定好的人生之路。即使脱离胚胎瓶成人,他们其实依然在一个瓶中,这个瓶子无影无形,却把所有人的命运固化,与他们的婴儿期并无区别。当然,我们每个人,”元首沉思着,继续说道,“也一样在这个瓶子中度过我们的一生。但如果碰巧我们是α人,我们的瓶子相对而言会更大些,所以,如果我们被放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时,我们会感到极大的痛苦。将高等级种姓的代用香槟酒倒进低等级种姓的瓶子里也是绝不可以的,单单从理论上看,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而在现实当中,这一道理也得到了验证。塞浦路斯实验的结果是极有说服力的。”
“什么塞浦路斯实验?”
穆斯塔法·蒙德微微一笑,说道:“那个实验啊,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重新装瓶实验’,当时是福特纪元473年,元首们决定,清除塞浦路斯岛上所有的居民之后,往岛上移民,当时是精心挑选的一批α人,总数达到两万两千人,提供给他们所有的农业、工业设备,并允许他们自力更生。这一实验的结果完全验证了先前的理论预测:土地荒芜无人照顾,所有工厂悉数罢工,法律形同摆设,命令无人执行;所有被派遣去做低级工作的人挖空心思要获得高级工作,而占据了高级工作位置的人,则竭尽全力要保留自己的位置。于是,六年之内,最残酷的内战爆发了,两万两千人中死去一万九千人,剩余的三千人一致恳请元首们重新管理该岛。元首们同意了。这就是世界上唯一一次由单纯的α人组成的社会,结局不过如此。”
野人长叹一口气。
穆斯塔法·蒙德又说道:“适度人口的设置,是按照冰山的模型来做的,冰山是九分之八体积在水里,只有九分之一体积在水面。而α人,只能占总人口的九分之一。”
“可是那些生活于水下的人,他们会幸福吗?”
“他们倒是比生活在水面上的人幸福哩。比如,他们就比你这两个朋友幸福得多。”
“尽管他们要做各种粗笨的活计?”
“粗笨?他们可不这样认为。相反,他们喜欢这些工作。工作量很轻,就像儿童游戏那么简单。大脑和肌肉都不会有任何的紧张感。要知道,他们只有七个半小时轻松不累的工作,然后就能享受定量的索玛,参加运动,还可以不受限制地交配、观看感官电影。他们还能要求更多吗?也许,他们还会要求压缩工作时间,这个我们肯定能满足,从技术上讲,把低种姓的工作时间减为一天三四个小时,实在是简单至极的事情。但是他们会因此而更开心吗?不,他们不会的。一个半世纪多以前,也曾做过一个实验。当时,整个爱尔兰岛定为一天四小时工作制,你们想得到结果是什么吗?结果是动乱、索玛用量的激增,这就是实验的结果!由此可见,多出来的三个半小时空闲时间绝不能给他们增加幸福感,反而使他们非要再来一个索玛假期。发明局其实有了节省劳动时间的方案,有好几千种,”穆斯塔法·蒙德做了一个表示很多的手势,“但为什么我们不实施某个方案呢?因为我们完全是为劳动者们考虑,如果给他们更多些空余时间,简直就是折磨他们,这不是太残忍了吗?农业也是如此。假如我们想,我们可以人工合成所有粮食,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宁愿让三分之一的人在土地上劳动,这也是为了他们考虑,因为耕种收获粮食所花劳动时间要远远比工厂里合成粮食花的劳动时间多多了。此外,我们还要考虑稳定问题,我们不希望任何变革,任何一个变革对稳定的社会都是一个威胁,正因如此,我们在采用新发明时非常非常谨慎。纯科学领域的任何一个发现,都具有潜在的颠覆危险,因此,即使科学本身,我们有时也要视其为一个可能的敌人。不错,科学也是敌人。”
科学?野人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这个单词。但是这单词所指为何,他就说不清楚了。莎士比亚和村子里那个老人从未提及过这个词,琳达也只是给过他一些很模糊的暗示,比如,科学是制造直升机的东西,科学是会让你嘲笑“玉米舞蹈”的东西,科学是让你青春永驻的东西。他拼命想要理解元首的意思。
元首继续说道:“是的,为了社会稳定,科学也是要被牺牲掉的一个词。当然,艺术这个词与幸福是水火不容的,科学这个词也好不到哪里去。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锁住它的手脚,封住它的口。”
“你说什么?”亥姆霍兹大惊失色,“可是我们不总是说科学就是一切吗?我们在睡梦中已经听滥了这句话。”
“从十三岁到十七岁,一周三次重复。”伯纳德突然插嘴说。
“而且我们还在学院里对科学进行大肆宣传……”
“不错,可是你们宣传的是什么科学呢?”穆斯塔法·蒙德挖苦说,“你们从没有经过科学的训练,所以你们判断不了什么是科学。我原本是个不错的物理学家,我能看出来,你们所谓的科学顶多是烹饪书的水平——不过是关于烹饪的陈词滥调,不准人质疑,除了厨师长同意的菜谱,不允许任意添加新菜。现在,我就是那个厨师长。但是我却曾经是厨房里一个很年轻的打下手的人,我会质疑,那时我甚至开始打理自己的菜谱了,会有新奇的菜、以前禁止的菜端上桌子——实际上,这些倒可以说是真正的科学哩。”说完,他沉默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亥姆霍兹·华生问道。
元首叹了一口气,“年轻人,就像你们即将遭遇的事情一样,我当时也差点被发配到一个岛上去。”
这话一出来,伯纳德深受刺激,举止狂乱失态。“要把我送到岛上去?”他跳起来,跑到元首面前,站在那里比划手势,“你不能发配我,我啥都没有做,是他们做的。我发誓,是他们做的。”他控诉着,把手指向亥姆霍兹和野人,“啊,求你了,不要把我送到冰岛,我保证,我一定按规定来做,再给我一个机会吧。”他的眼泪哗啦哗啦流淌起来。“我告诉你了,都是他们的错,”他啜泣着说,“我不要去冰岛。啊,求你了,元首阁下,求你了……”
一阵怯弱之情陡然发作,伯纳德扑的一下跪在元首面前,穆斯塔法·蒙德试图让他站起来,但是伯纳德却固执地保持着奴颜婢膝的姿态,语若悬河地恳求着。到最后,穆斯塔法·蒙德只得打铃叫第四秘书来。
“找三个人过来,”他命令道,“把马克思先生送到一间卧室去。给他喷点索玛喷雾,把他抬上床,让他一个人休息吧。”
第四秘书退出,回来时果然带了三名穿绿色制服的孪生男仆。伯纳德叫着、啜泣着,却还是被带了出去。
“他还以为自己将要被割喉呢,”当门关上后,元首说道,“其实,他要是有一丁点的意识,他就会明白,对他的惩罚不过是个奖励。他是被发配到岛上去了,那也就意味着,他将在那个发配之地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最有趣的男男女女。这些人,因各种原因,导致个体意识过于发达,已经不能适应社群生活。他们对正统的秩序不满,他们形成独立的思想。一言以蔽之,他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华生先生,其实我相当嫉妒你呢。”
亥姆霍兹笑起来,“那么你为何不到某个岛上去?”
“因为到最后,我更喜欢这里,”元首回答说,“当年我有两个选择,一是被发配到一个岛上去,在那里,我可以继续我的纯科学研究;二是被选进元首理事会,有机会论资排辈当上真正的元首。我选择了后者,从此放弃了科学。”他又沉默了会,然后说道:“有时,我非常怀念我的科学。幸福是个残酷的主人,尤其这个幸福还是属于别人的。如果一个人没有驯化到能毫无保留地接受幸福的指令,那么幸福就是一个比真理残酷更多的主人。”他叹了一口气,又一次沉默,忽而改成更轻快的语调,“不过,责任就是责任。既然做出选择,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对真理感兴趣,我喜欢科学,但真理是一个威胁,科学则危害着社会——虽然它同时也是给社会造福的。因为科学,整个历史达到了空前的稳定,相比较而言,汉唐盛世也是极其不稳定的,连原始母系社会都不如我们现在这般稳定呢。我再说一遍,我们感谢科学。但是我们绝不容许科学破坏它所造福的绝佳世界,正因如此,我们小心谨慎地限制着科学研究的范围,而我当初差点就是因越过这个范围而被发配到岛上去的。除了应付最紧急的难题,我们不允许做其他科学研究。所有其他的探索,我们孜孜不倦地予以否决。”
歇了一小会,他继续说道:“其实,在我主福特生活的年代,人们写了一些关于科学进步的文字,读读这些东西,倒是能满足人的好奇心呢。那时的人们似乎认为,科学可以随意发展,不用关心其他事情,知识最为可贵,真理则是最高价值,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说实话,从那时开始,观念就已经开始变化。我主福特为使人们转变观念,更注重舒适与幸福,而不是真理与美,付出极大努力。机器化大生产也要求这一转变,因为普遍的幸福感推动着社会车轮稳定运转,真理和美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当然,当大众掌握了政权,社会就更关注幸福,而不是真理和美。然而,即使政权已经更迭,可是科学的研究仍然无限制,而有些人也依然大肆讨论真理与美,似乎它们倒是最宝贵的。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九年战争,这场战争彻底扭转了人们的观念。当炭疽炸弹在你周围四处开花,高谈什么真理、美、知识有什么意义吗?九年战争之后,社会开始控制科学。从那时开始,人们甚至开始控制自己的食欲。控制一切,为了过上安稳的生活。从此以后,我们一直都在加强控制。当然,对真理来说,这绝非什么好事情,但对幸福来说,这却再好不过了。你要有所得,必定有所失。为了幸福,必须付出一些代价。华生先生,你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人,原因就在于你恰好对美太过喜欢。而我,则是对真理太过喜欢,因此我过去也付出了代价。”
野人在长久的沉默之后,此时说话了:“但是你根本就没有被发配到岛上去。”
元首微微一笑。“这就是我付出的代价,当我选择为幸福效劳——我是说为别人的幸福,不是我自己的幸福。幸运的是,”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全世界有这么多岛屿,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可怎么办是好?我猜,或许是把你们这些人全部关进毒气室。顺便说一下,华生先生,你喜欢热带气候吗?比如,马克萨斯群岛[4]如何?萨摩亚呢?或者某些更凉爽的地方?”
亥姆霍兹从充气椅子上站起来。“我宁愿去一个气候极差的地方,”他回答说,“气候越差,越有利于一个人写出好作品。如果那里有一些暴风雨……”
元首点头表示赞许。“华生先生,我欣赏你的精神。实际上我真的非常喜欢。虽然从官方的角度我必须否定你。”他又是微微一笑,“去福克兰群岛[5]如何?”
“可以,”亥姆霍兹说,“现在,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去看看可怜的伯纳德情况如何了。”
* * *
[1]语见《暴风雨》第三幕。
[2]语见《奥赛罗》第四幕,奥赛罗的咒骂之语。
[3]语见《麦克白》第五幕。
[4]马克萨斯群岛,南太平洋群岛,位于澳大利亚和美洲的中间。
[5]福克兰群岛,英国、阿根廷争议领土,位于阿根廷南端以东的南大西洋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