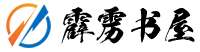外面,在尘土与垃圾之间(现在这地方已经聚集了四条狗),伯纳德和约翰正缓慢地散步,来来回回。
“对我来说,明白这里的一切,然后重新认识世界,实在是太难了。仿佛我们两个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星球上,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胎生妈妈、所有的灰尘,还有神灵、衰老、疾病……”伯纳德说着,摇摇头,“这几乎令人无法相信,除非你解释给我听,否则我永远都不会明白。”
“解释什么?”
“就是这里。”伯纳德指着村子说。“还有那里。”他又指向了村庄外围这间小屋,“以及这里全部的一切,包括你的生活。”
“可是你到底要我说什么是好?”
“从头开始,越早越好,从你能记事开始吧。”
“从我能记事开始?”约翰皱起眉头。他们沉默了好长一会儿。
天气很热。他们吃了太多的墨西哥玉米饼和甜玉米。琳达说:“到这里来,躺下,宝贝。”他们在那张大床上一起躺下。“唱歌吧。”于是琳达就唱起,她唱的是“雄鸡粘上链球菌啊,右拐跑进班伯里T……”和“再见瘦瘦的小宝贝,待会你就要被倒瓶……”两首儿歌。她的声音逐渐降低,低下去,低下去……
突然有响亮的说话声,他吃惊地醒来一看,只见一个男人正在对琳达说话,而琳达正在大笑。只见琳达把毯子往上拉,都到了下巴,那男人却又把毯子扯下来。男人的头发梳成两条辫子,就像两条黑色的绳子,胳膊上戴着一根漂亮的银手镯,手镯内部镶嵌着蓝色的宝石。他喜欢那手镯,可是他仍然被吓坏了。他钻进琳达的怀中,遮住了自己的脸,琳达拍拍他,使他感到安全些了。他听到琳达用那种他不能清楚领会的说话方式对男人说:“约翰在这里,咱们先不做。”男人看着他,又看看琳达,用温柔的声音说了几句话。琳达说:“不行。”但是男人弯腰伏在床上,直直盯着他,男人的脸很大,令人讨厌,黑色的发辫碰到了毯子。“不行。”琳达再次说,他感到她抱他抱得更紧了。
“不行,不行!”但是男人抓住了他一只手臂,他感到生疼,他尖叫起来。男人又抓住他另外一只手臂,将他拎了起来,琳达那时仍然抱着他,仍然在说:“不行,不行。”男人说了些什么,话简短,充满怒气,突然,琳达的手离开了他。“琳达,琳达。”他踢着脚,扭动着。但是男人把他拎到大门边,开了门,把他放在另一个房间的地上,走开,关上门,任他一个人在黑暗中。他爬起来跑到门口,踮起脚尖勉强够着那粗大的门闩,他把门闩抬起,使劲推,不料门却打不开。“琳达。”他叫道。但是她不吱声。
他还记得有一个巨大的房间,很黑暗,屋内有巨大的木头制作的什么东西,上面绑着许多根绳子。许多妇人站在旁边,琳达说,她们正在纺织毛毯。琳达让他坐在角落里,与其他孩子一起玩,她则去帮助那些妇人。他与那些小男孩玩了很长时间,突然,人们开始大声说话,只见妇女们推搡着琳达,琳达则在哭泣。琳达朝门外走去,他就跟在后面跑。他问琳达,为什么她们那么生气。“因为我打碎了一个东西,”她回答,“可我又怎么知道该怎么做编织,这是野人才做的事情啊。”他问琳达,野人是什么。当他们回到家,珀毗正在门口等着,他们三人一起进了屋子。
珀毗带来一个大葫芦,里面似乎装满了水,其实并不是水,而是某种难闻的液体,烧灼双唇,使人咳嗽。琳达喝了些,珀毗也喝了些。琳达便大笑起来,说话的声音都响亮了。然后琳达和珀毗一起进了琳达的卧室。珀毗离开之后,他进到琳达的房间,那时琳达正酣睡,他叫不醒她。
珀毗时常过来。珀毗说,葫芦中装着的是龙舌兰;可是琳达却说不是,认为应该叫索玛,虽然喝了之后会让人难受。
他憎恶珀毗。他憎恶所有来找琳达的男人。
他仍然记得,有一天下午,天气很冷,山顶上可以见到积雪,他与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过后回家,却听到卧室中有愤怒的声音。那是妇女们在喊叫,她们说的话他一句也不懂,但知道那是极其可怕的语言。突然,哗啦一声响,什么东西翻倒在地,他听见众人快速走动的声音,然后又是哗啦一声响,接着传出一个声音,像是有人在踢打骡子,只是没有击中骨头那种清脆的质地。他听到了琳达的叫声。“啊,不要,不要,不要啊!”他冲了进去,见到三个披着黑色毛毯的妇人,琳达躺在床上。其中一个妇人抓住琳达的手腕;另一个妇人横坐在琳达的腿上,确保琳达脚不能乱踢;剩下一个妇人挥舞着鞭子,抽打着琳达。一次,两次,三次。每次被打,琳达都要尖叫一声。
他哭了,用力撕扯着挥舞鞭子的妇人的衣摆。“求求你,求求你。”但她另一只空闲的手把他推到了一边去。鞭子又落下来了,琳达再次尖叫了。他双手抓住那妇人宽大的褐色手掌,用尽全身力气咬了下去,那妇人大叫一声,挣脱了他的双手,然后狠狠地把他推倒在地。他躺在地上,那妇人竟用鞭子抽打了他三下,那种痛苦,比他曾经承受过的所有痛苦(比如被火灼伤)还要重得多。鞭子又嗖嗖地响起,落下,这次,轮到琳达继续尖叫了。
“琳达,到底为什么,她们要伤害你?”当晚,他问琳达。那时他哭着,因为鞭子抽打在背上,那红红的伤痕仍在深深作痛,也因为人们行为如野兽、世道不公平,他一个小小的男孩,根本无力反抗。琳达也在哭泣。她是成年人了,可是她没有强壮到可以抵抗三个妇人,这对她也是不公平的。
“琳达,到底为什么,她们要伤害你?”
“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模糊,因为她那时面朝下躺着,脸埋在枕头里。“她们说,那些男人是她们自家的男人。”她继续说着,却根本不像是在跟他说话,而是在跟她身体内的某个人说话,她说了许多,他却听不懂,最后,她痛哭起来,他从没听过她如此大声地哭泣。
“啊,不要哭了,琳达。不要哭了。”
他靠着她的身体,手臂搂着她的脖子。琳达叫起来:“啊,小心,我的肩膀!啊!”她推开他,非常用力。他的头一下子撞到了墙上。“小蠢货!”她吼道,突然,她开始扇他的脸,一次,一次,又一次……
“琳达,”他哭叫着,“啊,我的母亲,不要打我!”
“我不是你母亲,我不想做你的母亲。”
“因为你,我变成了一个野人,”她吼叫着,“随身跟着你这么一个小畜生……如果不是你,我早就到巡视员那里,也就可以远离这里。可是我走不了,因为有你这个小孩子。我不能承担着这样大的羞辱回到文明的世界里。”
他看出来,她作势又要打他,便举手保护自己的脸。
“啊,不要啊,琳达,不要再打我了呀。”
“小畜生!”她掰下他的手臂,他的脸露出来。
“琳达,不要啊。”他闭上了眼睛,知道琳达要打他了。
但是她没有打他。一会儿之后,他睁开眼睛,发现琳达正看着他。他试着朝她微笑。突然,她伸开双手,拥抱了他,然后一遍又一遍地亲吻他。
有一段时间,是几天吧,琳达一直不能起床。她躺在床上,满心忧伤;要不就喝珀毗带来的那东西,然后就大笑起来,于是睡着了;有时她也会呕吐。她常常忘记给他洗澡,除了冰冷的玉米饼,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他仍然记得她第一次发现他头发里那些小虫子时,她是如何地尖叫,不停地尖叫。
他们在一起最快乐的时光,是琳达告诉他有关“它世界”的事情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想飞哪就飞哪?”
“是的。想飞哪就飞哪。”然后她就告诉他,那个世界里,音乐多么美妙,它们从一个盒子里跑出来;所有的游戏都很精彩;食物味美,饮料可口;朝墙上按一个小物件,光就出来了;那些画,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听,可以触摸到真实的物体,还散发芳香;还有个小箱子,能制造醇香的气味;还有一幢幢高楼大厦,有粉色的,绿色的,蓝色的,银色的,高如山峰;所有人都幸福生活着,从来都没有人会伤心、愤怒;在那里,每个人都属于别人;还有一个箱子,在箱子里可以看到、听到在世界的另一头发生的事情;小宝贝们则生活在迷人而干净的瓶子中。在那个世界里,一切皆清洁,绝没有肮脏的味道,也绝无灰尘,人们从不孤单,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有点像玛尔普村夏日的歌舞盛会,但是更幸福,那种幸福的感觉每一天每一天都弥漫在人们心中……
他总是认真听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有时,当他和其他孩子玩得太过,有些疲惫时,村里就有一个老人,很愿意和他们说话,他说话的方式跟琳达完全不一样。他告诉他们,曾经存在过伟大的世界变幻者;曾经有过“左手”、“右手”以及“湿”、“干”之间漫长的争斗;曾经有一位阿威纳威罗纳,他在黑夜中沉思,遂造成一场巨大的雾,从这雾中,他造出全世界;曾经地母和天父逍遥于天地之间;曾经有一位阿艾羽他,还有一位玛赛乐玛,他们是战争与希望双胞胎;还有普公和耶稣两位神者;还有圣母玛利亚以及艾灿阿特蕾——她令自己脱胎新生;还有拉古纳一地的黑石,神鹰,以及阿科玛的圣母。[1]这些奇怪的故事以特别的语言讲述,他并不能全懂,但他却感到极其美妙。当他躺在床上,他忍不住想及天堂、伦敦、阿科玛的圣母,还有装在瓶子里一排一排的婴儿、飞升的耶稣、飞升的琳达,以及世界孵化场的主管和阿威纳威罗纳。
许多男人都来见琳达。其他男孩开始对他戳戳点点。用他们那种陌生而奇怪的语言,他们说琳达是个坏人,用一些他不能理解的诨号称呼琳达,虽然他知道这些诨号都没什么好意。有一天,他们唱一首歌,歌里描述的就是琳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他就朝他们扔石子。他们反击,其中一颗锋利的石子割破了他的面颊,血流不止。
琳达还教他读书。拿着一根木炭,她在墙上画画,比如一只坐着的小动物,瓶子里的一个婴儿;她还会写一些字母给他看。他记得那些句子,比如“猫在垫子上”,“小孩在盆里”。他学得又快又轻松。当他认得她写在墙上的所有单词的时候,琳达打开了她那个巨大的木箱子,拨开她那些从来不穿但颜色鲜红的长裤,从箱子下面找出了一本书,很薄、很小。他见过这本书,琳达以前常常说,“等你更大些,你就可以读它了。”终于到了他长大一些的时候了,他可以读书了,他感到骄傲。但是琳达说:“恐怕你不会认为这书很有趣,可我也就只有这本了。”她叹息了一声,继续说,“真希望你能看到在伦敦,我过去用的那种阅读器,是多么神奇啊!”
“胚胎驯化的化学法与细菌法”、“β族胚胎商店员工实用说明”,单单这些标题,就让他读了一刻钟时间。他把书扔在地上,“烂书,烂书!”他一边说,一边哭起来。
男孩们继续唱有关琳达的歌,那歌实在令人难堪。有时,他们则因为他衣衫褴褛而嘲笑他,因为他把衣服撕破,琳达却不知道如何缝补。在“它世界”,琳达解释说,衣服有了洞,人们就把它们扔掉,去买新的。“破布,破布!”男孩们时常对着他高声喊叫。“但是,我可以阅读,”他自言自语,“而他们不会,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阅读。”当他认真思考自己会阅读这件事时,装作不在乎男孩们的嘲笑就变得非常容易了。他于是向琳达要那本书。
男孩们越是对他戳戳点点,越是对他唱有关琳达的歌曲,他就越是刻苦阅读。很快,他能够熟练阅读书上所有的字词,即使最长的那些。可是,这些字词意思何在?他问琳达,但是即使她能解释,他还是搞不清楚字词真实的意思,更何况通常情况下,琳达根本就不会解释。
“化学品是什么东西?”有一次,他问道。
“化学品啊,就是镁盐,或者保持δ、ε族人矮小迟缓的酒精,或者骨骼生长所用的碳酸钙,总之,所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可是,琳达,你如何生产化学品呢?或者这些化学品是从其他什么地方产生的?”
“这个啊,我不清楚。你只是从瓶子里把它们挑出来,瓶子一空,就跑到化学品商店买来更多。我猜,恐怕是化学品商店里的人制造了它们。也有可能是工厂在给化学品商店供应。但我不清楚。我从来都没碰过化学。我的工作仅仅涉及胚胎。”
在其他问题上,琳达的回答也大致如此,她似乎什么也不清楚。而村里那个老人,相反倒能回答许多问题,还头头是道的样子。
“男人的种子,万物的种子,太阳的种子,大地的种子,天空的种子,凡此一切,都是阿威纳威罗纳从大雾中创造的。需知世界存在四个子宫,阿威纳威罗纳则把种子放在最下面那一层子宫中。慢慢地,慢慢地,种子开始生长……”
一天(约翰估摸了下,这一天极可能就在他刚过完十二岁生日之后),他回到家,发现一本书躺在卧室的地板上,这书他从未见过。这是一本很厚的书,看起来年代久远了,老鼠将装订线都咬坏了,一些页面松散了、揉皱了。他捡起来一看,书名页上写着《威廉·莎士比亚全集》。
琳达躺在床上,就着一个杯子啜饮着令人憎恶的发臭的龙舌兰。“这是珀毗带过来的,”琳达说,她的声音嘶哑、变粗,像是另外一个人在说话一般,“原来躺在羚羊基瓦会堂[2]的一个柜子里,据说有数百年历史了,我觉得恐怕是真的,因为我翻开来看过,书里面写的似乎都是些胡言乱语,是野蛮时代的作品。尽管如此,用它来练习下你的阅读能力,倒很是不错。”她最后喝了一口,然后将杯子放在床旁边的地板上,身子翻到另一边,打了一两次嗝,于是便睡着了。
他随意翻开那本书。
“不,你去,缱绻于那破床之上,
在臭汗中流连,
为腐烂、甜言蜜语熏陶,
好比在下流的猪圈,
做爱缠绵。”[3]
这些陌生的字句在他头脑里翻腾,轰隆作响,仿佛会言会语的雷霆响彻;又譬如盛夏歌舞盛会中的鼓声——只是这鼓声不曾言语;又好比众人齐唱玉米颂,何等甜美,何等甜美,你忍不住泪下;又似乎老米辞玛对着他的羽毛、雕花权杖、骨片、石头念神奇的咒语——kiathla tsilu silokwe silokwe silokwe.Kiai silu silu,tsithl——但这些字句却又比米辞玛的咒语更胜一筹,因为它意味更深,因为它在和他对话,声音动听迷人,虽然他半懂不懂。这字句等同于极其美妙的咒语,描绘着琳达,描绘琳达鼾声四起的睡眠,描绘床边地上的空杯子,描绘琳达和珀毗,是的,琳达和珀毗。
他越来越憎恨珀毗。一个人虽然总是对人微笑,却也可以是一个恶棍:“冷酷、奸诈、淫荡、无良,一个纯粹的恶棍。[4]”这些词准确描述的是什么?他依旧是半懂不懂。但是这些词语的魔力强大,一直在他脑袋里轰鸣,以至于他莫名其妙地感觉,似乎他过去从来没有真正仇恨过珀毗,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能力去描述他究竟是如何仇恨珀毗的。
但是现在他有了这些词语,它们就像鼓声、歌声、咒语,不仅这些词语,还有这些词语描述的那个陌生又陌生的故事(他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故事,可这故事依然是那么的迷人),它们给了他仇恨珀毗的理由,使他的恨意更加真实,它们甚至令珀毗本人的形象也变得更加真实自然。
一天,在外面玩耍够之后他回到家。内屋的门开着,他看到琳达和珀毗躺在一起,熟睡着。一边是纯白的琳达,一边是几乎全黑的珀毗。琳达枕着他一只胳膊,他另一只手抱着琳达的胸脯,他那长长的发辫中有一条垂落在琳达的喉咙处,仿佛一条黑色的蛇意欲扼死她。珀毗的葫芦,还有一只杯子,放在床边的地上。琳达在打鼾。
他的胸膛突然空洞洞的,似乎他的心在离他远去。他的内在变得空虚,空虚而寒冷,他犯恶心,他头晕眼花摇摇欲倒。他靠在墙上,支住自己的身体。冷酷、奸诈、淫荡……好像鼓声,好像众人颂扬玉米,好像咒语,这些词语在他的脑子里不停重复。他本是冰冷,忽然变得炽热,血液冲向双颊使他双颊火热,于是,在他眼前,房屋飘浮起来、暗黑起来。他咬牙切齿。“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他一遍遍说着。突然间,他似乎听到了更多的句子。
“当他醉醺醺沉入黑甜之乡,
或者,当他沉溺于愤怒,
或者,当他在床上享受着乱伦之乐……”[5]
这魔咒仿佛为他而设,它自我言说,自我解惑,并发出命令。他退出房间,到了外屋。“当他醉醺醺沉入黑甜之乡……”壁炉旁的地上有一把切肉刀,他捡起来,踮着脚尖再次向内屋走去。“当他醉醺醺沉入黑甜之乡……”他跑过内屋,将刀刺上去——啊,那喷涌之血!他再次刺向珀毗,珀毗挣扎着从睡梦中醒来,他举起刀又一次刺下去,却发现手腕被人捏住、扭曲,他一动不能动,他陷入了困境,然后他看见了珀毗的双眸,黑色的眼珠,小小的眼眶,靠着他很近,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他不敢回视。
珀毗的左肩上有两处伤口。琳达哭起来:“啊呀,看看那些血!看看那些血!”她从来不敢见到血。珀毗抬起另一只手,他想,珀毗是要揍他。他身体僵硬了,不得不承受对方的拳头。但是珀毗只是抓牢他的下巴,迫使他转过脸,于是他不得不再次直视珀毗的眼睛——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是几个小时吧。突然,他再也忍受不了,他哭了。珀毗却大笑起来。“走吧,走吧,”珀毗用的是那种印第安人的语词,“我勇敢的阿艾羽他。”他于是跑进另一个房间,羞愧于自己的泪水。
“你十五岁了,”老米辞玛说,用印第安的语词,“现在,我要教会你制作陶器。”
于是,他们坐在河畔,开始一起忙碌。
“首先,”米辞玛说,拿起一块湿黏土放在双手之间,“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月亮。”只见老人将这块黏土捏出一个圆盘来,并将边缘往上捏挤,只见那月亮忽而变作一个浅浅的茶杯。
他模仿着老人精细的动作。很慢,很不熟练。
“先是月亮,再是茶杯,现在我们做一条蛇。”米辞玛将另一块黏土捏成柔软、细长的圆柱体,又扭出一个圆圈,粘在茶杯的边缘。“然后再做一条蛇,再做一条,又一条。”
米辞玛又做水罐,一圈又一圈,黏土在他手下旋转,然后水罐的边缘竖起来了,底部该细的地方细,中间该凸的地方凸,再往上又细了些,一直捏出水罐的颈子。米辞玛又捏又拍,又敲又刮,终于,玛尔普村常见的水罐立起来了,只不过它是乳白色的,而不是村里常见的那种黑色,那水罐依然柔软可触呢。
至于他做的那个,纯然就是米辞玛拙劣的模仿品,也立在旁边。对比这两个水罐,他忍不住笑了。
“但是我的下一个作品一定会更棒。”他说,然后着手润湿另一块黏土。
塑形、结构、感觉手指获得技能与力量,这一切给予他格外的快乐。“A,B,C,维生素D。”他一边忙碌,一边哼着歌。
“脂肪存在于肝脏,鳕鱼存在于大海。”米辞玛也唱起来,那是一首关于猎熊的歌曲。
他们终日忙碌,日复一日,他满身心都觉到一种紧张、投入的幸福感。
“下一个冬天,”老米辞玛说,“我要教你制作弓。”
他在门外站了好久,终于,屋内的仪式结束,门打开了,众人出来。科斯鲁最先出来,其右手伸出来,却握得紧紧的,仿佛手中护着某件珍贵的珠宝。卡其美随后出来,她的手一样握紧着伸出。二人沉默前行,在其身后,同样沉默行进的是一支老年人的队伍,还有就是两个年轻人的兄弟姐妹或堂表兄弟姐妹。
他们走出玛尔普村,穿过台地,在悬崖边众人停步,共同面对朝阳。科斯鲁张开手,只见一撮白色的玉米粉在他手掌上面,他朝玉米粉上吹一口气,念念有词,然后将玉米粉挥洒出去,好比一手洁白的尘雾飘向太阳。卡其美照样施为。然后卡其美的父亲走到人前,手拿一根装饰着羽毛的祈祷杖,做起了冗长的祷告,随后将祈祷杖扔出去,像是要追逐玉米粉而去。
“仪式了结,”老米辞玛大声说道,“二人终于结合。”
“要我说,”当他和母亲离开时,琳达说道,“就这么点小事,却闹出这么大动静。在文明的国家,当一个男孩想要一个女孩,他只需要……等等,约翰,你要到哪里去?”
他没有理睬她的呼唤,而是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他感觉自由自在的地方。
仪式了结。老米辞玛的话不断回响在他的脑海。结束了,结束了……在寂静中,满怀虔诚,远离人群,他曾热烈、绝望、无可救药地爱过卡其美,而现在,一切了结。那时,他才十六岁。
圆月的时候,在羚羊基瓦会堂,秘密将被泄露,秘密亦会发生。男孩子走入会堂,待其出来,已为男人。所有男孩皆怀着恐惧,同时却充满渴盼。终于,那一天来到了。太阳下山,明月升起。他与其他男孩一起走向会堂。村里的成年男性则站在会堂入口,黑影黢黢的。有一架梯子,通向会堂下部深处,内里有红色的光芒。打头的男孩已经开始往下爬,突然,一个男人走出来,抓住了他的手臂,把他从男孩的队列中拉出来。他摆脱此人,试图躲进他原来的队伍中去。此时,那男人动手打他,并抓住了他的头发。
“没你的事,你个白头小子!”
“对,那母狗的儿子没资格。”另一个男人说。
男孩们笑起来。
“滚!”
他那时仍然在队伍的边缘犹豫。
“滚!”男人们朝他吼叫。其中一人弯腰捡起一块石头,朝他砸过来。
“滚!滚!滚!”随后好像下起了石头雨。
流着血,他跑进了黑暗中。他听到,从那被红光照亮的会堂里,传来歌声的喧嚣。最后一个男孩也爬下了梯子。此刻,他孤独一人了。
纯然孤独,游离于村子之外,他站在台地光秃秃的平地之上。月色之下,那些岩石好像漂白的骨头。在山谷之中,郊狼朝向月亮嚎叫。伤口很疼,还在流血,但他不是因为疼痛而啜泣,而是因为纯然的孤独而啜泣,因为他被逐出人群,孤独地流浪在月光和岩石构成的骷髅一样的世界中。在悬崖边缘,他坐了下来。月亮在他身后,他朝下望,可以见到台地那黑色的影子,那是死亡的影子。只需一小步,只需轻轻一跃……月色之中,他伸出右手,在手腕伤口处,血仍在渗出,每隔几秒钟,一滴血就跌下,伴着黑乎乎的光泽,在死寂之夜色中好似无色一般。一滴,一滴,又一滴。“明天,明天,复明天……”[6]
在那一刻,他发现了时间、死亡、神灵。
“孤独,永远是孤独。”约翰沉吟道。
在伯纳德心中,这个词语引起他悲哀的共鸣。孤独,孤独……“我也一样孤独,”他说,他心中涌动着知己之感,那无限的信任,“我极其孤独。”
“真的吗?”约翰非常惊讶地问,“我本来以为,在‘它世界’……我是说,琳达总是告诉我,在那个世界里,永远都不会有人感到孤独。”
伯纳德脸红了,扭捏不安,眼神都不敢正对约翰。“老实说,”他喃喃说道,“我与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我猜是这样,要知道,如果一个胚胎被倒出容器时与别的胚胎不同……”
“对,正是如此,”约翰点了点头,“如果你与别人不一样,你必定感到孤独。对付一个人,他们好像畜生一样。你可知道,几乎所有事情,他们都将我拒之门外?当别的男孩被打发到山顶去过夜时——知道吗,你要在山顶梦见你生命中的神兽——他们却不允许我去。所有的秘密,也不准任何人告诉我。尽管这样,但我独自去做了所有这些事,比如,连续五天什么也不吃,然后在一个夜晚,独自出发到山里去。”他指着山的方向说道。
伯纳德笑了,他居高临下地问道,“那么你究竟梦到了什么没有?”
约翰点点头。“但是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他沉默了一会,然后低声说道,“有一次,我做了别人都没有做过的一件事,在夏日的正午时分,我面对一块岩石站立,双手张开,假装自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想体验,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在大太阳底下,就那么站着……”
“可是为什么想体验这个?”
“为什么?因为……”他犹豫了会,“因为我觉得自己必须去体验。如果耶稣可以忍受,我也可以。而且,假如一个人犯了错……这么说吧,我不开心,这也算是一个理由吧。”
“用这种方式解决你的不幸福感,看起来有些好笑,”伯纳德说,可是再一想,他却觉得在约翰的行为中,到底存在着某种价值。那是比吃点索玛更高的价值……
“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就晕倒了,”约翰说,“面朝地跌倒了。你看,那次划伤的疤痕还在这里。”他撩开前额又密又黄的头发,只见右太阳穴处,有一个苍白色的伤疤,那里的皮肤起皱了。
伯纳德看着,然后微微发抖,迅速移开了视线。他接受驯化教育,使他有根深蒂固的洁癖,使他无法产生更多的同情感。只要提及疾病、伤痕,对他来说不仅是可怕的,而且甚至是深感厌恶、排斥的,就像排斥灰尘、畸形和衰老。他迅速转换了话题。
“我很好奇,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回伦敦?”他问道。当他在那小小的屋子里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年轻的野人其“父亲”究竟是谁时,他就开始秘密谋划,这个邀请,乃是他首次将自己的密谋付诸行动。
“你们会愿意?”这年轻人脸上像放了光一样,“你是说真的?”
“当然,只要我能获得许可,你就能去。”
“琳达能去吗?”
“这个……”他犹豫不定起来,自己也不能确信。琳达是多么令人厌恶啊!不,带她回去是绝不可能的。除非,除非……突然,伯纳德意识到,琳达令人厌恶之处,或许正是有助于他实现密谋的巨大的优势呢。“当然,绝对可以!”他叫起来,表现出极大的热诚,以弥补刚才他表现出来的犹豫。
约翰深深呼吸,“我一生都在梦想这一刻,想想看,居然真的要梦想成真!还记得米兰达[7]说过什么吗?”
“米兰达是谁?”
可是这兴奋的年轻人显然没有听到这个疑问。“这是奇迹!”他说道,两眼闪亮,面颊因激动而焕发红晕光彩,“这里有多少美妙的人儿啊,人类又是何等的美丽非凡![8]”他脸上的红晕忽然加深,他是在想列宁娜,这个身着深绿色纤维胶衣服的天使,因青春与润肤霜而荣光焕发,丰满多姿,正朝他微笑呢!他的声音忽然颤抖起来,“啊,美丽新世界!”他说道,却突然打断自己的说话,双颊忽然惨白,白如薄纸。
“你和她结婚了吗?”他问道。
“我和她怎么了?”伯纳德问道。
“结婚。你知道的,永远在一起。‘永远’是一个印第安词汇,表示契约牢不可破。”
“主福特啊,当然不!”伯纳德忍不住大笑起来。
约翰也笑起来,却单单为了快乐而笑。
“啊,美丽新世界,”他重复说道,“‘啊,在美丽新世界里,该有何等样的人啊。[9]’我们立刻启程吧。”
“有时你说的话甚是奇怪,”伯纳德说,困惑、讶异地看着这个年轻人,“但是,不管如何,要想看到新世界,你还得耐心等等。”
* * *
[1]上述的神灵以及神迹,除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外,皆源自印第安人的神话。
[2]基瓦会堂,或称为大地穴,是印第安人的一种圆形建筑。
[3]语见《哈姆雷特》第三幕,哈姆雷特攻击其母。
[4]语见《哈姆雷特》第二幕。
[5]语见《哈姆雷特》第三幕。
[6]语见《麦克白》第五幕。
[7]米兰达,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女主角,正是她在台词中提到了“美丽新世界”。
[8]语见《暴风雨》第五幕。
[9]语见《暴风雨》第五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