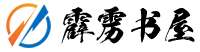益智子,如笔毫,长七八分。二月花,色若莲,着实,五六月熟。味辛,杂五味中芬芳,亦可盐曝。出交趾合浦。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张津尝以益智子粽饷魏武帝。
——嵇含《南方草木状》
荣贻生和司徒云重重逢,是他来香港的第五年。
三月初时,“同钦”进了一批新茶器和骨碟。以往入货,都是从石硖尾的“锦生隆”瓷庄。不过因政府收地,“锦生隆”将厂子搬去了新加坡的裕郎,那里新建了铁路轨道,利于搬运。可往返海外,这样于“同钦”的购买成本就高了许多。“锦生隆”便介绍了深水埗的同业瓷场。新到货那天,荣师傅与方经理一同查验。看瓷胎上好白靓,花头与车边都十分细致。底下印着“粤祥”大红三角印章,里头是英文缩写“Y.C.”。检查至骨碟,绘着普通的鱼藻纹。可这摇曳的水藻,并不是通常的绿。光线下,有一种少见的艳异与通透。背阴处看,又是幽静的。荣师傅心里轻颤了一下。他将碟子翻转,看到碟子底部,画着一朵青色的流云。
他脱口而出,鹤春。
前来送货的伙计,有些惊奇地望他,说,师傅这么懂行,知道“鹤春”。
他放下碟子,敷衍了过去,我哪里懂,听人说起过。
一星期后,荣师傅来到了“粤祥”瓷场。
他看到门口一棵高大的椰树,突兀而挺拔地立着。四周倒是漫漫土坡。这些新建造起的厂房,犹如城堡。有巨大的烟囱突起,像城堡上的塔楼。烟并不浓重,袅袅飘向远处狮子山的方向。
他手里执着那枚骨碟,向人打听。一个路过
的工人,将颈子冲烟囱扬一扬,说,云姐,看火眼呢。
荣贻生走进炉房,似乎空无一人。当中的红砖砌成的大圆炉,倒十分壮观。七百来呎的炉房里,可感受到一股热力,还有木炭燃烧发出的,有些酸涩的气息。他走出去,向外望,却听到后面有细隐的声音问,你揾边个?
他转过身,于是看到了那个细路女,用一双灰蓝的眼睛望着他。那瞳仁上,像是蒙了一层轻薄的雾,因而有些失焦。这是一双略为凹陷的,很美的眼睛,镶嵌在净白而透明的脸上。在香港这些年,荣贻生见过许多洋人孩子。但由于他们鸣放的性格,很少见到这样安静的眼睛。但是,这细路女也有很茂盛的黑发,束在脑后。身上穿件显见是成人衣服改成的夹袄。有些陈旧的蓝底,缀着灰白的碎花。这些都是中国的背景,让灰蓝的眼睛漂浮起来。这个孩子,用地道的广东话问,你揾边个?
荣贻生弯下腰,刚想说话,听到圆炉后有声响。他听见一把女声,唤,阿妹。
细路女便回身快步走过去。这时,他看到有一个女人从炉后走出。
是司徒云重。
他们,立刻认出了彼此。云重本有的微笑,此时凝固在脸上。她瘦而尖削的脸,因梳了一个发髻而更为单薄。或许是扬起的炉灰,额上有苍青颜色,混着汗。她不由自主地抬起手背擦了一下。大约觉得没擦干净,又撩起了袖子使劲擦。擦着擦着,放下手。脸上是得宜的水静风停的笑,开口道,响……
这时,她停住,略低下头,对身旁的细路女说,阿妹,叫姨丈。
细路女,怯怯地躲到她身后去,又慢慢探出头,只露出双眼睛,望着荣贻生。
荣贻生愣一愣。他看出来,除了这双眼睛,这孩子脸上的一切,都来自云重。
这时,云重似乎想起什么,急急走到外头,喊一声,扒火。
喊声嘹亮,但有些沙,不是少女的声音了。
外面便进来了几个年轻汉子,都精赤上身,着短裤,对云重并不避忌。嬉笑着,一边用一只铁钩,钩进炉底,钩扒出赤红的火炭。炉房里顿时火花四扬,伴着更为浓重呛鼻的硫黄味。荣贻生不禁咳嗽起来。这些伙计们已是灰头土脸,更为放肆地笑起来,一个将荣贻生往外推出去。
炉子刚还是通红的火焰,待扒清炭烬后,已是冷灰色。伙计们收拾了东西,也就离去了。荣贻生问,瓷器烧好了,不收拾出来吗?
云重拿着扫把,仔细将炉灰扫成了一堆,说,东西还滚烫着,炉不能开,会吹爆。明天揭炉顶,再逐件提出来。
荣贻生躬身,向那细路女唤一声,阿妹。
女孩侧他一眼,头拧过去,不应。
云重便说,阿妹,唔好失礼人。
女孩扁一下嘴,说,我有名字的。
荣贻生笑笑,问,你叫什么名?
女孩说,灵思。灵思堂的灵,灵思堂的思。
荣贻生又问,那姓什么呢?
云重抢过话说,司徒。司徒灵思。
荣贻生看她站在门前,眼里灼灼的。这时眼神却躲闪了一下。
他便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了一个纸袋,给女孩,说,姨丈打的点心。
女孩不接,恋恋地看一眼母亲。云重点一点头。她才接过来,打开,里面是几块只烤得焦黄的酥饼。到底是被食物的香气诱惑,灵思忽有了细路女该有的样子。她小心翼翼地舔一下那块饼,咬一小口。灰蓝的眼睛里,泛出了光来。
荣贻生问,灵思,好唔好味?
女孩使劲点点头。荣贻生便说,好味,姨丈再整给你吃。
云重便说,阿妹,阿妈点同你讲,有了好东西要怎样?
女孩眨一眨眼睛,似乎不太舍得。但用细细的声音说,分俾人食。
便捧着这些饼,慢慢朝厂里走去。
荣贻生沉默一下,赞道,女女好教养。
云重看着孩子的背影,轻轻说,论理女仔要富养。养不成了,起码要上规矩。
两个人,看着那小小的身影,被一群孩子簇拥。个个是雀跃的,大概都是瓷场的子弟。这时候,荣贻生听到云重问,你怎么找了来?
他便掏出了那只骨碟。云重张一眼,说,你们要得急,瓷场的人手不够。我平日不画饭货。
荣贻生说,我知道,碟子底下没有“粤祥”的印。可你舍得用了“鹤春”。
云重便不说话了。久后说,现在谁还在乎这些呢。
他们便一路往前走着。走了一会儿,渐听到了潺潺水声。長坡后边,竟隐着一条溪流,漫漫地流向草丛中去。这时节,还传来间或的蛙鸣。
荣贻生一时间,似乎有许多的话。待开了口,却问道,你等到那个人了吗?
云重愣一愣,站定了。脸庞望一望瓷场的方向,说,就在这吧,我还没收工。替我问秀明好。
荣贻生想一想,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将烟壳剥下来,在上面写了个地址。他说,这是我们家。远一点,在上环。有空来,秀明念着你。
“做冬”那天,云重才带了灵思来。
因未见过,孩子们都很认生。家里男孩们到底活泼些,不一会便也熟了。小的那个,追着灵思叫“鬼妹”。
大人们一听,愣住了。秀明就冲他屁股上打一记,说,冇轻重,这是你表姐。
云重将自己和孩子,都收拾得齐整。头上抿着很紧的发髻,穿件青绸的旗袍夹袄,十分合体。秀明却看见,这衣服的袖口有浅浅磨毛,怕已有年头,只是穿得珍惜。
云重带了一只很大的碌柚来,说记得秀儿爱吃。秀明说,这么多年了,亏你还记得。入冬来这东西金贵,人哪里舍得吃,都用来敬神。
说着接过来,直接便摆到了神龛前头。龛里敬着德化瓷的水月观音,音容慈济。下面有两个牌位。一只上面写着,“尊师叶凤池生西灵位”;另一只写了“先妣荣氏慧生往生莲位”。
云重看了,不说什么,也没问。只与秀明求了三支香点上,随她拜一拜,插进香炉里。又默立了一会儿。
她还带来一只瓷盘。正中画着凤穿牡丹,瓜果边是白菜百蝠。开了斗方,里头画着一对捧了石榴的总角孩童。秀明啧啧称赞,说好喜庆。又凑趣说,这细路画得真好,像极了家里的两个讨债鬼。
云重便也笑说,石榴多籽,以后还能生。儿孙满堂。
秀明道,唉,香港这几年物价飞涨,揾食艰辛。再生养不起,能把小冤孽们糊弄大就不错了。
说罢,她便将这只盘,郑重摆在了客厅正中的腰柜上。云重看到这腰柜上还有一只大盘,正是自己当年画的安铺,如阴阳太极,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光外。
这时,荣贻生端着菜,从厨房里走出来。戴着青花的围裙,样子有些可掬。秀明就说,他啊,平日里一个厨子,回家是不做饭的。这是当你作贵客了。
荣贻生便说,在家里头,就几个家常菜。
云重看这些菜,说是家常,又很见心思。鱼生腊味蚬菜煲,有几分“围炉”味道,是要往年菜的丰足上置备的。她也发现,盛菜的碗盏,也是自己送的。荣贻生给他们夹菜,说,这套瓷器,秀明可疼惜。从广州带过来,一年用两次。过年一次,中秋一次。今年“做冬”,算是破例了。
秀明说,云姐,你还记得,我哋上回一起“做冬”,是在安铺。成个屋企,阿爸阿妈,还有周师娘。也是六个人,三个老的,三个小的。那时我们仨是小的,如今成了老的了。
云重笑笑,摸摸灵思的头,说,是啊,又是“做冬”。我到哪里,都是个客。
秀明听了,脸上的笑容敛了一下,说,讲乜哦,我哋系一家人。这不是团圆了吗?
说罢,便支一下男人。荣贻生恍然,站起来说,看我,高兴到大头虾!汤圆都忘了煮。
饭吃到了一半,秀明问,响哥当年送你回广州,再没见过。我们一直担心着,你去了哪里。
云重放下筷子,嘴巴抿一下,用手帕擦了擦。她说,广州湾。
秀明说,鬼子飞机炸安铺,我们也去了广州湾。竟没有遇得上。
云重便道,都是乱离人,谁能碰得到谁呢。
秀明轻轻说,也是。个个自身难保,一家人能全须全尾就不错了。
云重说,方才我一路走过来,经过摩罗上街,好多铺子在卖古董。那价钱高得吓人。以往在广州湾,收了工,去赤崁海边街。骑楼底下,都是逃难的人。什么好东西都有,都是三文不值两文地卖了。
她便给秀明看她耳上的坠子。原来是水色很好的翡翠,爍烁在灯下闪着光,从她朴素的形容里跳脱了出来。她说,买这一对,当年也就几张西贡纸。
几个大人喝了点酒,渐渐微醺。秀明说,响哥,你记不记得,那时云姐教我们唱一支歌,是她阿爷教的。云姐,那句怎么唱来的?有船又有花。
云重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唱道:伍家塘畔系瓷乡,龙船岗头艺人居。群贤毕集陈家厅,万花竞开灵思堂。
刹那间,这歌声唤醒了荣贻生,或者阿响。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少女,站在安铺连街的桂花树
下,一边唱着歌,并无忧虑地望着他。然而,此时这歌声,似曾相识,虽婉转,却听来郁郁的。尾音不复当年丰润,草草收束,是被岁月风干了。
唱着唱着,云重自己先黯然下去。她捋捋鬓发,抱歉地看一眼,说,细路女的歌,不好再唱了。
她抬起头,看一眼挂钟,说,不早了。我们要回去,赶末班的渡海船。
秀明这才想起,她是一路迢迢而来,便说,今晚别走了。难得来,让孩子们多玩一会儿。
云重摇摇头,明天一早还要开工。
秀明就问她住哪里。云重说,住在大窝坪厂里的宿舍。
秀明说,你带着孩子,住厂里方便吗?
云重浅浅笑,大家有个照应。原本住九龙仔大坑东,这不去年一场火烧了木屋区。现在有个容身之处不错了。只是孩子上学,以后麻烦些。
她弯下腰,对女儿说,思女乖,跟秀姨姨丈说拜拜。
荣贻生和秀明,将云重送到德辅道上。两个人又沿着山道,慢慢走上来。秀明这时回过身,对男人说,云姐现时这样,我们要帮帮她的。
我在尼斯见到了司徒灵思。她如今寡居,住在一幢老年公寓里。
我们吃过了晚餐,她提议去海边走走。路上经过了一个周末市集,卖各种皮具。她看上了一串绿松石的珠链。她坚持不懈地和小贩讨价还价,用流利而嘈切的语调。她的法语有浓重的后鼻音,我不知这是否是传说中的里昂口音。她如愿地买到了那串珠链,立刻戴上,并问我好不好看。灰蓝的眼睛,在路灯下,泛着暖色的光泽。我问她,是否记得,她母亲有一对翡翠耳坠。
她看我一眼,很清晰地说,记得,我九岁时,给她当掉了。
司徒灵思与很多老人不同。她对往事保持着惊人的记忆,精确到可以年份作为刻度。
除了幼年时造成家变的那场大火,她似乎善于向我勾勒所有记忆中的场景。她有很好的中文能力,将这些场景还原得如此逼真。甚至于瓷场里所有厂房与房间的方位,房间的布局,其中的陈设与工具,工具的功能,都一清二楚。特别是房间里的圆炉。她说,她在寄宿学校里,第一次听嬷嬷讲起巴别塔。也许那时太小,她总觉得这圆炉高得像巴别塔一样,可以一直通到天上。
直到她稍长大,还不足以登上阶梯。云重便抱着她,从火眼望进去,才看清里面层层叠高的瓷器。为了防止瓷器底面刮花颜色,都以薄瓦在周边支撑或上砖分隔。她告诉我,极小时,母亲便教会了她有关火与颜色的奥秘。这也是烧制过程中加炭升火与扒火的规律。最耐高温的是西红。西红中有黄金磨粉,所谓真金不怕红炉火。而大红不耐火,遇火则变黄。我问,那鹤春呢?她说,鹤春和大绿一样,在火中早成通透。调色里用了水白,过火便会冰裂,前功尽弃。
虽然是五月底,夜里的海风,其实有些凉。但这没有阻挡人们下海的热情。也因为水凉,为了抵御寒冷的体感,有人在水中热烈地唱起了歌。是支我并不熟悉的法文歌曲。司徒灵思,跟着这些泳客一起哼唱,一边在大石嶙峋的海岸边坐下来。
我终于问,离开香港这么久,有没有关于食物的记忆。她想一想,说,瓷场的工人们,都好吃狗肉。瓷场厂里的女工很少,他们将买来的狗交给云重打理。母亲将这些狗放掉,然后买了羊肉替代。两年都未被发现。她那对翡翠耳坠,就是为买羊肉被当掉的。
我于是引导式地开启话题,说,广东最出名的,是点心。恐怕和这里唐人街的口味,还是不太相同。
司徒灵思,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夜归的海鸟,翅膀掠过海面,牵起无数的水花。落下去,便是层层涟漪。
一个幼小孩童从水中出来,在大人看护下,慢慢向岸上爬。司徒灵思,定睛看他终于爬上了岸。大人们兴奋地对他叫着:“Bravo!”她似乎也松了口气。看一眼我,说,我知道您想问什么。我已经老了,不会介意更老的人发生过的事。我想,那时我可能需要一个父亲。
荣贻生想,他一直错过了司徒灵思的眼睛。
这个孩子此后的成长,渐渐偏离了云重基因的赋予。她的面目,轮廓开始变得硬朗,深目高鼻,却有海藻一样丰盛而卷曲的黑发。在她开始发育时,显见比同龄的孩子更为茁壮。为了掩饰,她学会了含胸,这并非让她显得谦卑,反而有些尴尬。当她上中学时,她发现自己被同学无端地孤立。在中国孩子与本港的西人中,都不被待见。因为他们想当然地,将她推给了对方的阵营。
这种误会也来自于大人。她的成长,渐渐将这种误会滋生壮大。有一个男人,长久蛰伏于她灰蓝色的眼睛,这时开始显山露水,改造着她,用她的形貌复制着自己。这个人,这么多年,是云重想要忘却的。代表某一段不想被提及的过
去。她知道,荣贻生也知道。但是灵思的成长,在提醒和鞭笞她,对这段过去的不可遗忘。
然而,荣贻生却也在这孩子的成长中,获得了某种侥幸。他想,这终究是一个外国孩子,她不属于云重,甚至不属于这个地方。非我族类,或是一切隔阂的开始。当然,他对灵思比以往更加好,甚至比一个真正的父亲更为周到。他心里很明白,这是对一个“客居”者的耐心与善意,而不是对自己的孩子。这种心态一旦膨胀,无知觉间,带来了自欺欺人的安全感,让他自我麻痹。
他不再那么审慎。一个外国孩子,会懂得什么呢?东方人的含蓄情感,她不会懂。发乎情,止乎礼,她也不懂。她只有一双笼着薄雾的、灰蓝色的眼睛。她看不懂的,中国人的眼眉之间,不露声色,水到渠成。
他没有意识到,这已是险境的边缘。当将灵思送进了寄宿学校,他便在深水埗的北河街租了一个唐楼单位,让云重搬了过来。开始云重并不愿。他说,你一个女人家,住在厂里,总不是长久之计。
他选择这里,是因为靠近深水埗码头,有来往于上环与深水埗的“油麻地小轮”。一些清寒的周六,他和秀明会沿着威利麻街一路走到码头,登上小轮去看望云重。后来,秀明的身体不再适合远行。他便一个人去。这座唐楼在码头的斜对面。正门口是铲刀磨剪的铺面,走进去是九曲十八弯数不尽的板间房。里面除了住家外,更隐匿着小型工厂,有打铁的、铸模的和印刷的。四周荡漾着一种带有金属味的烟火气。
那个单位在最里面。开开窗,能看见码头上的光景。他总是带着点心。带什么,取决于他来的时候。若是中午来,多半是小按包点,叉烧包、虾饺,又或者是粉粿。到了深水埗,还带着余温;若是过了午后,便是大按的糕饼,莲蓉酥和光酥饼,这多是他自己的手笔。两个人就就着夕阳的光线,慢慢吃。透过窗户,看码头上的人聚和散。
有一次,他进门,就闻到鲜而甜的杧果味。屋当中的火水炉上,坐着一只小锅,里面咕嘟咕嘟,正煮着西米。云重将西米捞出来,待冷了,用纱布滤干。这才开始切杧果,切成九宫格,然后细细地将果肉剥下来。她低着头,说,小时候,我阿妈给我做杨枝甘露。我学会了,还未做给人吃过。
做好了,他们仍是靠着窗吃。看一辆巴士在远处停下。多是荃湾与葵涌的居民,挤挤挨挨地从车上下来,赶着码头的钟点。一班船走了,码头忽然就空了。阳光将栅栏的影子投在石屎路上,像一丛丛剑棘。
云重放下手中的碗。码头上的几个孩子玩“跳飞机”,她看得入神。一些光线柔和,笼住她的侧影,镀了金一样。荣贻生看她脸上是毛茸茸的。把岁月的痕迹抚平了,竟还是当年那个少女,站在青龙舌上,惘惘望着九洲江,浩浩汤汤。他走过去,倏然捉住了她的唇。闭上眼睛,杧果余香,还有一丝薄荷的凉。
以后,荣贻生吃过这只火水炉做过的许多东西。都很简单,但并不简陋。有时是甜品,有时是粥品,有时是一只啫啫煲。虽非盛宴,却经时间堆叠,成了荣贻生内心的一个盼头。每每他坐上渡轮,就在想,云重会给他做什么吃。这样想着,脸上会有笑意。他想起回广州的船上,云重将他打的莲蓉月饼掰碎,一点点掷到海里去。
有一回,云重什么都没有做。他未免失望。却见云重说,我今天在街市看到卖蚬,广州来的黄沙大蚬。我想等你来了再买,新鲜。你等一等我。
他要跟她一起去。她竟默许了。两个人,就走到了北河街的街市上。云重在前面走,荣贻生遥遥地跟在后面。看她出入店铺,买香料、买葱姜,看她相中了路边一束姜花,驻足,与小贩讨价还价。她捧着姜花,人走到哪里,香味便畫出她的行迹。荣贻生便跟着这香味,越跟越近。这仿佛某种成人的游戏,带有冒险的性质。卖蚬的摊位上,他们终于走在了一起。他们从未在外面,站得如此接近。云重买好了,极其自然地,将手中的菜篮递给他。他也极自然地接过来。
当两个人走进唐楼,走上楼梯。云重问道,攰唔攰?
她一边拎起篮子的提手。但他并没有放手。两个人便一人拎着一边,在黑暗的楼道里走。这提手便将两个人的体温,传给了彼此。
黄昏时候,他在姜花的香气中醒来。这花香中,有浅浅的清酒煮蚬的清甜。
他看见云重,披着衣服,坐在一只灯胆的光下。一手执着瓷盘,一只胳膊靠在枕箱上。此时她脸上神情,有种端穆与肃然。微微蹙眉,眉宇间似乎也有些苍青。这一切,似曾相识,让荣贻生恍惚了一下。
他也认得这只乌木枕箱。是云重的阿爷传给她的。箱盖深深镌着“司徒”两个字。凸凸凹凹,一刀一痕。箱身陈旧斑斓,是许多代的绘彩人沾染上的颜料,和时间一道被桐油封印。
荣贻生看她画的,是一个码头,苍黑地伸向
海中。海是蓝的,包裹了远帆,与大小舟只。海天相接处,用的是鹤春。那样绿的一线,接于幽明之间。
荣贻生这样看了很久。直到天色黯淡,云重回过身来,才察觉。荣贻生说,阿云,你可还记得?那时在虞山上,你对我说,等我们都出了师,我做的点心,都用你画的彩瓷来装。我们还勾了手指。
云重放下笔,定定地看外头的云霭,对他淡淡笑说,我算出师了么?我画的东西,如今在你们茶楼,只配做骨碟。
司徒灵思,很早发现了母亲的异样。这异样体现在食欲的偏狭。云重终于不再信任女儿如此粗枝大叶,因为她看到桌上出现了一包杨梅和嘉应子。她刻意没有去碰。想一想,又在灵思面前故作坦然地打开,拿出了一颗放进嘴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忽然,司徒灵思看见母亲捂了下嘴巴,肩头战栗了一下。
即使再谨慎,只要一方自认成为猎物,另一方自然洞若观火。云重开始穿起宽松的衣服,有了街头师奶的样子。这不符她一贯的审美。灵思仍不动声色。当渐渐显出腰身的时候,母女间的博弈也行将结束。灵思想,为什么那个男人还没有出现。她于是问,姨丈最近怎么没有来。我想他的莲蓉酥了。
下一个周末,荣贻生便来了。一切如常,带来的是同钦楼的素包。问她的学业,和同学的相处,开长辈分寸无关痛痒的玩笑。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却没有看云重一眼。灵思说,姨丈,下个星期分级试,我心里没有底。想去黄大仙拜一拜。
他们就到了九龙城。因为过了十五,人并不很多,但香火依然鼎盛。灵思说要去麟阁拜文曲星。云重说,女女,我想求支签。
荣贻生事不关己的样子,说,我都去望一望。灵思看他们走远,便往麟阁去。拜完了,又磨蹭了一会,才去解签档。却未见人。便一个个殿看过来,在三圣殿看到母亲,正在观音前,阖目而拜。荣贻生站在很近处,脸上有戚然之色。
晚上,趁母亲冲凉,她找到了那支签。签诗写,“十九年前海上辛,节旄惆败逐沙尘,餐毛嚼雪谁怜我,惟有羊儿作伴群。”她便将签文抄下来,拿去给师傅解签。师傅说,求签的是什么人。她想想说,我阿姐。师傅说,不好,中下。寒凝瘀阻,孤而不得。
灵思恍惚一下,孤而不得?那我算是什么?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孩子还没生下,便有个老窦看着。哪怕不名誉,但至少是有。
清明前,云重的孩子没了。
她只身到“多男”时,已平心静气。
她还是个细路女。云重轻声说。
荣贻生将头偏到窗外去。因为隔着玻璃,路面上车水马龙,却无声。他想,为什么今天七少爷还没来。这女人却来了。
他的孩子走了。他无数次憧憬过这孩子。
签上说,“苏武牧羊”,苏武终究不是回来了吗?可这孩子呢,却永远走了。这女人的细路女,亲手把母亲从楼梯上推下来。然后在医院里哭着告诉自己,没想到阿妈有身己。流了好多血,佢好惊。
云重喝下一口茶,很热。但她还是大口地喝下去,没有停下,直到喉咙灼痛。这茶里,有一丝甜。她想,大概是因为最近口苦,吃什么都是甜的。可是喝到最后,她看到茶盅里卧着一颗开瓣红枣。
她从楼梯望下去,望见刚才那个男孩。正是长身体的年纪,长手长脚,身形却单薄。举着一只很大的黄铜水煲,疾走在各台之间。她看看面前这个男人,想,她错过了他的成长。他小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七年后的初夏,五举记得很清楚。
这一年他十七岁,已近成年。这城市经历了许多,也变化了许多。同钦楼里,他已看惯了每日朝夕景象。客还是那些,有些老人来不了,或者不来了。有些年轻些的面孔,渐老去。这老去也是在无知觉间,是安静的。
然而这初夏,城市不再安静。
空气中燠热,隐隐弥散一种干涸气息。港岛中环至北角,开始出现聚散的人群。这股热浪中便挟裹了声浪。五举依稀听说,这与前一年的“天星小轮加价”有关。人们头顶盘旋着直升机,也是轰隆作响。港英政府发表声明,街上出动防暴军警。
这一日,五举去中环送货,回来路上,路过皇后像广场,看见挤挤挨挨的人群,他们手中举着红色的小书,口中呐喊,向港督府的方向走去。汹涌的人流,将路截断了。电车停下来,五举随其他乘客下了车。也随着人流往前走。走到华丰百货,看几个英籍警察,荷枪实弹,正围着一处消防栓。消防栓上醒目地摆着一个纸盒。盒子上写着“同胞勿近”。五举知道,这是在民间传说的“土制菠萝”,是真假难辨的炸弹。
一个督察模样的警察,用洋腔调的广东话,呵斥与驱散围观的人群。但因经过人流的声浪,他的声音被淹没了。人们簇拥在昃臣爵士铜像周围。铜像的底座上站着一个青年人在慷慨激昂地演说,忽然举起一条白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爱国无罪,反英抗暴”。见此横幅,铜像四周便是如云的臂膀。就在这时,五举看到了谢醒。那是师兄的背影,他再熟悉不过,一肩高,一肩低,看起来有些散漫。他和众人一样,高举起臂膀。他想,这两日都没有见到师兄返工,原来是在这里。他于是喊着师兄的名字,但这声音,也被声浪所淹没了。
五举是黄昏时回到史坦利街的。在茶楼附近,他看到了那个女人。他想,这么多年,他时而见到她,自从“多男”开始。此时,她站在街角路灯的灯影里,对面是师父。两个人站得有些远。师父的影子被灯光折叠在墙上,她就站在这影子里,也像是师父的一个影。这么多年,她是师父的影。只是匿在背阴处,一旦有了阳光,她便不见了。这些年,他从不知她是谁,师父也从未告诉过他。但他知道,人都会有影子。哪怕自己看不到,影子还在。时而浮现,可亦步亦趋,可如影随形。
女人比他印象中,更为朴素。没有穿旗袍,而是着暗色的短衫。头发也竟剪短了,衬着尖瘦的脸,远望竟像是个少女。五举走去了街对面,远远地想绕开。但却看到师父抬起头,对他喊,举仔,去帮我买包烟。
他愣一愣,便去士多店,买了一包“金宝”回来。荣师傅接过来,撕开烟盒,抽出一支,点上。又用手指弹出一根,对五举扬一下。五举不知何意,让一下。荣师傅说,大个仔啦,陪师父食一支。五举想一想,點上。这是他第一次抽烟,不得要领,感到一股绵长刺激入喉。未及品味,不禁咳嗽起来。
荣贻生大笑,自己吐出一个悠圆的烟圈。散开了,在灯光底下,袅袅地散了,成了极其稀薄的蓝雾。
五举见对面的女人,抬起手,似要驱散眼前的烟雾,却慢慢地放下了。她说,佢学人去港督府抗议。学校的人都回来了。得佢一个,到依家都没返。我是真的冇办法。我知道佢对你唔住,可她当年只是个细路女。你要记一世吗?
荣贻生又吸了一口,却未将那烟吐出来,咽下去。眼里有苦意。五举看他用手指将烟掐灭了。他说,举仔当年都是个细路,如今大个咗可跟我食烟。你嘅女细时已经好有主意,你唔俾佢做,佢会听你讲?
女人沉默了一下,说,我听说那些英国人,捉人到差馆,给女仔饮头发水,他们乜事都做得出啊。我求下你。
荣贻生看着她,目光很冷,忽然笑了。他说,放心,她生了一张洋人的脸,差佬能拿她奈何。
女人似被什么击中了,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她抬起头,五举看她脸上有两道泪痕,已经干涸了。她慢慢地走近了,满面疲态。但眼睛里头,是细隐的光。荣师傅不禁后退了一下。她从五举手里夺过还在燃烧的香烟,放进自己嘴里,使劲地抽了一口。然后那烟雾从她口中游出来,松软地消隐在黑暗里头。她将烟掷在地上,用脚使劲蹍一蹍,转身离去了。
五举再见到女人,是在师娘的丧礼上。
她有些见老了,也更瘦,但仪容优雅。不同其他女宾,她穿一身丝绒西服,举止端穆利落。她敬的花圈,署名是表姐,司徒云重。
五举这才知道她的名字。
五举帮着师父招呼宾客,也做了孝子的身份戴孝。荣师傅有两个儿子,一个年纪比他大,一个比他小。荣师傅便让他站在中间。在旁人看来,是要让他在亲子中行二,视如己出的意思。此时,谢醒已经出走。五举以这种方式出场,众人也便明白。将来这年轻人,是要继承荣师傅的衣钵了。
他与两个义兄弟,一一向来宾谢仪,鞠躬。对望重的老人,还要磕头。到了云重来,弟弟愣愣,忽然趴在她身上哭泣。哥哥在旁边不说话,身体却依过来,云重便也拥过他的肩膀。云重看着五举。五举随这对兄弟,轻轻叫她云姨,对她鞠一躬。云重伸出手,将他的手拿过来,放在自己手里。她的手心有些凉。云重又将另一只手,放在五举的手背上,重重地按一按。他们的手叠在一起,就有些暖了。
隔年的正月初三,荣贻生与云重相见。
彼此心里都有话,不知该谁先说出来。两个人走了一程,荣贻生便说,去看戏吧。云重愣一愣。荣贻生说,看大戏。
此时香港的戏院,平日其实放的是电影,新年多是用好莱坞的新片贺岁。粤剧戏班的热闹,则不在戏院里,倒是在公众地方搭起临时戏棚。如湾仔的修顿球场、油麻地的佐治公园、旺角的伊利沙伯青年馆。每个剧团大概只演到年初八。因是新年演剧,对点演剧目,十分看重应
景。多是吉祥之正本剧头,观剧亦欢喜得佳兆之乐。如《郭子仪祝寿》《五子登科》《十三岁童子封王》,讲的是戏里戏外的好意头。各个戏班,也将班牌套入剧目,要一个喜上添喜。凡此种种,投观众所喜,辄得旺场。唯正月初三,俗谓“拆口”,依戏班规例,向点演兆头不好的剧本,亦有教忠教孝之意。如《罗成写书》演罗成殉国的忠烈,后始有罗通扫北,父子英雄;《薛刚打烂太庙》,则是薛家将为奸佞所害,满门抄斩,仅薛蛟为徐策所救,后讨武立功,保全本族声誉。这些剧谈不上大团圆,甚至有血光杀气,但含英烈传代之意,观众便也不会责难。
荣贻生和云重走到了“修顿”,看是觉先声戏班的台。荣贻生便先挤进人群去。出来,云重问演的什么剧目。荣贻生脸上有犹豫,便说,是《十二寡妇征西》。两个人对望一眼,云重说,来了就进去看吧。她们这一仗,不是打胜了吗?
进去才发现,看的人并不多。大约外头簇拥的人群,想想,终究没有进来。戏开演了。因是连台本,这时已演到二本。杨文广率领十二夫人班师。扮佘太君的,大约是个年轻的老旦,唱腔尚好,体态却是窈窕的。杨排风的演员倒是上了年纪,身形魁伟。大约自知其短,矫枉过正。金殿上与魏化争帅印一场,竟演出了几分娇憨。场上莫名有了喜气。
戏演完了,走出来。听到身旁一个师奶,激动地跟老公说着对演员的刻薄话。老公则唯唯诺诺的,敷衍道“一出戏啫,唔使咁认真喇”,显见平日在家里也是诈傻扮懵惯了。
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心情竟有些好起来。
就往维园的方向走。忽然,云重见荣贻生停住了,引着颈子向人群中张望,看了半天,却转过头来。眼里空落落的。见云重望着他,就说,我好像看见七少爷了。
两人穿过轩尼诗道。到处是人,喜洋洋的。大人穿得平朴,孩子们倒都是锦簇的,想是将全家人对新年的盼头,都堆叠在了这些细路身上。维园里头,正开着花市。多的蝴蝶兰、黄金果、富贵竹和大盆的修剪得像山一样的金橘树。明晃晃地照人眼睛。云重在一个摊位上停下来。这摊位显见有一些冷清,摆着几盆西府海棠。红的白的,红白相间的,开得舒展。
她就对荣贻生说,太史第里,养得最好的就是海棠。
荣贻生想想,杜耀芳村的西府海棠,都是赶了夜送来的。第二天早上正开得好。
云重说,我进过几次太史第,就记住了海棠。
荣贻生就挑了一盆小棵大红的,叫摊主淋上水。颜色越发地浓艳。云重有些欢喜,就抱着那花盆。花盆是石湾的老式样,上面彩绘闻香的佛陀。
往前又走了一会,走到了电气道上。这时,荣贻生才说,你来太史第头一年,我记得。你还从我手里头,接过一个福袋。可记得?
云重摇摇头。
荣贻生便停下来,在怀里头掏出了一只红灿灿的缎袋。他说,这个给你。云重见上头绣了一只金猪,底下写“家肥屋润”。她便笑道,几十岁人了,这唱的哪一出。
荣贻生便说,你不要?
云重扁一下嘴,说,你敢给,我怎么不敢要。
她便放下手中海棠,接过来,一倒,里头是个织锦的盒子。她的笑容,便在脸上凝固了。荣贻生说,打开看看。
她犹豫了一下,到底打开了。
盒里,卧着一只钻戒,戒面折射了璀璨的光。这些光由四面八方凝聚为一点,太夺目,有些晃人心神。
荣贻生说,我替你戴上?
她摇摇头,自己将戒指拿出来,想想,便郑重地戴在了右手的无名指上。不松不紧,将将好。她抬起手,放在阳光底下看一看。看得很仔细。夕阳的光暖暖地从她的指缝间漏了过来,照亮了手背上青蓝的血管。
看完了,她将这枚钻戒,从手指上慢慢褪下来,又放进盒子里去。将福袋拉紧,还给了荣贻生。她笑笑说,响哥,谢谢你。这辈子,我算是戴过了。
年初八那晚,荣贻生一个人,在茶楼的后厨补饼。
这样的活计,如他一般的大按板,是很少做的。一个人待在后厨,寂寞不说,何况还在年关。他对新上的车头道,我来吧,屋企反正都冇人。
他补的是“光酥饼”。此刻,炉头渐弥散出浓烈的、难以名状的奇臭,让他的意志骤然清醒。这是臭粉的气味。松身雪白的光酥饼,面团发开,全赖于它。这臭味在烘焙过程中挥发。臭味散尽,饼也就成了。
戴凤行悄然进入后厨时,被这臭味打击,不禁掩了一下鼻。同时间,荣贻生也看到了这个陌生的青年。他想,这是谁,如何就进入了同钦楼
的禁地。
他注意到徒弟五举,也看见了这个人。五举更多不是惊奇,而是不安,以有些虚惶的眼神望向自己。荣贻生于是知道,他们是认识的。
此时,青年已镇静下来,对他鞠了一躬。待头抬起来,目光与他相对,凛凛的。
荣贻生想,他竟不怕。这个瘦弱的青年,为何眼里会有这样坚强笃定的光?
荣师傅看一眼五举,问来人,你是五举的朋友?
青年点点头。
荣师傅沉吟一下,目光转向徒弟,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说,送客。
然而,待两个年轻人走了出去,他大声一喝,回来!
他戴上手套,将刚刚焗好的光酥饼从炉里取出来,对五举说,回来,给你朋友带两个走,回家吃。
然后,他从怀中掏出一封利是,递给青年,说,以后不要到厨房来了,唔啱你。
待徒弟回来,他问那青年人的名字。五舉回,凤行,戴凤行。
他想一想,笑笑,说,这名字,倒像三毫子小说里的侠客。
刹那间,他想到了云重。她告诉过他,自己名字是阿爷起的,出自一位明朝的武状元。
听说五举要娶,荣贻生并不很意外。
又闻说是凤行,他愣一愣,便哈哈大笑起来。他说,衰仔!瞒天过海啊。你哋两个,原来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说这话时,他心里是高兴的。他回忆起凤行与他对视的眼神,坚强笃定。他想,这样好。这衰仔冇主张,身边需要咁样嘅人。
他想,五举无父无母。这一杯新抱茶,便要由他这个做师父的来饮了。
然而,五举扑通对他跪下来。他说,师父,我结婚后,恐怕不能回来店里帮手了。
荣贻生瞠目,听完缘由,跌坐在了椅子上。
他想,原是自己有眼无珠,外江女是在厨房长大,怎会怕入厨房。
他想,都说衰仔无主张,难道这也是他人主意?过半晌,他轻声问五举,我养了你十年,你为咗条外江女,说走就走?!
五举语带哽咽,声音却坚定,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当我仔来养,我这辈子都拿您当亲爹孝敬。
荣贻生闭上了眼,冷笑道,我有亲生仔,我要你孝敬?我养你是来接我的班。不是帮外江佬养出一个厨子,去烧下作的本帮菜!
五举听到这里,猛然抬起头,他说,师父,捻雀还分文武。我敬您,但我不想被养成您的打雀。不是用来和人斗,和同行斗,用来给同钦楼逞威风的!师父当年拣我,不选师兄。是看我好,还是看我孤身一人无挂碍,好留在身边?
荣贻生战战地站起来,指一指五举,厉声说,你走,我不留你,走了莫要再回来。滚!
五举抬头,眼神灼灼,好,徒弟不留后路。师父传给我的东西,我这后半世,一分也不会用。
五举对着师父,狠狠地磕了五个响头。荣贻生偏过身,不再看他,只摆一摆手。
这一晚,五举架锅起火,最后一次为师父炒莲蓉。
荣贻生走到后厨,没进去,静静看着徒弟的背影。因为使力气,五举肩胛上的肌腱鼓起来。孩子这些年,长厚实了。当年他教他炒,先是握着他的手炒,然后让他自己炒。百多斤的莲蓉。五举身量小,人生得单薄。一口大锅,像是小艇,锅铲像是船桨。他看那细路,咬着牙,手不停,眼不停。他在旁边看着,不再伸手帮他,和当年叶七一模样。
他看那莲蓉渐渐地,就滑了、黏了、稠了。他心里也高兴,细路眼睛亮了,划得更有力了。如今他长大了,艇和桨都小了。他还在划,却不知道要划到哪里去了。
他想起了云重的话,这细路,好似你年轻嗰阵时。
他看五举忽然停下来,用手背抹一抹眼睛。他终于听到了细隐的歌声,有些沙,呜咽传来,时断时续。“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这是叶七教给他的,他教给了五举。他说,学会了。往后,唱给你的徒弟听。
荣贻生让云重陪着他,一同找到了赵阿爷。
他拿出从银行取出的两条黄鱼。阿爷问,这是做什么?
他开不了口。云重说,阿爷费心,揾个好师傅,打一套赤金龙凤。
此后,每逢年节,新年、端午、中秋,五举必带上凤行,去看望师父。
每每在门口等上一两个小时,才走。经年雷打不动。
荣贻生没有再见他。
他从后厨的窗口望出去。望见那孩子,一动不动地站着。旁边的年轻妇人,紧靠着五举。但也是直着身体,站得定定的。
⊙ 鬼妹:粤俚,指西方白人女孩,略带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