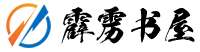伊尹论百味之本,以水为始。夫水,天下之之无味者也。何以治味者取以为先?盖其清冽然,其淡的然,然后可以调甘,加群珍,引之于至鲜,而不病其腐。
——袁枚《陶怡云诗序》
五举来到“多男”的第一天,就给荣贻生瞧见了。
照例每个周五,荣师傅会偷上半日闲。选了“多男”,多半是因为其内里格局曲折,无人打扰,落得一个自在。他长包了三楼的一处雅座。这里原是为“捻雀”客备的,所以茶资要比楼下贵上一倍。三号台靠着拐角的窗户,可俯望见外面街市的好景致。早市开了不久,只见人头攒动,上货的、讨价还价的、马姐趁着买餸聚散倾谈的。可因为有窗子隔着,不闻喧嚣,只见烟火。而另一边,则挨着楼梯,正对着影壁上“凤凰追日”的木雕。这影壁上,昔日镶嵌了一枚巨大棋盘,“棋王争霸赛”也算为“多男”在城中博了不少风头。眼下这只赤色凤凰将其取代,成为这间茶楼的新标志,在灯映下亦称得堂皇。
作为同钦楼的“大按板”,在其他茶楼喝茶,总会引发议论。旁人说,他选了“多男”的原因,不外有二。也是本港的老茶楼,企堂的規矩,和茶博士的手势都说得过去。他在这里存了几饼老茶,点心也尚好,不算迁就;更重要的,这间茶楼在同业里中上的资历,也为他的出现提供了说辞。叫人看见了,至多说是降尊纡贵,不至于有关乎业内竞争的联想与嫌疑。
然而,这雅座的提笼客们,原并不好静。过了八点,人鸟神归其位。靠南一字排开,莺莺燕燕,便是一番唱斗。原本头顶只一笼石燕,啼声尚可称得上婉转。这时七嘴八舌,渐不胜其扰。半个时辰过去了,唱累的刚静下来。北边的“打雀”,又是一番缠斗。看的人也跟着激昂,倒比雀鸟更昂奋几分,面红耳赤的。喝起彩来,更无法充耳不闻。荣师傅阖上报纸,站起来。就在这时,看见了那个孩子。
那孩子手里,拎着一个铜制的大水煲,俗称“死人头”。看着又重又沉。孩子矮小,水煲占去他三分一的身量。孩子抬着头,定定地看。目光落在那笼里两只正在打斗的“吱喳”。但在这身边的喧嚣里,他的眼睛,却是静的。没有兴奋,也没有喜乐,没有这年纪的孩子眼里所惯有的内容。这些内容,是荣贻生熟悉的,毕竟屋企已养了两个男孩。但这孩子都没有,即使在斗事的高潮,也未动声色。荣师傅不禁对这种怠工方式产生了兴趣。孩子看了很久,却自始至终没有放下手里的沉重水煲,仿佛牢记自己的责任,精神却已在“游花园”。这时,楼下传来一声断喝。这孩子像从梦中惊醒一般,本能地拎起水煲,便走向五号台。眼里竟然毫无对刚才所见的流连。荣师傅也听到了这声喝,是个略显拗口的名字:五举。
以后便常见到这孩子。因为留心,荣贻生便似乎也为他做了见证,见证了他在这茶楼里的成长。他默然地长高,原本有些拖沓的企堂衣服,渐渐合身。他的手势,也日益熟稔。孩子是勤力的,懂得与茶博士配合,懂得察言观色,也懂得见缝插针地干活。有一日,他看这孩子上楼来,忽然站住了。蹙一蹙眉头,也不动,一瞬后,荣师傅听得童音喊一声:十六少到,敬昌圆茶服侍。
过了好一会儿,听到咳嗽,继而是迟缓的步子,便见得潮风南北行的太子爷,撩着长衫下摆,提了鎏金的鸟笼慢慢走上来。孩子爽手爽脚,伺候他坐下,又将那对鲜绿的相思挂到了鸟钩上。
这一霎,荣贻生捕捉到了孩子嘴角的笑容。稍纵即逝,他大约为自己经年练就的好耳力而得意了一下。但很快,便又恢复了静穆的表情。
我问过五举山伯,荣师傅是几时决定收他为徒。他想了许久,才对我说起那次关于“文斗”与“武斗”的对话。对话因由,大约是来自“多男”的老客张经理放飞了他两条黄鱼买来的雀鸟。这只叫作“赛张飞”的吱喳,似乎从未输过,却在那次打斗中轻易落败。山伯说,记得荣师傅说了一句,英雄末路。
说这只鸟?我问。
他很肯定点一点头。他说,在这三楼的雅座上,荣师傅是长年包座,却唯一没有带雀的客人,他记得很清楚。这中年人说,英雄末路。
我又问,荣师傅没有养过雀鸟?
他说,在收了他做徒弟后,荣师傅曾经养过。而且是本港的“捻雀”客称为“打雀”的一种鸟。
我问,那,是吱喳还是画眉?
他摇摇头,说,都不是。这种鸟的名字很怪,
叫“里弄嘎”。他怕我听不懂,便用手指蘸了茶水,在桌上写下“里弄”二字。我问他,这鸟难道和上海存在什么渊源?他说,他问过他丈人家,都不知道这种鸟。他只记得师父将鸟笼在小厨房里挂着,并不拿它去打斗,是当文雀养的。但这鸟啼叫很难听,是一种石子划在玻璃上的声音,而且中气很足。渐渐整个后厨都不堪其扰。这样养了半年,据说有天笼门忘了关,这鸟便“走咗鸡”。他笑一笑,说,也有人传,是别的师傅,使唤手下“细路”,偷偷放走的。
不知为何,我忽然对这种叫“里弄嘎”的鸟产生了兴趣。在网上遍寻不着后,我决定还是做一次field work。旺角曾有著名的雀鸟街。这条叫康乐街的街道,在上世纪末被划进了旧区重建范围。重建后的成果,即当今的朗豪坊。然而这条街的人事,倒并未消逝。而是就近迁去了园圃街花园。我从牌楼走进去,便听到一片啁啾之声。沿街数笼山雀,挤挤挨挨的,笼上贴着纸“放生雀”。走了好久,进了内街,反倒是静了下来。我看到一个颇大的店铺“祥记”。鸟并不很多。铺面外头却挂着许多鸟笼,笼底下摆着一个个塑料袋。里头装着蚱蜢。袋上用粗豪的笔迹写着“30蚊”。我走进去,问那正在洗雀笼的店主,有没有“里弄嘎”。他仔细看一看,说没听说过,他阿爷可能知道。我等着下文,他说,我阿爷一早走咗啦。
我便一路走,一路问。这时烈日焦灼,街上的人和鸟,都有些恹恹的。忽然一只很斑斓的鸟,对我嘶叫了一声,像是猛兽发出。我吓了一跳,看笼上标着“南非蕉鹃雀”。它隔壁的黑羽毛的鸟,则过于安静。我发现是只鹩哥,臊眉耷眼。这鸟,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写小说《谜鸦》时的种种,不禁多看了一眼。这时有个很老的老伯从店里走出来,招呼我。我便又问起“里弄嘎”。他眼光一轮,说,我呢度冇,但我见过。我问他几时见过。他摆摆手说,咸丰年间事啦。我问他,这鸟是从上海传来的?他又摆摆手,说,系南洋雀,好嘈!
他约莫看出我的兴趣,便把我拉进了店里。我心里虽有些失望,但想他大概也寂寞。为了报偿他提供的信息,就表现出了很大耐心,听他介绍他的收藏。是不同款式的雀笼。迎门最堂皇的镇店之宝,是这行的祖师爷“卓康”所制,如今已经失传。每只鸟笼都是故事,大的是芙蓉笼,小的是绣眼笼;哪里是玉扳指,哪里是马尾弦。他说,我成间铺冇胶嘢,只只手钩都是天寿钢!
离开雀鸟花园时,已过晌午。路人行色匆匆,却都不忘看我一眼。大概因我手里拎着只古色古香的空鸟笼。
其实,荣贻生决定收五举,是在这孩子开口与他说话之前。
他之所以下了决心,是因司徒云重的一句话。
这些年,他已经惯了,有许多事都和这个女人商量。而且这些事,多半是大事。他记得许多年前,慧生说过,阿云是个女仔,有男人见识。
此前,云重从未到“多男”来,是守着分寸,也是彼此间的默契。这时她虚白着脸,面对着荣贻生。因为三号台的位置,整个茶楼,无人能看见她,唯有眼前的这个人。
两个人静默着,对望间,甚至未意识到这少年企堂的到来。五举,便在他们的无知觉间,做好了所有的事。荣师傅来“多男”,从未让茶博士服务过。茶博士张扬的表演,于他是繁文缛节。他只要两只壶。一只茶壶;一只装了八成热的滚水,用来续茶。这滚水的温度,是他的讲究。全靠企堂的大铜煲,快一些、慢一些都不对。
以往的企堂,三不五时“甩漏”。五举这孩子接了手,一回水冷了,给赵师傅好教训,以后再未行差踏错。此时见他有条不紊,洗茶、摆茶盅、开茶。眼里清静,手也稳。临走时,只如常微微躬身。似乎云重如荣贻生一般,是他长年关顾的熟客。
待他走了,两人仍是相对坐着。事情过去了,说什么也不是。说多说少都不是,索性不说了。云重揭开茶,喝一口,又喝一口。或许也是身子虚,额上便起了薄薄的汗。她不擦,继续喝。喝了一阵,放下说,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这“双红”的饮法,还是我教你的。可现在,自己倒分不出香和苦了。
她启开了茶盅,续水。却见茶盅里卧着一颗开了肚的大红枣。她便打开荣贻生跟前的茶盅,倒净了茶,里头什么都没有。
云重觉出脸上漾起了一些暖。她望一望底下,方才那个小企堂,跟着茶博士,拎着大铜煲,在不同的桌间穿梭。停下了,脚下有根,站得稳稳的。她看一眼荣贻生,开口道,这个细路,真像你后生时候。
荣贻生回家时,头脑里还回响着这句话。
打开门,家里有浓郁的中药味扑面而来,冲击了他一下,也就冲散了他头脑里的念头。秀明倚在沙发上,目光斜一斜,道,谢醒阿妈送来的,说是端午的礼。
荣贻生望见饭桌上,摆着几只龙凤纸包着的大盒。红得火一样,在这灰扑扑的房间里,有些触目。他说,端午还有半个月,现在送来?
秀明说,天下父母心,佢哋不放心自己嘅仔。讲真,你到底教成怎样?
荣贻生说,我俾心机教,佢肯学至得。
秀明抬一抬眼,说,佢阿妈知佢不生性,说按规矩管教。这行谁不是这么过来。
她慢慢地站起身,说,大仔今朝返来,在石硖尾买了几个粽。我热给你吃。
荣贻生连忙道,不用了,我同班老友记饮过早茶。你唔使理我,自己歇着罢。去过医馆了?
秀明便轻轻抚一抚心口,说,换了个医生,重开了一剂方子。先试一试吧。
荣贻生服侍她躺下。关上卧室的门,细一想,谢醒这孩子,已跟了他两年了。
收谢醒这事,当初他没听云重的。
荣贻生从窗口望一望外头。皇后大道上有些成群的中学生。男孩子穿了白恤衫、宝蓝色长裤,是圣保罗书院的学生。女孩子们则是石青色的旗袍,来自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大约这时已经下了学,在西营盘周遭吃饭闲逛。几个时髦女,手挽着手,从对面金陵戏院里走出来。打头的一个,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副墨镜戴上。
隔壁无端地,又响起了吊嗓子的声音,咿咿呀呀。是个已经退休的粤剧老倌。和荣家同年搬进来的。
算起来,从广州到香港,已近二十个寒暑。当初离开“得月”,按广府庖界的流传,是出于“政变”,这未免夸张。只是韩世江的大弟子发难,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他想想,便走了。不是怕,是为当年事,对韩师傅还抱着疚。
他来时,“同钦”虽有老号“得月”的加持,已经打开了局面,但还远非如今地位。毕竟较之广州,香港的饮食界更海纳百川些。且不论西人加入,光是各地菜系在此开枝散叶,已多了许多对手。香港人又生就中西合璧的“fusion舌头”。“太平馆”这样中体西用的新式菜馆,也便应运而生,源自广府,却赚了本港的满堂彩。
谢醒的阿爸谢蓝田,是铜锣湾义顺茶居的车头。虽久在庖厨,这人天生带些江湖气,是个社会人。对时世天生看得清,也玩得转。荣师傅与他在佛山的同乡会结识。原本以为是点头之交,没承想谢蓝田却相见恨晚,引为知己。那时年轻的荣贻生,还有几分恃才傲物。人也木讷些,并不把张扬的谢蓝田放在眼里。这本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事。后者倒不以为意,对荣师傅还有些怒其不争。他自作主张,在一次业内聚会,将荣师傅的莲蓉酥作为伴手礼,送给了香港饮食总会的上官会长。会长一尝之下,惊为天人,这由此成为荣贻生在本港声誉鹊起的起点。潛移默化间,也助他在同钦楼站稳了脚跟。嘴里不说什么,荣师傅对他是感激的。毕竟同业相轻是常态,何况又同是做白案。谢蓝田对此,倒很豪迈。只说荣师傅潜龙出渊,出人头地是迟早事,自己不过是个顺水推舟的人情,“我就系睇唔过嗰啲新潮点心佬,喺度搞搞震!”
两家来往多了,彼此也都多了照应。秀明在战时落下了顽疾,一遇换季就胸闷憋痛。到了香港倒更厉害些。也是谢家忙前忙后地给找医生。这些好,荣贻生开始都记着,想要还。后来日子久了,长了,倒处得像半个家人了。
所以,当谢蓝田提出要谢醒跟他学徒。他没怎么犹豫,便答应了。谢家夫妻谈起这孩子,也直唉声叹气。说起来,也是阴功。两公婆上年纪,才得了这个独子。荣贻生是看这细路长大,周岁时拜过自己做“契爷”。小时看着精灵,整日跟父母盘桓在茶楼里,手势看都看了个半会,说起来头头是道。可长大了,就是读不进书,转了两间官校,到底辍了学。谢蓝田便说,贻生,你两个仔几生性,读“英皇”,日后考港大要做医生律师。谁来接手你的好本事?教教不成器的契仔,也算手艺有个去处。
荣贻生心里有自己打算,却不忍拒绝谢蓝田。要说心底柔软,身在他乡,经过这些年,已有许多的变化。世故是必然的,心也冷了些。但看纵横八面的谢师傅,蹙着眉头,是老意丛生的模样,他也便点了头。
大约一个月后,他方与云重谈及此事。云重沉默了一会,说,你莫后悔便好。我不想人背后叫你“西南二伯父”。
他听后心里微微一惊,这是广府人都知道的典故。说的是不负责任、庇短护奸的老辈人。看似厚道,里头却藏着阴和恶。云重话说得重,他听得也重。便收拾了心情,想要好好教谢醒。至于教法,也便如叶七当年。旧日茶楼里的师徒制,里头还是有许多行业避忌。白案师傅连上料称斤两,尚要背着徒弟。荣贻生便格外敞亮些,将谢醒当个仔来教。云重不让他收,也是因为行内有句老话,叫“教生不教熟”。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徒弟最好是白纸一张,不收别的师傅教出来的半吊子徒弟;二是不要收熟人子弟,教训起来,话里深浅都不是,难以成才。谢醒偏两样都占了。自己以为耳濡目染,将大小按功夫,早看了学了个七七八八。由于通家之好,又是契爷,也并没有将荣贻生这个名厨当师父来待。早两年,跟爷娘学的那些,在“同钦”也都能应付,且应付得不差,居然点拨起尚要偷师度日的同辈,这便有些犯忌。可是茶楼里都知道他的来头。荣师傅不训,谁还能说什么。这个混不吝,也有他的期图,竟有两次问到荣贻生脸上,问几时教他整莲蓉。
做师父的,被他问得一愣。荣贻生本没有叶七的心机。他师父将莲蓉的绝活儿藏到了最后,临了还靠他自己悟出了一味。然而,他也觉得时机未到。这孩子问得急,他便也琢磨是不是他娘老子的意思。这样想,心里越发冷。
他知道自己还是不甘心,在等一个人。终于,等到了,是个“多男”的小企堂。白纸一张,却是上好的生宣。
这细路先说不想做打雀,让荣贻生犹豫了一下,怕他缺的是一个“勇”字。可细细听他说下来,原来是要做自己的主张。荣师傅心里动了一下。他想,当年有叶七在,除了拜师这一件事,他何曾做过自己的主张。如今若收了这个,就不好再走这条老路。成全这孩子,便是成全自己。
他想起云重的话,这细路,真像你后生时候。
可他忘了,这二十年来,他自己已经变了。
五举是在小按出师后,见到七少爷的。
可他以前见过,在“多男”。就是这个人,他们都叫他“癫佬”。唯独阿爷,叫他“先生”。
这天晚上,荣师傅领着他,携了只包裹。叫他拎了一只食盒,里头有几碟小菜,还有刚打好的双蓉月饼,压了鱼戏莲叶的花。师父亲自在饼上一一打上了大红点。
这天是中秋的正日子。五举想,自己是个孤儿。可师父有家有口,这是要带自己去哪儿。师徒二人,沿着雪厂街,到山底下,搭了电车,走到了上一层坐下。他从车窗探出头去,望望天上,是一轮透亮的圆月。月光瀑一样地流下来,铺在德辅道上。行人、车辆、两旁的店铺,便都镀上了一层银白。电车慢慢地,停靠了一个站,车铃当当地响一响。他便看清楚了外头,地面与楼宇,似乎都成了线条组成。有的线硬朗,转上了轩尼诗道,就是一条悠然的弧线。每一点轮廓都发着毛茸茸的光,是个他熟悉而陌生的香港。
他们在湾仔下了车,沿着石水渠街一直走。行至一座老旧的唐楼,门楣上写着“南昌阁”。底下是个水果店,还散发着碌柚的馨香。荣师傅和店里的老板打了个招呼,是熟稔的样子。另一边是个裁缝铺,叫“妈记”,已经收了档。门口锁着一把破旧的竹躺椅。荣师傅将躺椅搬开,侧身进去,看到一扇狭窄的小门。荣师傅敲一敲,没人应。五举听到里头传出收音机的声响,好像在播钟伟明的广播剧。收得不好,吱吱啦啦的。荣师傅便又使劲敲敲门。收音机的声音没了,有瓮声道,入来。
他们便推门进去。灯光昏暗,迎面是一张碌架床,床上坐着一个人,目光滞滞地望着他们。五举抬头,看见床架上挂着一件西装,搭着条石榴红的暗纹领带。西装袖子的肘部,被磨得“起镜面”了。五举想,是他。
先前在“多男”时,见过这个人。五举记得,他总是在周五来,将近中午时。左手搭件干湿褛,卷了一大卷报纸。
施施然进来,也不理会人。举目望,见哪桌吃得差不多了,他便走过去,一屁股坐下。也不言聲,拿起桌上剩下的点心便吃,吃得心安理得。旁人见了,还以为他是搭台的。这桌上的客,嫌恶地站起身,骂他一声“癫佬”,急急便埋单走人。也有气不忿的,便要叫经理。他安静地抬头望一眼,无辜得很。站起来,对那客鞠一躬。经理便也息事宁人。他又走到其他桌去。那桌无人,他便安心吃;有人,又骂他“黐线”,经理便请他出去。他安静往外头走,也不说话。脚上的皮鞋倒踏得山响,大概是不合脚。五举,见他脚跟上插了几块香烟纸。只有路边给人擦鞋的人才会这样,怕的是弄脏袜子。
此刻,这双皮鞋静静地搁在地上。并拢,整齐。鞋里仍插着几张香烟纸。
荣师傅将手里的东西放下,轻轻唤声,少爷。
五举心里一颤,以为听错了。但见那人,撩起身边的干湿褛披上,望一望荣师傅,也轻轻唤一声,阿响。
这裁缝铺隔篱的梯间,狭窄逼人。天花与地面,构成一个三角。连五举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尚抬不起头来。荣师傅躬下身,从墙角拎过一张折叠桌,打开。然后叫五举帮他,将食盒里的小菜端出来,又拿出一瓶酒。
他自己抄过一只凳坐下。那人望一眼五举,说,细路,对唔住,没有凳子了。
荣师傅说,唔紧要。小孩子,就让他站着好了。
那人摇一摇头,从床上坐起来。走去墙角,从报纸堆里翻翻,弯腰抱起一摞书,有点吃力。他搁在桌子边上,让五举坐在上头。
荣师傅忙要阻止他,说这坐坏了怎么办。那人浅浅笑一下,说,如今这些剧本,在人眼里似笃屎,正好用来垫屎忽。
荣师傅说,这是我新收的徒弟,叫五举。
那人说,嗯,我知道不是先前那个。那个口水多过茶。
他从床头取过一副眼镜,用衣襟擦擦,戴上。眼镜柄上缠着胶布。他打量一下五举,说,细路,我认得你。在“多男”,你赏过我一杯茶。
荣师傅不等他说下去,打开酒瓶,斟满酒,说,今天中秋,要饮多杯。
那人执起酒樽,看一看,说,玉冰烧。
荣师傅說,少爷,你记不记得?那年我回到广州,在羊肉馆子里,你请我喝玉冰烧。如今这酒,在香港可不好找呢。
那人拿起酒杯,一饮而尽。望一望,目光却直了,慢慢说,是啊,我在香港了呢。
荣师傅看他又现出些痴相,忙给他夹了一筷子菜,说,那馆子的老板说,少爷欠了他一支曲,是支什么曲?
那人蹙一下眉,眉间有“川”字。忽而舒展开,用支筷子敲一下碟,口中道,查笃撑,查笃撑……清明节鸳声切往事已随云去远,几多情无处说落花如梦似水流年……
荣师傅说,少爷,今天是中秋啊,怎么就唱起了清明呢?饮酒饮酒。
他给那人夹菜,边说,你最爱吃我娘制的素扎蹄,我可学会了呢。尝尝味道正不正?
那人饮下一杯酒,蜡黄的脸色也红润些了。他问,慧姑可好,佛山住得惯吗,要不要跟我回太史第?
荣师傅愣愣,沉默了一下,说,阿妈好好呢。过几日就来看少爷。
那人又问,我允哥好吗?大嫂好吗?
荣师傅笑笑说,他们都好呢,好挂住少爷,让我给少爷带话呢。
那人脸上就又多了一些喜色,说,我上星期给允哥寄的本子,《李香君守楼》,他收到了吧?
五举看到师父放下筷子,脸上抽搐了一下,但立刻又笑了,说,收到了。允少爷夸您写得好呢,说,省港文胆,我堃弟居二,无人敢称第一。
那人便咧开嘴笑了,露出一排白牙。原本清癯老相的脸,这时竟有了孩子气。五举听他们说话,开始是前言不搭后语。后来,荣师傅喝多了,舌头也有些大,倒是那个人,神色渐渐肃穆。他说,阿响,我最近晚上睡觉,又听到枪炮声音。白天说给裁缝店的老板娘听。她说是填海区施工动了风水,要陆沉。被我听到了。
荣师傅就说,那个老板娘,成个神婆咁。还说我有宫宅相,将来富过包玉刚,我信佢?!
这时,外头传来钟声,“当”的一声响。荣师傅抬抬眼睛,说,少爷,我要返屋企了。秀明困得浅,等门睡不安稳的。
他拿出那个包裹,说,老规矩。还是四只大红点,应承我,自己食,莫益其他人。
那人接过包裹,打开看一眼,说,我唔要。
荣师傅就说,少爷,你忘了,这是你借给我办喜事的。说好中秋还,你不信,借条还在抽屉里呢。
那人抬起苍苍的头,茫然看着荣师傅,说,系咁?
荣师傅很肯定地点点头。那人从包裹里,抽出一张钞票。然后在碌架床的上层翻找。翻了许久,翻出了一个利是封。这利是封显然用过了,皱巴巴的红。他把钞票放进利是封,塞到五举手里。
荣师傅要挡,说,少爷,非年非节。这是做什么,纵坏细路仔。
那人不管他,拨开荣师傅的胳膊,对五举说,叫我声“七叔”。
荣师傅叹口气,示意五举接过来。
五举看他一眼,唤,七叔。那人笑,问,然后说什么呢?
五举想了半天,说,恭喜发财。
那人摸摸他的头,说,傻仔,又唔系过年,叫谁发财呢。应该说……他想一想,终究没说下去。他只是抬起头,看荣师傅,说,阿响,这细路好静,像你小时候。
师徒二人走出来。那个水果店,竟然还未关门。老板靠着门打瞌睡。荣师傅就拐过去,跟他买了一个大碌柚,让五举抱着,说,给你师娘带回去。
这时,夜风吹过来,荣师傅的醉意,也醒了几分。他看着前面走着的小小身影,又想起了七少爷的话,这细路好静,像你小时候。
他想,他要谢谢七少爷,才遇到这个孩子。
每个星期五,他坐在“多男”,等的是七少爷。七少爷从未来过“同钦”。少爷清醒时,硬颈爱颜面,知他在“同钦”,便不给他找麻烦,小心翼翼地避他。这中西区的茶居,许多是梨园燕邀聚集处,原本视锡堃是省港行尊。敬他一餐半顿茶,可少爷犯起糊涂来,天王老子都敢骂。旁人先同情,渐不能容忍。竟有茶楼请了印巴籍的保安,堵在门口,不许他入内。唯有一间给他进去的,是“多男”。这是荣师傅交代下的。他就每个周五来“多男”,等少爷。他包下三楼雅座,看得见大堂,少爷却看不见他。少爷坐在了哪桌,他便提前叫人多送一笼点心。怕被发现,有时是叉烧包,有时是虾饺。一边悄悄交代下面,他来为这桌的客人埋单。他做不了许多。只想这一天,少爷能吃得安心,吃得饱。有一次,少爷怕被人赶,吃得急。吞咽间,噎住了,咳嗽起来。他在上面望见了,揪着心。人也站起来,想要下去。这时,他看见一个小企堂,放下了手里的大铜煲,倒了一杯茶,快步走过去。给锡堃饮下,一边轻轻抚着他的背,帮他顺下气。
荣师傅慢慢坐下来,他看见七少爷不咳了,定下了神。那个小企堂,便又拎起了大铜煲,疾步走去别桌了。
我问五举山伯,可记得荣师傅说的这件事。他摇摇头,说不记得了。
但他说,记得赵阿爷的话,这个人不是癫佬,有一肚子学问,要叫他先生。
至于杜七郎的学问,他跟我说过坊间流传一桩事迹。湾仔菲里明道上的“太平馆”,曾是七先生出没处。头个请了印巴保安的,也是他们。那日七先生和保安鸡同鸭讲,进不去餐厅。他叹一口气。拿出笔,在墙上题了一句,“曾经纸毁苦经营”,便拂袖而去。太平馆昔日名流汇聚,便有好事者看出,说,杜七郎是出了个无情对。这联据说到如今,从未有人对得出。
我便向几个相熟的报界前辈求证。一位《文汇报》的退休编辑,说确有此事,当年他们报上还登过。他说,这联文难在,看似文人发牢骚,可里头隐了个德文词。“纸毁”是德语zweite的音译,“二次”之意,该联是指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句末“营”为平声,可见杜七郎是成心出了个下联,叫人对上联。旁边人说,岂止!你道太平馆最出名的菜式是什么?——“瑞士鸡翼”。怎么来的?话说当年,这道菜还叫“豉油鸡翼”,有个鬼佬客吃后大赞:“Sweet!Sweet!Good!”侍应不知何意,就向一位客人请教。客人也对英文一知半解,将Sweet(甜)听成了Swiss(瑞士的)。以讹传讹,“豉油鸡翼”就此成了“瑞士鸡翼”。这杜七,鬼得很,暗讽太平馆是做不中不西的“豉油西餐”起的家。
如今这湾仔太平馆,早因重建搬去了铜锣湾的白沙道,旁边是卖南货的“老三阳”,自然也就看不到杜七郎的联文手迹。倒是应了往日报上的专栏名,“逸人逸事”,皆踪迹难觅了。
那次见面后,五举便多了一个差事。三不五时,便到那“南昌阁”,给七先生送东西。多半是吃食,应时糕点,有时也是换季衣裳。还有一两封信,上头写着七先生的名字“向锡堃”。留的是荣师傅的屋企地址。五举走时,七先生就在墙角的报纸堆里翻好久,翻出一两本书,给他带回去看。倒也不是什么精深的东西,都是市面上流行的三毫子小说,像卧龙生的《仙鹤神针》,依达的《渔港恩仇》。荣师傅看见了,就说,都是印刷公司送给你七叔的。叫他依葫芦画瓢,写写太史第的事。书他留下了,人都给骂了出去。
这天,五举照例傍晚时候去。手里挟着一只盒,外头包着永安百货的画纸,里头是条新领带。五举走到裁缝铺,看到焦黄脸的老板娘,坐在门口的躺椅上,悠哉悠哉拍乌蝇。一见他,放下手里的蒲扇,满脸堆笑将他迎進去。说衣服一早做好,就等他来。说罢从架上取下一件西装,鼠灰色,枪驳领,新崭崭。她叹口气道,你看这面料做工……算了,你一个细路懂什么。可冇得改了!我要给他量身。他倒好,说男女授受不亲。
五举按师父说的,把钱付给她。老板娘点好,满意笑笑,却又斜一下眼睛,压低声音说,说给你师父听,唔好再给你七叔钱。佢傻傻啲,将啲钱跟生果档换成散纸,周街派给路边乞丐。我亲眼见到的。
两人敲开七先生的门。锡堃背对他们,床上散了一床的纸,口中念念有词。五举看不懂,不知那是工尺谱。叫一声七叔,他回过头来,眼清目亮,不是往日恹恹的混浊样。
老板娘就要给他穿上西装。他一闪身子,说我自己来。穿上了,老板娘啧啧称赞,说,你瞧我这眼力,膊头袖子都啱啱好!七先生真是衣服架子。
锡堃脸上也有喜色。老板娘说,先生精神好。穿得那么排场,唔通要去饮咩?
锡堃笑笑,不理她。老板娘就凑趣地出去了。
五举帮他将领带打上。锡堃自己从桌上拿过一只眼镜盒,小心翼翼地取出副眼镜戴上。不是原来那副,也是新的,眼镜腿上无胶布。
五举看着,也赞叹。想师父说得没错,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七先生收拾得体面,斯斯文文,成个港大教授咁。
他便也问,七叔当真要去饮?
锡堃笑笑,脸冲门上扬一扬。五举这才看到,门背后贴着戏院的海报。有利舞台的,有普庆戏院的,有太平戏院的。有新有旧,贴得密密麻麻。五举想,以往就未有留意到。这些戏码有些他听过,因称得上家喻户晓。像是《跨凤成龙》《百花亭赠剑》《双仙拜月亭》。赵阿爷迷陈凤仙,连他也哼得出“更闻鹤唳叫泣南岗,亭畔拜仙踪降”。
五举便问,七叔要去看大戏?
锡堃点点头,脸上神情稍肃穆起来,眼里头仍有一点潋滟的光。他说,我徒弟请我看他写的戏。
五举看海报上,编剧都写的是一个名字“宋子游”。这名字他也不生,阿爷常提起,是香港鼎鼎大名的编剧。五举想,这个人,竟是七先生的徒弟。
锡堃眼神晃一下,似看见了他的心事。他将西装慢慢脱下来,齐整地挂好在床架上。手在袖子上掸一掸。轻轻说,我不成了,至少还有这个徒弟。当年他在太史第门口,唱我的《独钓江雪》。故意唱得荒腔走板,我才收了他。如今太史第没了,阿爸也给我克死了。我就剩下这么个徒弟了。
锡堃回过身,从床上捡起一页,仿若自语,他写好这出《紫钗记》,同你师父一道来见我。我心窄,没脸,不肯见他。他在门口站定了,说,七哥,当年我唱你的戏,你让我进去了。如今我就唱自己写的。
就是这折《灯街拾翠》。锡堃便对着那页纸,对着五举唱:
携书剑,滞京华。路有招贤黄榜挂,飘零空负盖世才华。老儒生,满腹牢骚话。科科落第居人下,处处长赊酒饭茶。问何日文章有价?混龙蛇,难分真与假。一俟秋闱经试罢,观灯闹酒度韶华,愿不负十年窗下。
我听得忿气,就将门打开了。看他站在门口,笑笑哋看我。他说,七哥,我唱了李益唱崔允明,唱了崔允明又唱韦夏卿。师父,你终于肯见我了。
你看,过了几十年了,他还是来激将我。举仔啊,你说我人活一世,到头来,就剩下这么个徒弟了。
锡堃将眼镜取下来,撩起衣襟擦一擦。眯着眼睛,目光散着,渐渐汇聚在门上的海报,不再说话。
五举说,七叔,你莫唔开心。
锡堃回过神来,说,不不,我好开心。你要俾心机,同你师父学,学整莲蓉月饼。学会了,有出息,周街都买来食。你师父都唔知会几开心。
第二日清晨,天麻麻亮。还未上客。“同钦”的后厨已在忙碌,预备开早市,荣师傅督场。
这时候,外头有嘈杂声。荣师傅便出去,看见企堂拦着一个人,不让他进来。荣师傅一看,是七少爷。
他忙喝退企堂。想平日锡堃从不来“同钦”找他,请都不来。只见锡堃脸色惶惶的,身上还穿着新西装。领带歪在了一边,头发散在额头上。他走过去,笑笑问,少爷,昨天的戏好看?
锡堃愣愣地看他,忽然开了口。他说,阿响,阿宋死了。
荣师傅也愣住。没等他回过神,锡堃便哭了起来,开始是哽咽,忽然,哭得惊天动地。后厨的人都出来了,围成一圈看。看这不知哪里来的癫佬,站在茶楼大堂的中央,哭得像个孩子,不管不顾。荣师傅慢慢走过去,将手放在锡堃肩头。那手也趁着肩膀剧烈抖动。他心下一震,便将锡堃抱住了。荣师傅抱住他,闭上眼睛。觉得怀里的人,怎么这么薄,全是骨头。那时候,是个温暖厚实的后生啊。如今,怎么像片落叶似的薄。
一大早的报纸出来了。头版都是宋子游亡故的消息。在利舞台,新戏演到第五场,忽然心
梗倒在观众席上。送到圣保禄医院,翌日清晨不治。报纸配的照片,上头是剧照,下面是他观戏的现场照片。脸上微笑,踌躇满志的模样。旁边坐的人,也笑吟吟的,是师父杜七郎。
荣师傅开了酒店房,看着七少爷。戏曲总会的人说,万国殡仪馆的追思会就不要他去了。到时有媒体到场,还要体体面面地,经不起一番折腾。
第二天中午,锡堃跑了出去。先摸到了殡仪馆,灵堂挨个找,找不见。红磡沿途街道,报摊上,到处都是徒弟的遗照。他抢过报纸就撕,撕了扔在地上。又跑去第二个报摊,接着撕。有人报警,警察来了,拦不住他。他又打又骂,几个警察联合起来,才制服了,送上了警车。
在差馆里,他倒安静了。荣师傅赶过来,来保释。警察说,几个手足给他打伤,进来倒安静了。问什么,来回都只有一句话。
从差馆出来,杜七郎给送进了青山精神病院。媒体写,这是他第三次入院。上次是四年前,那時他的新戏《泣残红》,口碑票房双仆街。
夜里头,荣贻生到了云重那里。什么话也不说,脱下衣服,便与她造爱。
做完了,大汗淋漓的,点上一支烟。也不抽,烟灰燃着燃着,落下来。落到身上,烫得自己猛然一抖。他将烟掐灭了,捻在烟灰缸里。人还是呆呆的。云重起身,要穿上衣服,被他一把拉住。手劲很大,云重被拽得跌坐在床上,他翻过身,把头深深埋在女人胸前,也不动。半晌,云重感到有滚热的水,沿着乳房流下来,流得很汹涌。她使劲抬起男人的头,看他已是泪流满面。她静静看这男人,想这些年,他也有些见老了,脸上有浅浅褶皱。那泪水凝在嘴角的法令纹里,没有流下来,晶亮的一涡。
待平息了,荣贻生说,阿云,你知道七少爷在差馆里,来回都只有一句话。他说,我就剩下这么个徒弟了。
我细细想想,当年宋子游在太史第门口等。若不是我多说了一句话,阿宋兴许就走了。少爷还怎么收得成这个徒弟。后来宋子游名头大了,少爷面皮薄,不肯认这个徒弟。又是我求他,带着他跟少爷见面。我只想少爷心里,还能有个盼头和牵挂。你说当年,少爷在宝莲寺里,给鬼佬讲佛经。我远远看着,精神已经好了不少。要是我不急着找到他,报老太史的丧。他不是魂不守舍,怎么会从火车上摔下来。何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
云重听着这男人的呼吸,随自己的心跳起伏,渐渐没那么重浊了,方开口道,你说七少爷跟人讲佛经,他一定懂得,有因就有果。你既不是因,也不是果。因缘前定,没有你,也还有其他人。
荣贻生抬起头,直愣愣地看她,阿云,那你是我的因,还是我的果?
云重坐起来,披上衣服,轻轻说,你回去吧。秀明困得浅。夜里等着门,她睡不安稳。
⊙ 马姐:亦作“妈姐”,粤港地区指女家佣。
⊙ 胶嘢:粤俚,指假货、赝品。
⊙ 甩漏:粤语,有错漏、缺陷。
⊙ 搭台:在粤港,指互不相识的顾客坐在同一围台上一起用餐,多出现在茶楼繁忙时段。
⊙ 黐線:粤语粗口,神经兮兮。
⊙ 饮:此处指赴宴喝喜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