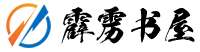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我没生气,你又在生气什么?”◎
——
天边最后一丝余晖散尽, 天色暗了下来。
方圆几里都是荒地的偏僻郊外难得一点烛光闪烁,隔着一道门扉烛光更显幽暗。
店小二和伙夫在门外守了许久,就差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在听到一声属于女子的痛呼声之后, 店小二本想冲进去被伙夫摁住肩膀压了下来。不过那一声属于女子的短呼急促且短暂, 单一声便再也没有了,好似一场错觉, 如果不是两人都听到的话真以为是听岔了呢。
伙夫、店小二两人对视了一眼, 彼此都有些酸。
“他娘的, 这瞎和尚倒是个会玩儿的。”
伙夫面色阴沉,按以往他们早就痛下杀手甚至分好了赃擦干了刀。但今天不同, 大魏新国君极其崇尚佛学道法, 僧人、道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等闲杀不得。因此这俩人还颇有些顾忌,不过在听到确确实实属于女子的呼喊声之后,最后一丝顾虑也没有了。
这算哪门子正经和尚, 他们可是在替天行道!
伙夫放下了压在店小二肩上的手,扬了扬下颚,精光从浑浊的眼里一闪而过:“不过一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瞎和尚, 我一人足矣。毕竟大小是个和尚,惹了一身骚就不好了。你下去把车备好, 这单干了我们就撤。”
“好嘞!”
店小二点头转身走之际突然间又停出了脚步, 扭头对伙夫搓着手笑:
“哥, 那声儿听得我心里头直痒痒的……别玩儿坏了,还有我呢。”
“德性!光这一声儿便知是个尤物, 哪舍得玩儿坏?放心吧, 少不了你的。”
店小二嘿嘿一笑旋即下了楼, 而伙夫敛住笑, 搓了搓自己的脸后,叩门:
“客官,您要的干净水儿来了。”
门霎时应声打开。
伙夫愣了一下,门开了却没见到人,他略略定神后探了进去,余光瞥见榻上悬着的一双白得晃人的小脚,还未瞧清楚,一道漠然的声线传来:
“看什么?”
伙夫一惊,猛的一抬头,不知何时摩柯早已出现在他面前,神出鬼没的,到了跟头才发现此人身量极高,站在他面前却足足高了他两个头,瞧着瘦高而已却带着极强的压迫感,就这般俯视着他不知看了多久,虽然眼上缚了条丝带,但……莫名就觉得被盯上了。
好似被野兽盯住一般,伙夫心头一跳,悬挂在腕上的长布跟着掉了下来也浑然不知。
摩柯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启唇,一字一句道:
“送进来。”
“唉……好,好。小的这就送过来。”
伙夫忙不迭将早已备好的一桶桶热水由外提了进来,他不敢多看,也不敢抬头,一直弓着腰只盯着手里的水桶,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亦或是什么,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威压……他后知后觉才发现是“恐惧”,是莫名产生的如千斤坠般的恐惧压在他的肩颈之上,叫他一刻也不敢抬起头,不一会儿浑身全被冷汗浸湿,机械的将一桶又一桶热水灌进浴桶里。即便如此,始终有一道森冷的视线死死锁在他身上。
他做惯了刀口舔血的活,对这样的视线极其的敏感,他毫不怀疑,只要他再多乱看一眼就会……就会……反正就会发生不好的事。
邪了门儿了,杀人越货十数年,第一次如此惧怕,如潮水般的莫可名状的恐惧越积越多叫他手一抖,木桶径直坠落,热水将要泼下去时,一只手牢牢抓住木桶的把手。
伙夫一愣,抬眸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双立在他身前的白的晃人的玲珑小脚,然后是一道背对着他的身着素装的纤细又婀娜的背影。
阿沅接过木桶将热水倒进浴桶里,转头将木桶递给他:
“给。”
伙夫顺着声儿抬头:“谢……”
才说一字就卡在喉头,愣愣地看着少女许久未说话。
氲氨的烛光跃映在少女一张白瓷无暇的面庞上,雪肤红唇,如瀑般的长发直到腰间,美得不似凡人好似勾魂夺魄的精魅一般,伙夫直接呆在原地,木桶也忘了接过来。
倏然,一道冷沉的声音响起:
“下去。”
伙夫这才如梦初醒,忙不迭、几乎同手同脚退出房,他甫一踏出门,门就被一阵劲风狠狠扫过,重重关上。
伙夫一惊,心脏吓得差点跳了出来。退出房后才发现,他的手居然在抖。
他龇牙咧嘴甩了半天手才将掌心的战栗挥去,盯着紧扣的门扉,浑浊的双眸里多了一丝志在必得。
--------------------------------------------------------------------------
随着木门重力地合上,屋内豆大的烛火灭了又亮起。
阿沅松手,木桶“咣当”一声落在地上。
她小跳着坐在榻上,两只白晃晃的脚丫子晃荡着,歪着头盯着摩柯眼神挑衅然而说出的话却是乖巧的:
“你不会又要说我招惹他吧?”
反正他又看不见。
自从阿沅答应他之后,摩柯好像默许了她什么不再拘着她,不再让她像只娃娃般任人摆布。现在她可以说话、也可以随意走动前提是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
阿沅还从来不知道摩柯控制欲这么强。
不,他又不是摩柯。
他是侵占摩柯身躯的邪物。
他不是摩柯。
一想起这人如此加害她此刻又胁迫她,还侵占了她珍贵的朋友的身躯,阿沅惊怒交加却不得不屈服于他,又是恨又是恼,即便为他人鱼肉,阿沅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想着想着眼神中越加是没有藏着掖着的怨恨和挑衅,忍不住激他:
“怎么不说话?”
摩柯望着她的方向,略略一顿才道:“我没生气。”
阿沅笑:“这会儿不觉得我招惹别人了呀?”
“我知你没有。”摩柯眉心蹙了蹙,“别闹了。”
阿沅最讨厌这样,最讨厌他这幅正人君子的模样明明他对她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情,明明这不是他,他为何要装作摩柯的样子??
他霸占摩柯的身躯还不够,还要仿着摩柯的性子做样子给谁看?他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
他得到的还不够吗?
摩柯忽然道:“我没生气,你又在生气什么?”
她没出声,可是他还是敏感的觉察出她生气了,这点真是和摩柯一模一样。
如果不是她知道摩柯不会骗她,阿沅有时真怀疑这人是装的瞎子。
阿沅冷笑:“我生气什么关你什么事?怎么,又想杀我啊?”
摩柯紧紧盯了她一会儿,忽的走向她。
阿沅突然浑身紧绷,背于身后的手紧紧的攥住单薄的锦被。
直到摩柯靠近,就在她跟前进无可进的位置,她浑身宛如一张拉满弦的弓紧绷到极致。幸而他看不见,如果他能瞧见的话,就会发现她现在就像一只浑身炸了毛的猫。
摩柯略略站定了一瞬,忽而侧坐于她身后,指尖沿着阿沅的手臂往上,两手轻柔又不失强硬地扶住她的脑袋,见指腹下的人僵直着身躯不肯动,摩柯神色未动只淡淡道:
“我以为你习惯了。”
阿沅咬牙,绞着锦被的指骨因过分用力而发白,从齿关里咬出来话:“……我可以动了,就不劳烦你替我梳洗了。”
摩柯想也不想回绝了:“不行。”
阿沅怒:“为什么不行!”
摩柯理所当然:“你洗的不干净。”
阿沅愣了下:“?”
“???!”
阿沅勃然大怒,本欲站起甩开他的手的,怒而回眸便对上了一双覆着丝带的眼,摩柯脸上没什么表情,因着丝带的掩藏更难辨喜怒,他堪称和煦甚至有商有量的对她道:
“俗语道‘小树不修不直溜’,可是我并不喜欢。佛曰‘种如是因,收如是果’,万般皆有定数。我喜欢你按照自己的心意自由的生长,前提是,不要忤逆我。”摩柯略一顿,扶着她脑袋的手指很轻的触了触指腹下的肌肤,“我不想不开心,也不想那么做。所以…别逼我好吗?”
阿沅直直盯着面前这双覆着丝带的眼,许久许久牙关才松了些,闭上了眼。
见少女许久没有牙尖嘴利的反驳便是应允了,摩柯心情陡地愉快起来,他轻柔地抚着她两侧的太阳穴,引着她的脑袋枕在他的膝上,而长发的另一端便在他们身前泛着热气的浴桶里。
摩柯一手掬起一捧水,自上而下淋湿她的发,而另一只手穿梭在她湿软的发中熟练的浣洗着。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他又开始像对待娃娃一样对待她。
阿沅紧闭着双眼忍耐着,忍耐他用方巾一寸寸绞净她的发,然后掌心相贴,灵力化为热气一点点烘干她的发。
接着是双手,从指尖到手掌,每根青葱一般的手指都细细的清洗了两遍,然后是双足。
摩柯的双手碰到阿沅脚背的时候,阿沅极轻的战栗了一瞬,下意识要缩回去被摩柯抓住了,牢牢攥在手心。
因前些日子在林间不断被追逐,她浑身、尤其是双足被树枝、碎石剐蹭的鲜血淋漓,血肉粘着白袜,撕下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疼,尤其她身为画皮鬼,一身皮肉异常娇嫩,有了伤便很难再好,那疤痕歪歪扭扭的自己瞧着都很糟心,不知怎的落入了摩柯的眼里。在他毫不吝啬的如潮水般浩瀚灵力的修复下伤口很快便好了,甚至肌肤更加的娇嫩,然伤口好了之后带来更令她糟心的事——摩柯……不,是附在摩柯身上该死的大黑蛇,似乎对她的……足有某种执念,不仅见不得一点脏污,阿沅甚至觉得,这黑蛇将她变成不能行动的废人就是为了不让她走路。
不能行走,她的足便不会受伤,也就不会变脏。
每当这个时候最是难熬,阿沅忍着,忍着他沾湿巾帕一点一点、从足踝到脚背,再细细擦拭过每根脚趾,终于巾帕落在柔软的脚心,热气消散了,巾帕沁凉。阿沅心里略微一松,知道酷刑快结束了,果然脚心湿润的触感消失了,紧跟着摩柯忽然起身,脚步渐行渐远,木门“啪嗒”一声响,阿沅愣了下睁开眼,只见摩柯端了盆水走了进来。
盆内徐徐蒸腾而上的热气柔和了他的眉眼,软化了他眉眼里丝丝入扣的邪肆妖异,恍惚间阿沅好像又见到了她所熟悉的摩柯。
哪怕手上做着最最质朴的活仍是那么圣洁而高雅。
摩柯端着水盆走到她面前,云雾消散之际阿沅也清醒了过来,这人是该死的蛇妖,这人怎配与摩柯相提并论?
阿沅从榻上只起身,不解:“你去干嘛?端水来干嘛?”
摩柯答非所问:“我以为你会闭眼到最后。”
“我原是这样想的……”
阿沅嘀咕着,只见摩柯将盛着热水的银盆放在地上,同样单膝跪下地上,两手在榻上摸索了片刻,很快就寻到了她的足,一手握住她一只脚踝往下,令她柔软的脚心踩在他的膝上……
阿沅懵了一瞬,连忙抽回脚,整个人连滚带爬缩在床角,两手死死抱住自己的小腿,戒备地瞪着摩柯:“你还想干嘛!”
摩柯握着她脚踝的手还僵在空中,闻言居然一脸无辜的样子:
“水凉了,换盆水。”
“不是、不是都擦了一遍了吗!”
摩柯答得简单:“不够。”
阿沅急了:“你平常不都擦拭过一遍就行了么!”
快点结束吧,她娘的她快受不了了!
不知为何摩柯今日特别估固执:“今天不行。”
阿沅难以理解:“为何?!”
摩柯淡色的唇抿的紧紧的,油盐不进的模样:“今天就是不行。”
阿沅直接哽住:“……”
其实这条大黑蛇除了偶尔变、态了点,大多数时候还是有商有量,脾气很好的。不然阿沅也总不会将他和摩柯认错。不过今天……是吃错药了???
在阿沅哽住之际,摩柯居然直接站起,只摸索了片刻,犹如抓小鸡一般将她从床脚逮了过来,半强硬的将她的足摁在他的膝上,暖湿的巾帕再次覆在阿沅的脚背上,往常这人动作轻柔的很,好似真的在护娇嫩的花朵一般生怕弄伤了她,但今天不同,他来来回回带着狠擦拭了三次了,脚背都擦红了还不停下,阿沅眉头微蹙本想呼痛制止住他,张口的一瞬间福至灵心,带着试探更多是难以置信:
“你不会是……你不会是因为那伙夫看了我的脚就……不对。”这荒唐的想法才冒出头就被阿沅掐断了,“你又看不见怎么会知道……”
摩柯声音清冷难辨喜怒:“所以确实入了他的眼。”
阿沅:“……”
阿沅后知后觉,不由拔高声音:“你套我话?不是……这很重要吗?他又没碰到我,只是看了一眼……”
摩柯不再回答,或者说——用行动回答了。
他整整又将阿沅的双足来来回回擦拭了十几次,几乎快剥下一层皮来才终于停了手。手背虚虚擦拭了下脑门沁出的汗,丝带下竖瞳闪烁了下又隐去,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干净了。”
阿沅只觉得双足火辣辣的,她嘴角轻嘶着,白了他一眼。
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洗净手,开始寻找她的唇。
这是他将她作娃娃对待,一整套繁琐的伺候下来后,最后一道工序了。
夜夜皆是如此。
她感觉到他冰冷的指腹游移在自己的面庞之上,她暗自吸一口气咬紧牙关,无声忍耐着。双手紧紧的攥着锦被,手背青筋鼓起。
阿沅始终不能习惯。
如何能习惯?
她终于忍不住,掀开眼帘问他:
“我妥协了这么多,你是不是也该答应我一件事?”
摩柯指尖一顿:“什么?”
“我要见摩柯。”
摩柯倏然一笑:“我说过了,我就是摩……”
阿沅忍怒:“我要见真正的摩柯。”
摩柯敛起嘴角的笑意,正色道:“出家人不打诳语,无论你信不信,无论你问多少次,我的回答还是如此,我就是摩柯。”
一瞬间指甲嵌进掌心的皮肉内,阿沅咬着唇,猫瞳倏然红了一圈,她扁了扁嘴,闭上眼,权当自己是个死人!
她忍受着屈辱一般的折磨,忍受着他沾着血的指尖细细研磨她的唇珠,她忍耐着忍耐着,终于他的手指从她口中探了出来,隐约牵动一根银丝落在嘴角上。
阿沅松了口气,她知道酷刑已经结束了,然而停滞于嘴角处的指尖许久都不曾有动静。等了许久许久,久到她都不耐烦了,终于睁开眼,却见摩柯似是茫然的模样,似怔忪。
阿沅眉头微蹙:“喂……”
字句还未完全吐出,停滞在她唇角的指尖又开始动了。
从唇缝滑落到下颚,指腹轻点着下颚,阿沅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指尖越往越下,沿着她的颈线一直往下——
一直到小巧精致的锁骨再往下即将没入交叠的衣领中时,被阿沅一把抓住了手。
“你想干什么!”
摩柯似是惊醒一般落于她衣领前的指尖剧烈一颤,僵在了原地。
阿沅不是傻子,一知道他对自己有怎样的龌龊心思之后,她勃然大怒,一是因为被轻视被轻薄,二是羞辱。他不仅羞辱了她,还羞辱了摩柯!摩柯才不是这样的人,摩柯才不会做这样的禽兽行径,而他占据了摩柯的躯体,却做着这样的事情,那便无论如何也忍耐不了,即便死在他手中又如何!
阿沅一把推开了他,从床榻上挣扎着跳下来,抢过铜镜前的一把剪子,尖口对着摩柯,怒喝:
“你给我从摩柯的身体里面滚出来,你不配霸占他的躯体,滚出来!”
摩柯在短暂的失神之后,嗤笑一声,指尖尚还淌着血,薄唇更殷红似妖:“我告诉过你了,我就是摩柯。我呢,敢做摩柯想做的事,敢做他不敢做的事。你口口声声说摩柯是你的朋友,但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你了解他什么?
你知道他一心求佛,可你知道他画了满屋满墙你么?你知道你日间守在榻前照顾他,而他日日夜夜都在做些什么梦?你以为仅仅梦到他的母妃么?
你根本不了解他。
他是男人,正常男人会做的梦他也会做。知道那个夜夜出现在他梦中的女子是谁么?知道他会在梦中对那女子做什么吗?呵……”
摩柯轻笑一声,无视阿沅手中的剪子一步步走向她,“可比我对你做的过分多了,想听么?”
“你胡说!你胡说!”阿沅攥着剪子紧紧护在身前,“我不会信你的,从摩柯身体里滚出来!”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你还不知道我说的是谁么?也罢。”丝带下隐约透出一抹暗紫幽光,摩柯声音陡地沉了几分,“让我来告诉,摩柯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
摩柯说完上前一步,阿沅彻底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摩柯不过甩了下袖子,阿沅手中的剪子便不受控的飞了出去,他再往前一步,便与她只剩半臂的距离,远远看去,阿沅完完全全被纳入怀里似的。
摩柯不再犹豫,伸手抚向少女白的晃人的颈部,指尖将将触及一抹令人眷恋而心惊的软腻之时,像是被针扎了一般,摩柯浑身骤然一颤,丝带之下瞳孔震荡,喉间发出一声低吼,忽而踉踉跄跄撞开门跑了出去!
阿沅愣住了,定定地望着他跑去的方向看了许久,喃喃着:“摩…柯……”
一定是摩柯阻止了他!
骤然惊醒一般,阿沅连忙将落在地上的剪子捡起,将木门合拢上,背部紧紧地贴在门上,握着剪子的双手震颤着,这时才惊觉出了一身冷汗。
做完这一切之后,方才像泄了气一般,紧绷的身躯松弛了下来,瘫软在地。
她双眸放空了一会儿,消化了一会儿今日、包括之前发生的种种荒唐事,失焦的双眸逐渐明亮而坚定。
她必须要跑出去,一定要跑出去!
她不能再像个娃娃一样任他摆布,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她一定要做些什么!
为了她自己也为了摩柯,一定……一定要做些什么!
--------------------------------------------------------------------------
夜半三更,月儿藏在乌云之后,蒙着一层云雾,本就暗淡的月光更显惨淡。
摩柯冲出客栈后,冲进一片黑暗中不知跑了多久,多久。
直到没有人味儿了他才停了下来。
如果此时有人在身边,一定会被他吓到。他周身青麟攒动,丝带在奔跑中不知何时掉了,一双竖瞳赫然出现在寂静的夜中,闪烁着诡谲的幽光。
他剧烈喘息着,不断以头抢地,不断的用双手捶打自己的头颅,犹如困兽一般怒吼着:
“从我身体里面滚出去!你怎么敢……你怎么敢这么对她!你怎么敢碰她!滚出去!从我体内滚出去!”
本愤怒的他陡地又变做另一个模样,痴痴笑笑,是裂变的另一个人格:“明明是你想做的事,我帮你做到了,你也享受到了,怎么?想推得一干二净啊?嗯?有没有搞错,我可是你,你就是我,而她是我们的掌中物,跑不了。还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在怕什么?懦夫。”
本嗤笑的他又变作另一个模样,是痛苦的、愤怒的,犹如困兽的他。
他双手紧紧捂着自己的脑袋,手背青筋毕露,低吼着:
“滚出去,我叫你滚出去!”
很快他又是嘲讽的模样,笑着讽刺着:“一个两个都叫我滚出去,她不知道,你还能不知道么小摩柯?我存活了数百年,一旦被我寄生便是死路一条。这些年来本座不断的更换躯体,这么多年、这么多飞鸟走禽、仙魔人妖,只有你,唯独只有你存活下来了。只有你配得与本座共享一体,唯有你配得与本座共享永生,你该觉得荣幸才是。”
紧接着又变做痛苦的他。他浑身都是血,即便他将头撞向地上的顽石,然而伤口很快就会被清理,再次完好无缺。无论他怎么伤害自己受伤的皮肉,很快就会被青麟完美覆盖。
“别挣扎了,你知道这是没用的。”
摩柯喘着粗气,他的目光继续游移着,忽然看到了不远处的深潭。
他大步走了过去,水面上印着一张与他一模一样的脸,那张脸是邪肆的,妖冶的。
他笑着同他说:“心爱的女人就在身边,而你却跟木头一样,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小摩柯,何不接受本座?”
“蛇,五百年化蛟,千年化龙。你不是想入佛门么?做个佛门小沙弥有何意思?本座带你做真正的佛!你知你我成佛只差什么吗?只差一块小小的龙鳞。而这块龙鳞你我都知道在哪儿,不是么?”
他一掌狠狠击打在水面上,霎时深潭卷起数丈波澜,那张肖似他的、妖冶邪肆的男人的脸消失了,而他踱步,一步一步走向深潭中心。
任由冰冷的潭水淹没他的口鼻,窒息感一点点覆顶,最后完全淹没他。
就……这样吧。
都说人死前脑海里会像走马观花一样,浮现生平经历。
摩柯想,他好像也见到了他的走马花。
他见到了小小的,他自己。
——
摩柯的童年并不快乐。
他也很少笑,完全不是现在这般清风晓月的模样,他小时候极少笑,或许说从未笑过。
所有人都说,他是随了他的生母容妃。
容妃不爱笑,即便是面对他,面对她的独子,面对圣上最小也是最宠爱的小九,甚至是面对圣上,容妃也是不笑的。
只有一人除外,那便是二皇子和三公主的生母皇后殿下。
所有人都知道容妃身份尴尬,容妃本是皇后身边的随侍丫鬟,一个小小的丫鬟,竟然趁圣上醉酒,爬上圣上的床,勾引圣上成功诞下龙子,一朝麻雀变凤凰。
所有人看似鄙夷容妃,实则嫉妒的眼都红了。
可所有人都道容妃心机颇深,荣宠享尽,只有摩柯知道他娘并不快乐。
他娘,不仅不快乐,她非常痛苦。
而这份痛苦顺利转嫁到他身上。
所有人都以为是容妃拼命爬圣上的床,只有摩柯知道,是他娘一次一次将圣上从床榻上赶了下来。
娘一点也不喜欢父皇。
甚至为了避免和父皇同床,娘还央求他,央求他夜夜啼哭,夜夜被梦魇缠身,唯有和母妃同寝,伴母妃身侧安睡才好了些。
因此确也替娘挡了不少别人求也求不来的盛宠。
父皇也因此恼过他,恼他不识趣,可他仍是夜夜啼哭,夜夜寻容妃,夜夜扰父皇雅兴,所有人背地里都道他是个白痴,他无妨,只要娘开心就行。
曾经,贵为九皇子的他和容妃是多么的受宠,盛宠之下,即便是二皇子玉宵和三公主玉陶从来也只敢在背地里使小绊子,没有人敢动他,谁人不知她是圣上疼爱的小九,而他母妃更是圣上心尖尖上的人?
雷霆雨露都是君恩,对摩柯和容妃来说从来都是雨露君恩。
对于别人都是这个道理,对于容妃却不是这么回事。
摩柯知道他娘不仅不爱戴父皇,甚至恨他。
恨他灌醉了她,恨他欺凌了她,恨他为什么天下那么多女子非要她,恨他令她与皇后娘娘生离。
很多人都不知,容妃不仅仅是皇后娘娘入宫前的贴身小婢,更是满门忠烈,良将之后,因圣上听信谗言,负了良臣的心,容妃一家满门抄斩,独独她被当年的手帕交,也正是二皇子三公主的生母皇后娘娘拼命护下才侥幸苟活了一条命。
她曾和皇后娘娘执手看遍京都的繁花,也曾和皇后娘娘吃过大街小巷的美食,她们也曾效仿过张飞关羽桃园三结义义结金兰,她们曾经无话不谈无话不说,她们立誓要永远在一起,即便入了宫,她也要陪在皇后娘娘身边,老了也不嫁人,除非皇后娘娘赶她走。
可她终究负了皇后娘娘。
负了这个世上对她最好的人,负了这个世上她最不该辜负的人。
她怎能如此???
她怎能如此!
“人可以贫外物却不能穷了脊梁,这是你太爷爷教与我的,现下我也教与你,望你记在心里时时不能忘,千万不能……像娘一样啊。”
容妃总是看着他说着说着,捂着唇咳下一口血被她隐在帕里。
所有人都知道容妃和皇后的关系,也都知道向来贤德大度的皇后娘娘为何单单与容妃不对付,甚至严明此生不会再与容妃相见。
而容妃总是雷打不动的去请安,即便吃了闭门羹也日日去,晨起去一次,午间再去一次,直到有人传来那是在给皇后娘娘耀武扬威呢,容妃这才作罢。
可是自那次之后,容妃身子一日不如一日,渐渐破败了。
“娘!”
容妃摆了摆手,将藏了血污的帕子藏在身后,忽然道:
“今日圣上去太傅那儿考你们学业了?”
年仅六岁的小摩柯懂事的点点头:“父皇让我们两两对对子,儿臣都对出来了!”
小小糯米团似的玉雕似的小人极力拱手学做大人的模样,神情却是藏不住的神气和得意。
一双漂亮似明珠的双眸眨巴眨巴望着容妃,好似身后有只隐性的尾巴摇啊摇的,仿佛再说:快夸我呀!快夸我呀!
容妃怎么会瞧不见,她脸色淡淡,轻轻“恩”了一声,哪怕只一声,小摩柯也高兴着红了脸,一双大眼睛越加闪烁。
容妃忽然又道:“与你对对子的是谁?哪个公子王孙?”
小摩柯顿了下,略略低下头:“是……是二哥哥。”
“玉宵?”原有几分怀念的暖色消失的一干二净,苍白的丽容全是怒色,容妃狠狠一拍桌子,“谁让你赢了玉宵?!你……你……”
容妃霎时蹲下来,小摩柯吓得想跑,被容妃死死抓住双肩,容妃抓着小小人儿的双肩,尖利的长长的指甲嵌进孩童娇嫩的皮肉内,小摩柯霎时迸出了泪花,低声道:
“娘……我疼。”
容妃或许没听到,又或许……并不在意。她失控地低吼着:“我跟你说了什么?!你是不是忘了我跟你说过什么?!!我说……咳咳……咳咳咳!”
“娘……”
“别叫我娘!”容妃甩开他的手,“你既然不听我的话,还叫我娘做什么!”
“娘……娘,娘……我知道错了娘……”
“你做错了什么?”
“我不该……我不该赢过二哥哥……我、我不该……我错了娘,我下次一定……”
“摩柯,我与你说过的,你要与任何人争我不管你,唯独二皇子三公主不行!你到底要我讲多少遍才能记住?啊?你是不是……是不是要气死娘才行!”
摩柯看到小小的自己在哭:“娘我错了……娘你别不要我……我错了娘,我错了……我不与他争,我不与他抢,娘你别不理我娘,娘……”
深潭之中的摩柯终于感觉到了溺水的滋味。
他漠然看着,仿佛在旁观他人的人生。小小的他还在长大,很快,到了七岁,拙劣的谎言再也用不上了。
他长大了,无法再与母妃同寝。
无法再帮娘了。
许多人说起他都会叹一句,小时姣姣,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真乃神童。接着便会跟一句“可惜……可惜。”
可惜长大后泯然众人矣,文采、策略不过尔尔,更无法与天资聪颖的二皇子相提并论。
十岁生辰那日,圣上本想与他封爵封地,被摩柯通通拒了,圣上问他想要什么,哥哥姐姐们不是有太傅教授四书五经就是有御前统领教授骑射,唯有他选择了混元宫。
选择了儒释道,选择了国师大人,同时也选择了放弃皇位。
父皇对他失望至极,但是母亲对他笑了。
母亲终于对他笑了。
母亲会笑着拥着他、夸赞他:“摩柯,你终于长大了。不该我们争的不争,不该我们抢的别抢,你终于知道了。”
摩柯却再也笑不起来。
母妃从来只告诉他不该和二哥哥三姐姐争抢,却从来不告诉什么是属于他的。
--
在混元宫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好。
国师大人是个极其好相处的人,在这里摩柯过了一段相当平静的日子。在这里国师大人总会教授他道家学术,他其实心中并无波澜,但是他知道娘喜欢这个。
娘喜欢他学这个所以他用尽心力学自己并不喜欢学的东西,所幸在这方面他还颇有所得,学着学着也就慢慢喜欢上了。
在这里,时间突然变得慢了起来。
除了偶尔学着国师大人要教授他的道家学说,他跟着身边的公公学了一项新的爱好,便是栽花种草。
他喜欢看着那些嫩芽在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一天一天的成长。
他喜欢看着那些含苞待放的花朵,一点一点的土壤一点一点的盛开,因为在偌大的皇宫里,只有这些是他自己选择的,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
只有这些。
即便是他的母妃,也并不属于他。
——
母妃,最近还好吗?
母妃已经很久没有来找他了。
从一开始的三天一封信,到一周一封信,到一月一封信到现在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收到娘的信了。
娘还好吗?
她可还记得我?她若记得我,又为何不写信与我?倘若她不记得我了……
娘真的会忘了我吗?
摩柯惊奇的发现自己居然没能在第一时间否定掉这个荒唐的想法。
这个世上真的有母亲会不思念自己的孩儿吗?
小摩柯就这样日复一日的等着容妃的信,可信没等到却等到了容妃的死讯。
容妃死在了冷宫里,而他是最后一个人知道的。
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所有人都对容妃的死讳莫如深。
即便他去问父皇,问来的却是父皇的一巴掌。
而他也从最受宠的九皇子一朝变成宫里,连太监和宫女都能唾弃的小九。
直到很后来,他才知道一些零星关于容妃的事。
容妃竟敢行刺父皇。
娘竟敢行刺父皇。
他不信。
他娘连一只鸡都不敢杀又怎么敢行刺父皇?
然而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不由他不信。
他的母妃谋害他的父皇,他的母妃是全天底下最胆大的女人,而他成了全天下最为人轻视的存在。这时摩柯开始思考自己该去哪儿。
或许母妃从来是对的,皇宫从来就不属于他,那他该去哪儿呢?
他不知道。
所以他就去问国师大人,从国师大人这儿,他得知了静一大师的存在。
静一大师是国师大人口中知晓天文地理,知晓真精奥义,是世上最接近仙人的人。
他一定能为他解惑。
摩柯是这么想的,而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三公主。
三姐姐玉陶自小就身体不好,他知道二哥哥请遍了天下名医,甚至连术士也请了不知方几,然而都无济于事。
他也曾多次见到自小不知天高地厚的二姐姐躲在众人背后哭泣。
她不想像其他姐姐那般成为河神的祭品。
不知从何时起,好像自从他有记忆以来,黄河经常泛滥,据传是天神降下灾难,为了惩罚谁、惩罚什么没人知道,而姐姐就要为这种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去祭奠河神,即便不是三姐姐,也会是其他的姐姐。
父皇是万民的君王,但如果父皇救不了万民于水火之中,那么身为父皇的子女该也应该担起责任。
天降灾祸,总要有人平怒,而这正是身为王女公主的责任。
而这样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姐姐身上,很快就会落在三姐姐身上。
即便不是今天,也会是明天,不是这次也会是下次。
只要黄河一日未曾平静,那么总有一天会轮到三姐姐。这样的话,时常出现在他母妃的嘴里,无非总是关心二哥哥,二姐姐多于他,她关心二哥哥不得父皇宠爱、关心三姐姐会沦为河神的祭品,却从不关心他吃饱了没,穿暖了没,甚至最后作出刺杀父皇的决定也从未为他考虑过。
甚至母妃连死后也从未入过他的梦里。
他身边的老奴说起这个总是长吁短叹,而他从最开始的闷闷不乐到现在也逐渐能接受了。
他想他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他找到了连国师也不能回答的、关于他自己的或许无人在意,只与他有关的答案。
既然皇宫不是我的归属,那么他就要去自己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
三姐姐总是藏在人群背后哭,即便她不哭也有皇后娘娘替她哭,也有二哥哥替她担心,甚至他母妃也会为她哭,只因她是公主。是公主,便要接受这般的命运。
母妃总是待二哥哥和三姐姐比对我好,所以母妃总是替三姐姐抱怨不公。
小摩柯自小就乖巧的令人心疼,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他母妃不知道。而这般乖巧的他,也令母妃生过两次怒。一次便是他在父皇面前对对子赢过了二哥哥,另一次便是因为三姐姐。母妃说上苍不公,为何要如此苛待三姐,他却觉得三姐祭奠河神是应该的,为黎明降下福祉也是应该的,因为她是公主。
而因为这样一句话,他被母亲罚跪在初秋冰冷的地跪了整整三个时辰,三个时辰后他倒了下来,三天后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公公。
他问公公母亲来看他了吗?公公说来了,只是又走了,不巧总是没让他撞见,所以他想下一次一定要见到母亲,所以还总是生病总是不见好,然而他总是遇不见母亲,后来他也就放弃了。
他放弃了母亲,因为母亲选择了二哥哥和三姐姐。
他羡慕三姐姐,因为三姐姐有他身为公主的责任和缘由,而他没有。他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九皇子,他是九皇子吗?甚至连他母亲都不承认,那他还算是皇子吗?他不是,他是个连小太监小宫女、任何一个人都能唾弃他一口的小九,他从来不是什么九皇子。
他想好了,他要出宫,他要找静一大师,他要拜他为师,他要成为人人敬仰的和尚。虽然他不能像三姐那样祭奠河神,但是他也要成为能为黎明百姓祈福的和尚。
他是这么想的,后来也这么做了。
当他说出他想出宫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包括国师大人。
后来他做到了,异常的顺利。当时他不知,后来才知应该是有了二哥哥和三姐姐的相助,若不是他们,凭他一人怎么能逃离囚笼般的深宫呢?
不过他不在意了,他想若母妃泉下有知,得知他去做了和尚也会高兴吧,因为他再也不会跟二哥哥争了,也不会跟三姐姐抢了,他要去寻找他自己的路,他要去寻找他自己的去处,所以他出宫了,然后他遇到了一个女孩儿。
那个女孩儿救下了泥泞中的他,也是那个女孩儿陪他去寻找静一大师,那个女孩儿叫“阿沅”。
他们度过了很多很多美好的日夜,她也教会他何为陪伴。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因为这个女孩,他不想当和尚了。他想和这个女孩待在一起,去看看山、看看水,看看这个大千世界,可是这一切都在见到静一大师之后变了。
他如愿见到了静一大师,却也被黑蛇咬了,成为静一大师之后,又一个被冥蛇寄生的可怜人,成了这副模样。
他以为他可以保护女孩,但是他不能。他变成了怪物。
在女孩深陷那个暗无天日的皇宫里,那些个日日夜夜,他不仅没有陪伴她,反而最后成为杀害她的凶手。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他不想的,他不想这么做,但这些都发生了。
而他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但是这一切女孩都没有怪他,即便现在掳走她的是他,做了那么多轻薄于她的事的依然是他。即便…………
即便…………
深潭的水在沸腾。
深潭之中摩柯又感觉到熟悉的窒息感。可惜他死不成。
他试过了,他试过无数种死法都死不成,他本想成为解救黎明、为万民谋福祉的和尚,却终究成为谋害人的凶手,成为大怪物,他明明……他明明…………
他不想这样的。
可是上苍为何待他如此这般?
他明明想护佑黎民,可是他连一只松鼠都救不了。他明明想要保护女孩却反倒是造成女孩死亡的凶手。
为什么上苍如此待他?
他做错了什么??
自小到大,他满足了所有人的期望。容妃叫他不要与二哥哥争、与三姐姐抢,他做到了。父皇希望他精于学习,他也做到了。国师大人希望他通于道法,他也做到了。他满足了所有人的期望,甚至是二哥哥和三姐姐,他们希望他离的远远的,所以他就离的远远的,他们希望再也见不到他,所以他去了宫外,他去做所有人不能理解的那个决定,他去剃度做和尚,他满足了所有人的希望,他自问没有做错任何事,为何偏偏找上了他?
为何是他被冥蛇寄生了,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
深夜下,死寂的深潭无风起波澜,撕裂一池死水,显出深潭下的暗流激湍。
如果不是他,如果是任何一个人,母妃会不会活得更开心?如果没有他,母妃会不会对皇后娘娘没有那么多的愧疚?如果没有他,没有那次醉酒的意外,会不会母妃还快乐地生活在皇后娘娘身边?
是不是他不存在,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了?他不会被黑蛇咬,那么他也不会伤害阿沅,那么他也不会造成那么那么多的失望,他明明是要救人的,为什么变成了害人的怪物?谁能告诉他为什么?为什么?
他该死啊,像他这样该死的人却死不了,他应该死去的,他应该………………
【不准放手,放手就没有希望了听到没有!】
是谁在喊他?
【听到没有?不准放手摩柯!我不允许你放手!】
【为什么是你啊?为什么偏偏是你?为什么?】
又是谁在哭泣?
是……你吗?
是那个女孩。
阿沅。
她为什么哭了呢?
又是我惹她哭了吗?
她是……为了我而哭的么?
倏然之间又回到了那一天,他的走马灯又回到了那一天。
是女孩儿将他从泥泞里拉上来的那一天。是女孩对他说不准放手,就在他以为全世界都抛弃他的那一天,女孩拽住了他。
是女孩告诉他,一定要活下来,活着就有希望。他不该死了,他应该……他应该活下去。
他主动去找静一大师,难道是为了去死吗?不也是为了谋福祉,可是他现在做什么?
如果女孩知道他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寻死,那女孩一定不会再理他的。
一定不会的。她是那么坚韧的人,她不需要这么懦弱的朋友,而他在做什么?他应该在她身边去陪她去保护她,去弥补,去做他应该完成的事情。
这是他的身体,任何人都不能掌控,只有他自己可以。
因为这个女孩他又回到了宫里,但他不后悔。因为他交到了世上唯一的朋友。
是的,她是他唯一的朋友,他要保护她。
他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即便是他自己。
波澜起伏的深潭终于恢复平静。
潭底,摩柯睁开了眼。
仍是一双竖瞳,但眸光坚定了许多。
“听到了吗?我不会让你再伤害她了。”
“你能控制得了我吗?”
“不信你试试。是你控制得了我还是我能控制得了你。”
“好啊,让我看看吧,就凭你?”
“总有一天我会将你从我的身体里剥离开,总有一天。”
“好啊,我等着那天。小鬼,知不知道本座活了几百年?知不知道本座换了几千几万个躯体?肉身一旦被寄生便没有回头路,而你是绝佳的、最与本座契合的躯体,你迟早会知道的。本座等着那一天,等着你将我剥离开的那一天,我等着你,小摩柯。”
波澜翻滚的黑潭终于沉静了下来,潭底一双紧闭的双眸突然睁开眼,露出一双幽紫色的竖瞳,摩柯从潭底爬了起来。
他要走了。
上次是为了寻他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寻静一大师,这次他要去寻找他的朋友,他要去保护她,他要去做他没有做完的事情,他要去做真正的自己,不被任何人掌控的他自己、做真正的摩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