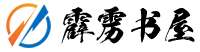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孤还有两个时辰◎
“宗行雍在关外二十七城占据压倒性优势, 比起通过联姻方式维持和平,打到西凉人心生畏惧更容易。”
白水顿住。
——他和白水印象中的储君不同,也和外表呈现出的柔和不一致。
殷臻平静道:“孤告诉过宗行雍, 孤不会选妃。”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再探究没有意义,战争号角声响彻四面八方。再解释无意, 殷臻问:“他人在哪儿?”
白水:“点将台。”
使者扣下后举兵必须快狠准, 不能给对方一丝一毫反应机会。殷臻狠狠闭了闭眼,话中森寒:“从均!”
“把阙水带上, 跟孤进肃州城。”
他要确保江清惕没有投诚西凉的念头,即使有, 也必须扼杀。
“殿下要带我进城?”阙水粗布麻衣立在夜色中, 轻轻笑了,“不怕我死在城内?”
“必要时孤会杀了江清惕, 最后一面……”殷臻对他道, “你确定不跟孤一起去见他?”
阙水叹了口气:“殿下果真铁石心肠。”
宗行雍打赢第一场仗时殷臻混进肃州城, 时间正是江清惕大婚当日。殷臻一柄长剑挑开新娘盖头, 他身后立着阙水。
满堂宾客皆惊, 假新娘尖叫逃跑。殷臻信手杀了三个混迹其中的西凉人, 鲜血流淌过脚底。
“孤知道你要什么人,送来给你, 只有一个要求, 战争结束前你不得和西凉人有任何交涉。”
江清惕直勾勾看向他身后:“殿下何意?让我眼睁睁看着肃州……”
三把长剑架在他脖颈, 殷臻耐心告罄,道:“要么应, 要么死。”
“好一个先礼后兵。”江清惕抚掌大笑, “凭什么?”
殷臻:“你只有一个选择, 将肃州奉上。不过是奉给谁, 以什么方式奉。”
江清惕不发一言。
阙水倒是苦笑:“我就这么被殿下卖了?”
殷臻没功夫在这儿掺和别人爱恨情仇,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头也不回:“江清惕跟孤说他爱慕你多年不得,贴通缉告示是为了找你,他早知道一双眼睛是你一年后折返治好,黄道吉日,孤看你们最好今日成亲。”
“对了,江城主当年没死全靠庸医心软,他接下的任务是杀人,后来不仅杀了同伴,还断了一条腿,就为了保你一条命。”
什么都没说、完全不知道的江城主:“……”
三两句大庭广众之下被揭露秘密的阙水:“……”
宗行雍第二场仗开始时殷臻控制整个肃州城,他压下暗中来访的西凉奸细共十三人,斩首示众,头颅悬挂城墙之上,以儆效尤。
所有异族面孔全部暂时收押。
他站在城墙上,看向烽烟黑沉的天际。
阙水:“殿下不必担心,少主所向披靡,从无败绩。”
“孤有不好的预感。”殷臻压着跳动眼皮,“很不好的预感。”
第二场,宗行雍依然胜了。
势如破竹,连取三员猛将首级。
事情断裂在第三仗后,关外第一场暴雪,群山绵延处,巨响至。
曙色熹微,蚩蛇深夜策马疾驰至肃州城池。他浑身浴血,在殷臻身前深深叩首:“殿下,少主失踪。”
“雪崩。”殷臻沉默后道,“西凉人在等这场暴雪。”
蚩蛇双膝跪地,他手上沾血,极艰难地开口:“虎符,请太子坐镇三军。”
宗行雍本有脱身的机会,他一旦后退,背后上千士兵将埋没在雪崩之下,和当年滂水之战将他送出沼泽的所有将领一样。
殷臻立在茫茫雪山前,身后是七百死侍,黑衣如鬼魅站立。深冬风如狼嚎鬼哭,从山谷中灌出的寒意蔓延四肢百骸,他下半身失去知觉,锦靴因灌满雪水变得沉重。
太子深深弯腰,胸口抽痛。
他知道此时应该往回走,知道一旦大肆派人寻找,主帅失踪之事随时可能暴露。宗行雍在军中地位如同定海神针,一旦消息传出去军心不稳,敌军得势,局面将糟糕到无法挽回的程度。
理智告诉他应该回去,情感上他却无法迈出一步。
他知道雪崩后十二个时辰是救人的最佳时间,他站在此地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活活消耗对方的生命。
殷臻想,他必须马上做决定。
他浑身血液一寸寸冻僵,握住虎符的手失去知觉,神经末梢颤栗起来。
直到有什么温热的液体顺着指缝往下流。
“殿下!”从均立刻上前,掰开他的手,虎符一角将他掌心扎破,刺目鲜红血液一滴滴往下流。
滴落在雪层上,盛开一朵朵鲜红小梅花。
“篱虫。”殷臻声音沙哑得像是鼓风箱抽动,他伸手拦开从均,每一个字都相当艰难,“孤一炷香内让你变成宗行雍的模样,虎符孤交给你和蚩蛇。你回到营地,立刻坐镇三军,和西凉打第三仗。”
篱虫猛然抬头。
“属下领命。”
殷臻衣袍猎猎,生生咽下口中鲜血:“胜负孤不在意,孤要你——”
他一字一句:“生擒敌将,取项上人头,以泄心头之恨。”
“蚩蛇。”殷臻极其清楚,“西凉粮仓至少有三处,在摄政王桌案上以朱砂标注,你带兵,放火烧,抢,炸药,孤要动静,越大越好。”
蚩蛇:“属下领命。”
七百死侍立在这场巨大风雪中,静默如死者。
一旦宗行雍身陨,他们将为汝南宗氏独子殉葬。既定命运如巨大阴霾,笼罩每一人心头。
“从均。”殷臻没有停顿,眼神始终看向层层压盖的雪岭,他心中穿了一个巨大的洞,不管什么都从里面穿过去,五感变得麻木,站在这里像做梦。
殷臻冷静得绝情:“孤要你以太子之令从曲水调兵,一日时间,违令者就地格杀,孤许你先斩后奏。”
曲水是离中州最近的驻兵城,有精兵骑兵三千,一旦肃州军饷至,西凉军队若不能在短时间内攻打营地,战场上将冻死成千上万的士兵。
从均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属下遵命。”
从均:“殿下,您……”
“孤有件事没做完。”
殷臻一步一步朝风雪中走,轻得几乎呢喃:“孤去找。”
“殿下!”从均立刻跪在他身前,焦虑,“不可!”
他话音刚落脖子上架了一把长剑,剑气刺破皮肤。殷臻声音细听在发抖,袖中握剑的手也在抖,长剑偏移,他眼尾一片深重红色,哑声:“滚。”
从均紧咬牙:“殿下不知摄政王方位,此番前去如大海捞针,何况此地随时有二次崩塌可能,殿下若执意如此,属下——”
“嘭!”殷臻手起刀落敲晕他,“把人带走。”
他用了不到一炷香时间将篱虫潦草易容,篱虫转身,身后七百死侍悉数后撤。
走出几十米,篱虫脚步骤然停住,忍不住回头,空旷荒芜雪山间一片白色,殷臻身影消失在天地一色中。
很快,大雪覆盖住他前行的脚印,一切痕迹都消失。
“首领。”篱虫身后人道,“我们……”
篱虫:“少主有令,一切听从太子命令。”他长刀锃亮,映出一张面无表情的脸,“有人想回去,我绝不手下留情。”
……
殷臻迎着风雪往前,大脑因寒冷而格外清醒——从篱虫口中转述的地形位置中他迅速在脑中构筑立体图,推测雪崩可能造成的两种情况,分别指向左右两种不同的路径。他只能赌一把,赌接下来走的那条路能将他带到宗行雍身边。
他在抉择地长久停留,迟迟无法走出那一步。
宗行雍。
殷臻在心中缓慢地想,告诉孤,往什么地方走。
孤不知道。
绝望压得殷臻生理性作呕,他精神濒临崩溃,想吐。
而他必须要走。
他选了左边。
越往前走殷臻心越沉,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捏紧。
无法判断时间和方向,只能漫无目的往下走。他可能走对了,也可能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为了找到人之后在最短时间内折返,他必须保持绝对的清醒和对东南西北的高度敏锐度,这对他来说不难,怕得是从一开始他就选错了方向。
殷臻浑身开始僵硬。
他走得很慢,也很困难。江州潮湿之地治水令他双腿无法忍耐一丝一毫寒意,密密麻麻痛感穿刺每一寸皮肤。
人在恐惧的时候,身体上的痛微不足道。
眼前大片白色。
殷臻闭眼,再睁开。
依然是找不到方向的白。
过去了很久,又像是睁眼闭眼一瞬间。
殷臻停下来。
他吃力地喘气,双手撑住膝盖。
——孤可能走错了。
他茫然地想,孤运气其实很不好。
孤出身不好,脾气不好,运气也很不好。有两个宫妃养孤,都倒霉失宠了。孤一点不讨人喜欢,孤嘴笨,说出来的话难听。孤对宗行雍也不好,孤利用他,伤他心。
不知道宗行雍喜欢孤什么。
孤好累,走不动。
孤好没用。
殷臻全靠微薄的意志力支撑,他双腿如灌铅——没关系,孤再往前走一点点,走一点点。只要到前面那个小山包,没事,再往前,过了那个小山包会更近。
越往前走殷臻越绝望。
四周没有人声,风声也在某一刻停止。脚下踩到大雪下枯枝,“咔擦”每一声都让他产生错觉是有人回应。他开口喊了宗行雍名字,但自己都无法感受到喊出口,或者没有——孤到底喊了没有,他喉咙剧痛,吞咽如咽刀片。
十步之内,孤必须回头。
十步又十步,十步又十步。
十步再十步。
殷臻怔在原地。
——他看到了一缕黑烟。
从不远不近的洞穴中飘出来,是焚烧物所致。
大脑嗡鸣。
殷臻至少在原地站了十个数,来确认那不是幻觉。他胸口抽痛,太阳穴跳动,大悲大喜后强烈情绪叫嚣,冲击每一根岌岌可危的神经。
他尽力走快,每一步犹如走在刀尖上,扎得双脚鲜血淋漓。
——孤从未见过宗行雍如此狼狈的模样。
殷臻将洞外光亮遮住大半,思绪迟钝地想。
石壁边他靠着,脸色青白,脱了外衣焚烧,长腿长脚蜷缩,脸色白如金纸。
孤要做什么?
要上前去摸一摸他还有没有脉搏?
殷臻被冻僵的大脑重新运转起来。
他外衣氅袍拖曳在地面,和细小沙粒接触,发出窸窸窣窣声音。
狂风暴雪急速而至,拍打在耳边。
殷臻半跪在宗行雍面前,僵硬地抬起手,做了个试探呼吸的手势。
微弱而不明显的热度卷过指尖。
殷臻有足足半秒没有动作。
他重重咬住下唇,保持清醒。隔了很半晌,抖着手去解厚重而聊胜于无的氅衣,接着是绒衣,接着是外衣。
脱了一地。
殷臻心中升起奇怪的庆幸——还好孤听话,穿得很多。
脱完一件件往对方身上披,手指顺着几乎变成冰块的手臂朝上,打了个哆嗦。
他和宗行雍的温度实在相差太大,几乎是一从火碰到了旷野一望无际坚冰,很快火苗禁锢在冰中,无法散发一丝一毫热源。
殷臻双手拢住面前人腰,将自己紧紧缩了进去。
冷得他牙关打颤。
不太够。
好慢。
殷臻焦躁地扬起头。
里衣依然冰冷,唯一的热度来自他自己。
他几乎缠在宗行雍身上,眉眼变得决然。
伸手拢紧了垂落在地的大氅。
最后一件贴身衣物滑落。
殷臻将自己整个缩进去,意识变得模糊。
——他隐约感受到自己身上温度高得不正常,可能是在发烧,紧贴的肌肤变得不再毫无人气,耳边心脏跳动缓慢恢复正常。
好久。
孤要睡觉了。
殷臻光-裸手臂向上攀附,勾住宗行雍脖颈。
被虎符刺破的手掌依然在流血,他定定盯着伤口瞧,将手掌费力地抬起,凑到宗行雍唇边。撑起上半身,往他嘴里灌。
宗行雍本能吮-吸。
好晕。
殷臻内心挣扎地想,孤再坚持一小会儿?可是孤真的很想睡,孤找到人了睡一小会儿没事,可是他万一醒了孤没发现……
他勉力撑着精神,很没安全感地凑上去,亲亲毫无动静的宗行雍薄唇。
沾了血,口中满是铁锈味。
过了很久,很久。
宗行雍似乎是从一个噩梦中混沌地醒来。
“本王要死了。”耳畔呼吸冰冷缓慢,殷臻被抱紧,听见他低低笑,不成字句地道,“太子……不该……高兴吗?”
温度下降,他声音也降下来,像某种华丽击打乐器泠泠敲在耳鼓上,不含情绪。
摄政王以为自己将死,在做梦,用得力道生生要将他勒入骨血,同生共死。
殷臻被勒得喘不过气,想去掰开他的手,一伸手冻得他打了个寒噤。太冷了,他疑心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冷,骨头缝里泛起一阵阵恐慌。他向来不耐寒不耐热,却忽然什么都克服了。
“五年前在大金寺,换另一个人,孤会杀了他。”呼出的白气将他眼前模糊,殷臻很轻,很轻地道,“宗行雍。”
“你不一样。”
你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孤求你,别睡。”
宗行雍耳中像是塞了棉花,他头痛欲裂,模糊捕捉到一点细微的哭腔,很难过,很绝望。
——本王从未听过他求人,也从未听过他哭。
即使是在最疼痛的时候,最受不了的时候。
摄政王打起精神,手指摸了摸怀中人耳朵,热度烫得他心中惊跳——高烧,这么烧下去人有没有命还另说。
他纵使有一千个一万个想就此睡过去的念头,那一刻简直是活生生吓醒的。
三魂六魄一下回了神。
宗行雍后背惊出一身冷汗。
什么太奶奶太爷爷他亲娘全部在召唤的黄泉路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僵冷的四肢急速回温,全凭借强大的生理素质强迫自己回到现实。
——他娘的。
摄政王一低头,骂了一句。
他看着烧得昏沉却不肯闭眼的殷臻头重脚轻,差点失手把人摔下去。怀中人像拼命燃烧的火炉,烫得他胸膛后背冰火两重天。
殷臻放下心,抓住他一截衣角,小小声:“孤要睡觉了。”
掌心蜿蜒血迹激得宗行雍太阳穴凸凸跳动,要说他刚刚还有三分睡意,现在就是魂飞魄散。
宗行雍厉声:“别睡!”
殷臻呆呆愣愣睁眼:“为什么?”
“你为什么凶孤?”他抓住宗行雍衣角,不依不饶地问。
纵使此刻宗行雍嗓子在冒烟,他依然努力道:“本王错了。”
殷臻笑了一下,大度:“孤原谅你。”
手指发僵。
宗行雍伸手又收回,血液缓慢流向心脏:“刚刚……说什么?再说,一遍?”
殷臻费力地想了一会儿,前言不搭后语:“孤放了信号弹,留了记号,从均很快会过来。”
宗行雍的角度能见到他粉白的颈,他将人抱紧,胸膛中两颗心脏贴得极近:“不是这句。”
“你不一样。”殷臻看着他的眼睛,困倦地闭眼。他烧得睁不开眼皮,依然执着地,不留余地重复,“孤刚刚说,在大金寺那日,换一个人,孤会杀了他。”
宗行雍心中有什么膨胀起来。
他干裂的唇瓣贴上殷臻额头,很慢地说:“本王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大金寺。”长句子对他来说过于困难,他尽可能地道,“本王第一眼,见到你。”
秋日,寺中落叶金黄,铺满一地。
他被虞氏女缠得不胜其扰,借口约了人跟着小沙弥离开。路过偏殿时顿住。
寺庙中有好几只皮毛顺滑的猫,被大慈大悲的和尚养得油光水亮,全部趴在草上四脚朝天地打滚,五六双猫眼儿眼巴巴地瞧。
摄政王一时生了兴趣,驻足。
身形清瘦的青年被围在中央,手中只拿了一块鱼干。他显然对这种状况束手无策,不知道到底该喂给哪一只,苦恼地犹豫半天,蹲下来,给每一只咬一口。
到嘴的食物岂有被夺走的道理,每一只猫主子咬住了就不肯松口。偏他一个人非常公平,铁面无私,从每一只猫口生生夺回来半截鱼干,在每一只猫懵逼的眼神中一路猫口拔食,坚守原则喂到最后一只。
摄政王那时候就想,这人有点意思。
宗行雍本想跨过佛门净地,问他是哪家的公子。那念头只在心中晃过一瞬,他觉得好笑,脚步一转,走了去往虞氏女屋子的路。
人的预感很奇怪。
中计时摄政王模模糊糊地想。
如果必须让本王选一个,本王希望是他。
“睡一觉。”宗行雍伸手,盖住他滚烫眼皮。向他保证,“睁眼时本王在。”
殷臻能挺清楚他说的每一个字,但无法理解句子的确切意思。
他实在太累,闭眼晕了过去。
做了梦。
梦到在大金寺见到宗行雍前的事。
美色确实有强大无比的助力,但当他并不具有保护自己的权势时,那会成为负担和累赘。
薛照离那张脸,足以引起达官贵人兴致。
他先遇到了一个很恶心的人。
能让太子用“恶心”来形容的,其实程度不止。
宫中野猫众多,都不亲人,见到人就会挠一爪子。大金寺的猫不同,他去后厨要了一只小鱼干,想等摄政王和虞氏女谈完,再找他。
不巧,遇见了当时的大理寺官员,虞氏的大公子。
此人好男色,府中多脔-禁,有施虐癖好。他当时并不知道,听得陪同对方的人低头哈腰称呼一句“虞大人”,也跟着叫了一声。
吸引对方注意的,是声音。
那人打量他的视线很奇怪,狎昵而饱含淫-欲。开口问他要不要跟他,以后金银珠宝供着,一生不愁吃穿。
殷臻记得自己客气拒绝了。
他被捏住了下巴,对方淫邪目光扫过他的脸:“你这样的……没个靠山,只有被玩死的命。”
后来他死了,死于车裂,殷臻亲自下的旨。
……
殷臻梦到很多事。
他梦到讨来的纸笔,梦到忍饥挨饿换来的书卷,梦到明亮的学堂,梦到学堂中一双碧绿深瞳的氏族公子,闲来无事脚边放了只叫声嘹亮的蛐蛐。
梦到在摄政王府那一年,梦到王府中那棵柿子树,结出硕大的果,沉沉坠在枝头;梦到呱呱落地的绿眼睛,梦到他甜软的包子脸,梦到他偷偷摸摸爬上榻打滚被抓包后狡黠神情。
梦到大红灼灼婚服。
大梦十年。
殷臻断断续续睡,断断续续醒,他喝了水,吃了粥和汤,吞下不那么苦的药。又陷入另一场光怪陆离的梦。
大片光亮照射在眼皮上。
殷臻睁开眼,骤然有不知身处何地的茫然。
他缓缓坐起来,环顾一周,瞧见熟悉的摆设定下心,这才揉着额角沙哑:“孤睡了多久?”
从均红着眼:“三天三夜。”
“孤好多了。”殷臻一顿,安慰道。
他眼前一阵阵发黑。要问什么,又想起一旦宗行雍回来,击败西凉只是时间问题——摄政王的身体素质堪称恐怖,掉到只剩一滴血都能在一觉之后恢复清醒。
从均知道他要问什么:“胜仗。”
殷臻精神很好:“你有何事要跟孤说。”
从均一咬牙,道:“殿下,京中来人求见,今日午时至。摄政王有令任何人不得打扰,属下看他神情焦急,应是大事。”
“京中?”殷臻皱起眉。
帐外平和,蚩蛇抱刀冷冷盯着在原地打转的人,见殷臻出来显然一僵。
大雪,雪如鹅毛。
殷臻抬起袖,遮住眼睛,慢吞吞望向那个衣衫褴褛的传信人:“孤是太子,你要跟孤说什么?”
“圣上病重。”来人跪地,急促,“宫中消息封锁,秦大人请殿下速速归京!”
殷臻梭然看他。
以传信速度看,晋帝病危之事至少发生在十日前。
“备马。”他当机立断对从均道,“孤立刻回京。”
从均迅速:“属下去探路。”
四周静得落针可闻。
殷臻缓缓回头,冰凉的唇紧抿:“孤要走。”
宗行雍深深地看向他,半晌,勾唇笑了:“本王没说不让你走。”
——自醒来后,他们只说了两句话。
殷臻不再看他,大步朝前。
他翻身上马,身后跟了三百死侍和七百精兵,皆出自摄政王麾下。
风雪未止。
殷臻紧握缰绳。
“吁——”
从均勒马拦在军队前,坐下良驹马蹄在原地焦躁打转:“殿下,雪太大了,此时离开太危险,需要清路。”
墨发被吹得漫天飞舞,殷臻自马背俯身,一字一句问:“要多久?”
“至少两个时辰。”
大雪白茫茫一片,落地如席。
两个时辰。
殷臻骤然翻身下马。
“两个时辰后出发。”他扔下一句话,接着转身往后。
从均见他奔跑起来,怔在马背上。
——自五年前太子居东宫,行走坐卧便自觉有储君仪态,喜形不露于色。而此刻,他在皑皑白雪中奔跑,氅衣旋开,像一只鸟,狠狠撞入了宗行雍怀中。
“孤还有两个时辰。”
宗行雍仿佛早有预料,张开臂膀一把将人接住。滚烫温度自手心传来,摄政王难得怔忪,听见殷臻在他耳边喘息,呼吸急促:
“你想不想确认,两年前重伤后那一夜,是梦还是……”
殷臻扬起头,眉心痣艳丽。
“真实发生过。”
宗行雍呼吸一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