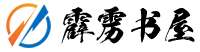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素溪是教了他很多奇怪的东西。
殷臻冷冷:“孤忘了。”
“忘了?”宗行雍低笑道, “本王帮太子想起来?”
“……”
从某种程度上说,宗行雍真是捏准了殷臻。
他思考问题从来只有解决和不解决两个选项,除非山穷水尽绝不考虑放弃。他要拿到军籍, 势必要通过宗行雍,摄政王说一不二, 除非他服软。
服软和想办法, 指向同一条路。
殷臻手指轻搭在桌面,下意识地敲。
宗行雍放轻声音, 光线幽暗的帐中无端透出缠绵诱哄意味:“做一做,做了前尘旧事一笔勾销, 太子从前骗本王的, 本王都就此揭过。”
殷臻用力地抿了下唇。
漆黑瞳仁一转。
宗行雍知道他会做。
——他虽容易害羞,却有一些不知世事的大胆。在床笫之事上意外单纯, 也很好骗。只要好好说话就会自己掉进圈套, 受骗多次还是忍不住相信, 像一只有戒心但不多的猫, 总摊开柔软肚腹给人摸, 摸得用力就会生气, 伸脚蹬人。
下次再不长记性地摊开,再被人翻来覆去地蹂-躏, 再重复。
宗行雍太爱这人主动。
这是他用心浇灌的花, 在爱中生长出一部分属于他的血肉, 和他紧密相连。
他至此真正从此君王不早朝,知道什么叫“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灯火幢幢, 映在营帐内壁。
殷臻含了一口水。
他真是漂亮, 三千青丝如乌墨绸缎, 肤白如象牙,黑与白形成极致反差,唇不点而红。美人痣妖而艳,偏他坐在宗行雍腿上,神色正经得像是在做什么大事。
从宗行雍的角度看他整个人从耳朵尖尖到后颈蔓开大片深红,整个人差点埋进他胸口,解他衣扣的手在微微发抖。
摄政王护住他后腰,没忍住笑了下,另一只手抚摸他后背脊梁骨,语带揶揄:“太子,你看起来像是要用毒药把本王毒死。”
这种事做过很多,但在四年前。
殷臻没觉得自己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他脸开始发烫,整个人和着火一般从头烧到脚,脚背和脚趾尖情不自禁绷直了。
他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却又形容不出来。
宗行雍每开口说一句话,一个字,他后背脊梁骨就抽出一道电流。
他忍不住想叫宗行雍别说话,但忘了口中含着水,情急之下全部往里咽。
“咳咳咳……咳咳!”
他反应很快,但水渍还是从唇边狼狈溢出。摄政王心中直想叹气,一手掌住他下颔,温柔地吻了上去。
他瞧见这人只觉得心中一片柔软泛滥,喜爱得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哪儿还顾得上生气。
殷臻简直呼吸不过来。
“换气。”宗行雍在他下巴上点了点,低低笑,“别让本王这个都教你。”
殷臻思绪陷在一片朦胧的水面,在里面沉下去,又浮起来,再沉下去。
他吞进去不少东西,很艰难地要把宗行雍推开,但能活动的空间有限,不得不攀附在对方身上。
这世间他不明白的事多了去,譬如摄政王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又譬如他屋里堂而皇之堆积的春宫图。
宗行雍五指牢牢掌控住他,令他窒息之余生出安定来。
仿佛回到此前很多个抵足而眠的日夜。
如果宗行雍不说话,事情会更好。
“啊,还有一件事。”宗行雍念念不忘道,“太子让人烧了本王的春宫图,那都是本王珍藏多年的孤品——”
殷臻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霎那:
“闭嘴!”
宗行雍这人有让所有人开不了口的本事,没有下限,只有无下限。
见真要把人惹毛宗行雍遗憾地闭嘴,表情可惜。
殷臻没想搭理他。
宗行雍“嘶”了声,呲牙咧嘴:“本王的背。”
殷臻:“……装的。”
摄政王哼哼唧唧。
殷臻冷漠:“再叫打人。”
宗行雍停了下,没两秒,真很痛楚地抽了口气。
——这回好像是真的。
殷臻占了一个角落,原本坐姿挺直,后来歪了点,又歪了点。他眉心皱成一个结,把这辈子宗行雍对他好的事都想了一遍,在心里开始比较到底补一棍子还是……
看得出来他下决心的时间很长。
殷臻踹了宗行雍一脚,干巴巴:“滚上去。”
榻上距离桌案很远,幽幽灯烛的光不足以照亮卧榻。宗行雍躺在榻上,双手枕在脑后,仰面兴味盎然地注视他。
这人从弱冠之年落在他手中,此后长达一年住在摄政王府,一切反应他都了如指掌。
摄政王去了一趟大金寺,宛如打开新世界大门,不禁唾弃自己人生前二十几年过的什么狗屁日子。在此之前他对男女之事毫无兴趣,没意思透顶,殷臻出现后他见着人就忍不住犯贱,变着花样逗人玩。
可真有意思。
他把人供在手心上养,时不时纵容人骑到自己头顶。毫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傲。
本王的王妃。
光是齿间念过这五个字,宗行雍心底就躁动起来。
殷臻吸气:“你根本不——”谁背疼还仰躺。
他话没说完宗行雍快如闪电出手,将他往榻上扯,他常年混迹军中,力气不是普通人能抗衡的。殷臻重心不稳往下摔,只来得及堪堪撑住上半身避免倒下去。
乌发如绸缎落下,将二人笼罩在私密空间中。
又上当,殷臻翻身就要往下。
“没骗你,是真疼。”
殷臻犹豫了半秒,怕压到他,迟迟没有下一步动作。
宗行雍指着胸口,故作可怜:“心疼。”
沉默震耳欲聋。
殷臻:“……”如果把他最想让宗行雍做哑巴的时刻排序,那一定是此刻。
宗行雍虚扶着他腰和腿,叹了口气:“不能认真点对本王吗?”
殷臻一顿。
宗行雍深绿近黑瞳仁中倒映出他的影子。他能从中看见自己,是一张柔软的、毫无防备的脸。
心脏在胸腔中不甘寂寞地跳动起来,“砰砰”、“砰砰”,一声比一声激烈。
——孤喜欢他。
所以不抗拒和他亲近。
连日来的种种妥协有了解释。
殷臻指尖血液都开始变凉。
他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一时间都忘了从宗行雍身上下去。那种陌生的感受游走全身,令他后背激出冷汗。
宗行雍几乎是瞬间就发现了他的异状,手顺着他后背往里,摸到汗津津的骨肉脸色一沉:“怎么回事?”
薛进掀开军帐:“今日外面有烤全羊王爷要不要一起——”戛然而止。他瞳孔地震,倒退两步,“唰”放下帐帘,脸涨红:“王爷恕罪,薛进不是有意……”
他看见太子跨坐在摄政王身上!
宗行雍脸皮厚,毫无所谓。
殷臻反应巨大地从他身上翻下来,脚落地发出“咚”一声响,差点从榻上栽下去。被一把捞住腰带回去。
宗行雍仍追问:“怎么了?”他担心殷臻有什么地方不舒服,语气不由得加重。一手牢牢掌住殷臻腰侧,控制欲和掌控欲显露无疑。
他声音和平时毫无差异,却像是无数羽毛钻进耳朵里,往更深处洒下种子,迅速生根发芽,一路痒进心里。
殷臻惊疑不定地看他,瞳仁都睁大了。
宗行雍:“你用什么表情看本王,本王是什么洪水猛兽?”
殷臻一把甩开他放在自己腰间的手:“——别碰孤!”
他对宗行雍说过那么多次这句话,只有这次非常凌厉,宗行雍眸色瞬间暗沉:“殷臻。”他一字一句。
殷臻脱离他立马接连往后退了好几步,脑中乱七八糟闪过很多念头——孤马上就要回京,一刻都待不了,马上斩断和宗行雍的一切联系,绿眼睛扔给他……
他深深吸了口气。狂跳不止的心脏令他大脑嗡鸣。宗行雍正要靠近,被一胳膊横拦住。他向下看,缓慢地眯了眯眼。
殷臻:“孤没事,”他喘了口气,“心悸而已。”
他瞬间和宗行雍拉开了距离。
宗行雍还待说话,门外薛进做了半天思想斗争,苦哈哈地再次喊:“王爷。”
殷臻袖中手攥紧了,几乎掐出一道血痕。他清楚无比地再次重复:“孤没事。”
宗行雍目光从他身上挪开:“进来!”
薛进老老实实进来,视线绝不多往殷臻身上多看一眼:“王爷,附近牧民送来的羊,今晚杀了,正在火上烤着。”
羊肉。
腥膻味。
殷臻以袖掩唇,胃里猛烈地一抽。
宗行雍:“本王知道了。”
薛进从帐内退了出去,殷臻肩上一沉,厚重大氅盖在身上。他看向宗行雍,宗行雍坐在榻边,看也没看他道:“伸手。”
“风大,别给本王着凉。”
殷臻发怔地看他。
外面狂风呼啸,北地风卷草折。
他原本不想去。
却没拒绝。
空地上边围了好几圈人,每一圈中心火堆上都架着一只被烤得滋啦作响、直冒油光的肥羊。几百双眼睛齐刷刷望过来,全是军中大老爷们,一个个热情似火。
殷臻手指尖缩进衣袖中,搜寻距离宗行雍尽可能远的地方。
宗行雍第一时间察觉到他的抗拒,他冷笑了声,阴沉沉:“太子。”
“你想本王当着这么多人面把你从那头抱到这头?”
殷臻一哽。
在场都是他不认识的人,他在冷风中吹了半刻,心知刚刚惹怒了宗行雍。
喉咙里生出无法遏制的痒意。
他心烦意乱,然而在场所有人都注意着他一举一动。他进退不得,只得跟着宗行雍入座。
殷臻神思不定。
军中酒宴不比皇宫,众人称兄道弟勾肩搭背,酒水辛辣味道穿肠过喉。他滴酒未沾,却被空气中浓郁酒香熏出醉意,头脑发热。
宗行雍就在他右手边,盘中烤羊腿香气扑鼻。摄政王拿把匕首熟练地切割,很快盘中摞起一叠叠焦黄的肉。
他甚至片成一小片一小片,每片不过毫厘厚度,以此来发泄情绪。
不需要刻意去看身边人一举一动就无限放大,殷臻对这种陌生感惶恐。由于所有人围坐一圈,他不可避免会碰到宗行雍的胳膊,每碰一下心脏就急速地尖啸,耳膜鼓噪。
一切都乱套了。
他一刻都呆不下去,忍耐到极限后立刻要起身,眼皮底下却突然多出一盘烤肉。
色泽金黄,上面洒了不知名香料。并不如想象中腥气。
殷臻眼睫狠狠往上一掀。
腹中饥饿后知后觉翻腾上来。
“吃完再走。”
“羊肉性热,温补气血。”宗行雍说了八个字。
殷臻猛然看他。
所有的恐惧突然在这八个字中潮水般退去。
他默不作声低头。
酒足饭饱,不由得生出其余心思。
军中私宴向来不拘小节,左手边腮络胡的将军喝得上了脸,打着酒嗝儿醉醺醺问:“王爷,屠洪山天今儿就替大伙问了,王爷如今还未娶亲,什么时候各位将军们能吃到汝南宗氏的喜酒……”薛进眼疾手快捂住他嘴,没防住,“——王爷今年都三十了!”
三十。
还未娶亲。
宗行雍手腕一翻羊肉翻了个面,懒洋洋:“你问太子。”
“……咳咳咳!”殷臻细嚼慢咽,羊肉还是差点卡住喉咙。他止不住地咳嗽,宗行雍长臂一展拍他后背,一点没耽误地问:“太子觉得本王是什么时候能娶妻?”
殷臻僵着脸往一边让。
这话一说大家没深想,只当宗行雍有心敷衍。单洪山一把拉下薛进的手,瞪着铜铃似的眼睛:“太子不是已大婚成家?”
殷臻和宗行雍齐齐一顿。
“殿下,这一圈坐的都是家中没个媳妇的,”有人搓了搓手,咽着唾沫问,“是啥感觉啊。”
殷臻眼神中流露出茫然。
他一时没听明白,轻“啊”了声。
“对啊,听说殿下有个深爱无比的太子妃,小皇孙都三岁了。”又有人羡慕且渴望,“太子妃长得啥样啊,好不好看?”
任何谣言经过一波一波的传都变得离谱,譬如说当朝太子至今没立太子妃,是因为在民间有个国色天香的意中人,身份低微不便带进宫;有人就说让一国太子神魂颠倒的这得是啥人,传来传去变了味,说东宫有只狐狸精。
殷臻呆滞地听一群军中将领七嘴八舌讲,这个说完那个说。他没跟上众人节奏,眼前无数张嘴开合,耳朵不知道先听哪一个人说话。
直到听见“狐狸精”三个字,终于反应慢半拍地眨了眨眼。
周边气压变低。
即使已经从别人口中知道殷臻并无太子妃,摄政王的心情依旧不见得多好。
尤其刚刚殷臻对他表露明显拒绝的情形下。
宗行雍往面前盘中羊肉上插了一刀,肉从正中央劈开。
坐他身边的薛进情不自禁抖了一下。
几十双眼睛目光炯炯,殷臻脸被冷风吹得发僵,吃了一嘴大氅的毛。他招架不住这种热情,含含混混:“好……”
他在寒风中揣稳了袖子,神差鬼使地,往宗行雍的方向瞧了一眼。
咬了咬舌尖:“不——”
殿下的太子妃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
殷臻想,似乎是好看的。
一直没说话的宗行雍凉凉:
“死了。”
死了。
死……了。
鸦雀无声。
薛进一匕首差点扎进自己胳膊,一众将士面面相觑,尴尬气氛从每一个人眼中蔓延。最后终于有人打哈哈道“这样啊”“没事”,又有人一言揭过了话题。
他们常年在军中,也没什么坏心思,自觉戳到人伤心事,望天望地再不望殷臻,装作若无其事地接着跟身边人攀谈。
月光满溢,人声嘈杂,和宫中冷清截然不同。
殷臻放在沸水中的心静了下来。
他隐约笑了下。
“王爷怎么知道孤死了太子妃。”他袖手,慢吞吞问。
宗行雍咬字:“太子。”
没关系。
殷臻冷静地想。
孤只要小心一点,不被抓住把柄。
没有什么东西是藏不住、戒不掉的。
篝火燃尽,冷烟上窜。天边圆月光晕朦胧。
裤脚被枯草上露水染湿。
坐太久,殷臻腿麻,起身时差点跌倒。他忍着酸胀去揉腿,小口抽气。
宗行雍:“又抽筋?”
殷臻低低:“嗯。”
宗行雍在他面前弯腰:“上来。”
殷臻又一愣。
“孤自己走。”他直起身。
宗行雍回头,要笑不笑:“想本王抱你?”
“……”殷臻默默攀上他后颈。
大部分人打着哈欠回了军帐,场地只剩寥寥几人。
“明日本王会传令,军中见太子如见本王。”宗行雍道,“想查什么去查,有问题来找本王。本王解决。”
嘈杂声远去,周遭静下来。殷臻趴在他背上,忽然道:“孤从来没有……过太子妃。”
声音很轻,还是飘到宗行雍耳中。
他没说“孤没有”,他说,孤从来没有过。
宗行雍脚步一停。
“告诉本王干什么?”宗行雍问。
殷臻在他后背闭上眼,不说话。
宗行雍非要追根究底问个答案:“跟本王说这件事干什么?”
殷臻被问得不耐烦:“孤今日看见了空营帐,要……”
“不行。”宗行雍拒绝得很快。
殷臻:“孤话还没说完。”
“想都别想。”
宗行雍:“本王让你出去查张卫的事就够了,你还想住出去?”
话音刚落他耳朵被拧了一下。
宗行雍:“……”
殷臻再次重申:“孤要住出去。”
“住出去住出去。”宗行雍眉心直跳,“大不了本王天天去爬床。”
等等,他眯了眯眼:“为什么要住出去?”
殷臻:“……张松有什么嗜好?”
他捏着宗行雍耳垂,犹如掌住一头野兽的命脉。
宗行雍:“赌。”
殷臻皱眉:“军营附近有赌场?”
“怎么没有?”
“军中生活乏味,睁眼不知道能不能见到第二日太阳。本王从不限制一切能发泄精力的行为。”宗行雍浑不在意,“只要不赌到本王跟前,本王一概不管。”
睁眼不知道能不能见到第二日太阳。
殷臻心里一颤。
举目望去旷野无垠,二十七城池河山尽在脚下。他伏在宗行雍背上,明明想说什么,却忍住了。
他想问你有没有后悔苦守边关四年,想问你是不是很喜欢很喜欢孤,想问能不能不造反。
最终缄默地、无声地收回了手。
孤没有立场。
殷臻想。
且宗行雍完全不在意孤的感受——真古怪,他脑子里只有“本王喜欢你,那你就是本王的人”这一连串逻辑,对方的感受如何,是不是接受,对他毫无影响。
殷臻觉得不太对劲,又具体说不上什么地方不对。他在感情上的空白更甚于宗行雍,身边又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范本。
他能知道他跟宗行雍先滚上床再认识的事不对都不错了。
宗行雍再回头人就睡着了,白天太累,手指还勾着他一截衣角,呼吸清浅,面庞沉静。
——想跟本王分床睡。
宗行雍心中斩钉截铁,不可能。
篱虫进到主将军帐中时宗行雍仍在处理军务,他身后床帐拉下,油灯被挑暗,影影绰绰露出人影轮廓。篱虫只抬头一瞬,立即低头。
“张松在军中三年除了嗜赌外并无异状。张卫死后军中发了一大笔抚恤金,全给他赌没了。赌场少东西闻息风曾来过一次,来要人。”
两年前宗行雍重伤昏迷,他抽身去找阙水,因此并不知具体情形。
“此事暂缓。”宗行雍道,“本王要你回京,确认一件事。”
篱虫作为死侍首领,唯一职责是保证宗行雍安全,他这些年只离开过两次,第一次是摄政王府那一年寸步不离跟着殷臻,这是第二次。
宗行雍:“去看看东宫小皇孙,他今年应该刚过四岁生辰。”
四岁。
篱虫猛然抬头:“此事不用告诉家主?”
宗行雍向后一靠:“本王的人,跟他有什么关系。”
“是。”
篱虫神色多有犹豫,他飞速看了一眼帐中人,道:“少主造反的事……”殷臻既然是太子,他心中疑虑宗行雍的计划还会不会正常继进行。汝南宗氏上下对宗行雍戍边四年耿耿于怀,他甚至不知道宗行雍对殷臻四年多前的重创抱何种心思。
宗行雍眼底幽暗一闪而过:“继续。”
“那少主会如何处置太子?”篱虫问。
“别用那个词。”摄政王不满地,“本王看起来像动不动处置别人的人?”尤其是殷臻。
篱虫噤声。
摄政王思索半天,又反问道:“皇帝很好做?”
这话篱虫不敢接。
“做摄政王妃不好吗?”宗行雍面露不解,“本王给他最大限度的自由,让他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就一个要求,在本王手心好好待着,别总往乱七八糟的地方跑。”
篱虫仍然不敢说话。
摄政王一旦下定主意无人能更改,他有自己一套既定的行事准则。对殷臻好是真的,喜欢这个人也是真的,想让他做笼中雀也是真的。他不在意殷臻这个人对他是什么感觉,因为最后的路殊途同归,无非是过程波折。
造反和夺人在他心中毫无冲突。
“算了,”宗行雍舔了舔犬齿,理所当然道,“本王要替他筑一座最华美的金笼。”
黑暗中,殷臻睁开了眼。
他袖中刀片极快翻转,在帐中闪过冰冷的银色。
半夜三更,宗行雍终于批完他比山更沉重的文书——他不耐烦这文绉绉屁话没有的请安折子很久了,偏偏还要忍着恶心屎里掏金,免得一不小心错过什么重要军情。
不过今晚好歹被窝不是冷的。
摄政王美滋滋摸上榻,刚脱一件外衫,心口猛然一痛。
电光石火间他迅速握住刺向胸口的刀片,手上青筋顿起。
殷臻咬着牙:“你是不是有病,老想把孤关起来。”他不能理解这件事很久了,比造反还不能理解。
整整四年这人念头毫无变化。
被戳了一刀,反正是皮肉伤。宗行雍没感觉,凑近了点捏住他下巴。殷臻吃痛,狠狠皱起眉。
“所以——”
宗行雍叹气,把他环进怀中,一寸一寸往外抽刀:“太子记住了,再往危险的地方跑,本王一定找……”
“世间能工巧匠,做最密不透风的笼。”
月光穿透床帐,流水般洒满一地,低低矮矮地越过窗。
宗行雍俊美眉眼笼罩在一层月色中,阴霾深重,明显不是开玩笑。
但殷臻在那一秒忽然明白了他生气的真正源头。
不是那一棍子。
是他在凉州城羌女手中受的伤。
他手松了力气,缓慢向下滑。
本来也没用太大力。
“行了。”宗行雍把他手中刀刃抽出,深深望向他,“现在,来谈谈太子东宫中那个……小皇孙。”
“若本王猜得没错,他有一双绿色的眼睛。”
殷臻瞳仁猛然惊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