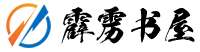嫁过去的第二个月,吴阿弟开始动手打她。
有时是饭菜不合口味,有时是打牌输了,有时是跟他讲话回话慢了,更多的时候,是他在别处受了气,无处撒邪火。
一年多了,吴细妹的肚皮一直没有动静,这也让吴阿弟一家看她更加不顺眼。
吴细妹忽然想到他第一个老婆也是没孩子的,但是这话并不敢说出口,经验告诉她,这番话只会招致更加恶毒的惩罚。
夜夜,她在床上辗转,祈祷上苍赐予她一个孩子,这样她就可以减免繁重的家务,换取九个多月不受打骂的日子。
可上苍并未理会,到十六岁的时候,她仍然没怀上孩子。
时间一长,村里的人像是也想到了什么,他们三五扎堆,鬼鬼祟祟,每当吴阿弟走过,就欠身向前嘁嘁促促地咬耳朵。
吴阿弟不是男人,这话不知是谁第一个放出来,渐渐流传开来。
“有那么些钱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绝后。”
说这话时,村里的癞子正倚着树,搓着膀子上的泥,心中一阵舒坦。
大人们嘁嘁喳喳,小孩则更加口无遮拦,一日日地耳濡目染着闲话,慢慢也学会了拿阿弟开玩笑。
每当他从村口路过,光屁股光脚的脏孩子们一哄而上围着他跑,挂着鼻涕的小嘴唠叨着,学大人的样子,问小媳妇几时大肚子。
吴阿弟心中忧闷,性情也越发暴躁乖戾。成日间脸色阴沉,喜怒无常。
有时吃着饭会猛地停住,夺过细妹手中的碗,朝地上狠命一掼。
有时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屋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
有时成宿成宿地不睡觉,手枕着胳膊别过脸去,不搭理人,问话也不答,当细妹迷糊过去时候,则飞起一脚突然将她从床上踹到地上。
还有几次在酒后红了眼,抓着菜刀贴在她脖颈上,强迫她发誓会在一个月内怀上孩子。
吴细妹以为只要不断忍耐,总有一天会过去。
然而,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只挑苦命人。
某天午后,正在田间干活的她看见吴阿弟站在田埂上,跳着脚冲她招手。细妹茫然走过去,被吴阿弟抓住手腕,急匆匆拖回了家。
刚进门就看见一个半大小子坐在竹凳上,眼瞅着地,不敢瞧她。
吴细妹认出这是阿弟大爷家的小儿子,今年刚满十八。
非年非节的突然上门干什么?
虽然心里犯嘀咕,面上却未表现出什么,洗手烧饭,她很快就张罗了一大桌子菜。
只见过几回的堂弟缩在桌角,全程只顾低着头,大口大口扒拉着饭,跟堂哥一口口地灌酒。
这是她第一次见他喝酒,还喝得这样凶。
陪着吃完了饭,闲话也说的差不多了,堂弟依然没有走的意思。
三个人就那么干坐着,谁也不看谁,任由窗棂射在地上的影子一点点倾斜。
吴细妹先沉不住气了,说得回田里干活,吴阿弟突然拦住了她,扭头给小伙子递了个眼色。
危险像是藏在花布门帘后的庞然大物,虽看不清面貌,但已将帘子顶得高高的,阵阵阴风扑面而来。
吴细妹身上汗毛倒立,转身想跑,一回头才发现吴阿弟早在她身后上了门栓。
“我得有个儿子,有个儿子。”他嘴里念叨,反剪住她的胳膊。
“哥,我不行——”
“赶紧的!”
他将她拖到地上,膝盖压住她的胳膊。
她扑腾,尖叫,脚四处乱踢,眼前一道黑影,有谁攥紧了她的腿,紧接着山就压了下来。
她放弃了挣扎,嗓子喊哑了,没有用,她知道就算喊破天去也没有用。
挨揍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来救她,她的世界没有神明,没有奇迹,没有一丁点的慈悲,只有恨和忍,她所受的所有教育只告诉她打掉牙齿和血吞。
很快结束了。
堂弟讪讪地望着她,一双手慌乱地提着裤子。
她没有言语,眼泪干在脸颊,几丝头发贴在上面,他想要帮她擦拭,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似羞似怕,站起身来跟堂哥点点头,嘴里咕哝了一声什么,逃也是的奔出门去。
吴阿弟松开她的胳膊,点了支烟。
“他下礼拜还来,你肚皮最好争气,”他弹弹烟灰,“我也不想的。”
吴细妹没有说话,缓慢地穿着衣裤。
窗外日头西斜,不知不觉间已时至傍晚。
“做饭去吧,”他把钱扔在她腿上,想了想,又多扔了五块钱,“你喜欢吃什么,自己买去,最近补好身子。”
吴细妹在杂货铺徘徊了很久,眼睛直愣愣地望着货架。最终她买了一只土鸡,剩下的钱全打了酒。
晚饭时,吴阿弟脸上看不出表情,闷着头喝酒,一杯接一杯。吴细妹在旁伺候,帮他倒酒时,吴阿弟忽然叼住手腕,抬眼端详她。
“后悔嫁给我吗?”
她一愣,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第一次知道原来女人也是有资格不满意的。
见她长时间不言语,他喃喃道:“你是个好女人,是个好女人,”打了个酒嗝,“我也不是坏人,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吧。”
又是命。
他很快醉倒,在竹榻上鼾声如雷,吴细妹在一旁安静地收拾着碗筷。
吴阿弟不知梦见了什么,在睡梦中高声咒骂起来,不停蹬腿。
细妹停下手,惊奇地望向他,像是第一次见到这人般仔细打量。
矮小黑瘦,头发并不多,细软的贴着头皮,有些皮屑。脸上已有了皱纹和晒斑,只是肤色黝黑,看得并不清楚。眼皮朝下耷拉着,酒精作用下永远红肿,像是大哭了一场。此刻的吴阿弟张大嘴巴打着鼾,不时吧唧两下嘴。
她再回来时,手里提着杀鸡的刀。
没什么两样,她告诉自己,鸡和人没什么不同。
刀扬起,落下,血溅到她脸上。没有眨眼,一下又一下,直剁到脑袋整个滚落。
原来杀鸡和杀人没什么不同,鸡是畜生,有的人也是。
她刨开卧室的泥地,挖了一个深坑。锄头挥了没两下就触到了什么,扫去浮土,看见一具烂透的尸骨,没由来的,她觉得是吴阿弟那个脸色枯黄的老婆。
吴细妹感到彻骨恶寒,接着是一阵恶心,自己竟在这枯骨之上完成了新婚。
不知听谁说的,人走时要留个全尸,残缺不全的尸骨过不了奈何桥,来生不能投胎做人。想到这里,她重又捡起刀,在吴阿弟的四肢上狠狠剁了几下,七零八碎的躯块儿,全都用鞋底踢进了坑。
“来世别再祸害别人了。”
一锨掀的土倒进去,将坑重新填平,她在上面来回踏着,一点点地踩实。末了已经看不出什么,只是泥土松软些,新土的腥气。
“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吧。”
这话说得像是冲他,又像是冲自己。
她去打水,碰上洗衣的邻居。
“细妹,这么晚还打水啊。”
“嗯。”她点头,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冷静,“天热,洗澡。”
“咿呀——”邻人忽然凑上来,揉搓她右侧脸颊,“这沾的什么啊?像是血——”
“哦,晚饭杀了鸡,不小心碰到了。”
她想,确实买了土鸡,杂货店老板为证,不怕人查。
“阿弟好福气哒,媳妇乖巧又能干,顿顿吃烧鸡。”
她笑着敷衍,提水离开,只一转身,眼里就没了笑意。
将屋子擦拭干净后,她安静地关上灯,锁上房门。
夜已极深,四下响起此起彼伏的鼾声与低语,辛苦了一天的劳作人早已陷入睡梦,不怕遇上什么人。
她提着旅行包,打着手电,深一脚浅一脚地翻过山头,将婆家的村落甩在背后。
高大的棕榈与椰林遮挡着新月,林间人迹罕至,只有她独自一人,越走越快,最终飞奔起来。
耳边响起凄厉的嚎叫,像某种绝望的动物,过了好久她才意识到,原是自己在哭。
她一路跑,一路哭,想为自己的逃亡寻一个终点。
她想到了福昌,跑回来,轻轻叩他院里的竹门。
“谁?”
陌生妇人的声音,她这才忽然想起来,早听说福昌娶了妻,去年抱上了大胖儿子。借着月光张望,果然看见一个妇人的身影,摸索着过来开门。
她在院门打开前逃跑了,实在不忍心将厄运传给别人。
吴细妹成了这个世界的孤儿,漫无目的,异乡人般游荡在自己长大的村庄。
兜兜转转,回到了从前的家。
阿婆死去后,这块地基顺理成章的归了二舅,曾经的老屋已经扒倒,新盖的草屋蛰伏在夜色之中,居高临下地蔑视着她。
这座新房,是用她的血肉砌起来的。
蓬松的茅草是她用脸上巴掌换的,刷着新漆的木门是她被撕扯掉的头发,四面新墙是踹在腰上的那一脚,她依稀记得痛得三天没法下地走路,竹梯是谩骂,院子是羞辱,新房里的一桌一椅都浸着她夜深人静时的哭泣。
羞愤烧灼着吴细妹的灵魂,她点燃火种,连同多年来的积怨一齐丢向屋顶。
缕缕白烟后火势渐渐大了起来,转瞬间洪炉燎发,火舌冲天,空气猎猎作响,烈焰映红了夜空。
她躲在暗处,看着屋里的人从睡梦中惊醒,尖叫着逃出屋来,心底无怨无恨,反倒是一片宁静。
“我只取走你们欠我的,自此两清。”
她离开村子的时候,初升红日从山间升起。
吴细妹眼中含泪,看着朝霞满天,赤红遍野,目光所及皆是红辣辣的一片,像是吴阿弟的血一路蔓延到了这里。
如果天塌下来正义才能得到实现,那就塌吧。
她昂头沐浴着血色前进,身后是燃烧的烈火,眼前是升起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