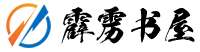一袋速冻饺子吃完, 薛队长瞄到凌大厨去洗手间, 起身就跟了过去。
凌河从洗手间出来,与薛谦一错肩的片刻须臾, 薛谦一掌伸出去按在墙边, 毫不客气地拦住去路, 对凌河勾勾手掌。
凌河心里料算薛队长就不是过来排队解手的。
薛谦找了个严总视线无法拐弯就看不见听不见的客厅角落,低声道:“凌先生, 就是找你聊聊, 关于凌煌的那件相关案子。”
凌河一听,怪不得薛谦出差特意“路过”峦城。刑警队长平时忙得日夜颠倒四脚朝天, 哪有闲工夫跑来寒暄要饭?显然, 薛谦不是来通报普通的案情, 这人也绝非“路过”。
凌河冷然道:“原来,薛队长就是来问案的。”
薛谦讲话干练利索,简明扼要,就说三件事。
“凌河, 关于凌煌那件案子, 经侦部门已经有大致眉目, 我先给你透露一二让你放心!集资诈骗和走私都有内情,省内发改委、法院和海关有几个内鬼,贪赃枉法偷梁换柱,与人合伙罗织了罪名。凌煌出问题之后,他公司的资产当时都被查封。然而,那些资产变现之后价值大约二十几亿, 在档案中七零八落下落不明,这笔资产和现款可能被人以其它方式贪掉了。专案组会继续调查,查出来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能追回的财产尽量帮你和你的家人追回来。”
“辛苦薛队了。”凌河点点头,早知道就是这样。
薛谦眼带一丝迟疑和不忍,还是讲出第二件事:“凌煌这个人,在出事入狱之前,还犯了一件小案子。但他当时贵为大老板毕竟有头有脸,有人报案指证他,被他轻而易举化解,就不了了之了。他……他被人报案参与猥亵男性未成年人,在公司和家中有针对少年的不轨行为,这件事你是否了解?
“很凑巧的,你能猜到举报他的这个人是谁吗?”
薛谦说出每一个字都盯着凌河的脸。
凌河干脆地说:“猜不到。”
薛谦没给凌河喘息的机会:“那你知道受害人是谁吗?”
凌河沉默。
薛谦眯眼描摹凌河脸上每一分每一毫的细微变化。凌河慢条斯理地用一条毛巾擦着手掌,擦手的力道几乎要将毛巾撕成粉碎,每一节指关节都攥出刺眼的白色,攥出叛逆和抗拒的情绪。
凌河也明白薛队长特意避开了严小刀,试图单独撬开他的嘴,这算是薛队长顾及他的隐私,表现出一番关怀体贴之心么?一路不依不饶穷追猛打,这番体贴不要也罢,有什么可问的?
凌河眉峰微挑,反问道:“薛队长问我?你觉着是谁啊?”
薛谦再接再厉乘胜追击,以审案的节奏加以诱导再层层推进,在凌河闪烁不定刻意回避的目光中放出第三句话:“凌河,凌煌当真是你亲生父亲吗?还是说,你亲生父亲另有其人,当年出事了?
“根据我们调查,凌煌曾经因病就医医治无效死亡的材料是造假,也没有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档案。所以,凌煌是不是根本就没死,这个人还活着?他现在在哪?……你愿意跟我们合作说出真话吗,凌河?”
“……”
“我不愿意。”凌河以四个字回敬,随手将毛巾甩回毛巾架。长条形的毛巾带着鞭子的力道,好像是用一根鞭子“啪”的甩在薛队长脸上,尽管薛队长也不该挨这一鞭。
凌河拒绝得生硬,不兜圈子不拖泥带水,根本懒得纠缠,连薛谦都没料到凌河是这么坚不合作的硬脾气。
我不愿意。
就是这样,一切都没的谈,凌河眼神一挑,就是准备送客了!
薛谦轻咳了一声:“我知道这种陈年旧事再提起来,你……”
“再提还有意思吗?当时没查,现在假仁假义地跑到我这儿嘘寒问暖再刨根问底?”凌河倏地凑近薛谦,以带着刃光的愤怒眼神逼视对方,“也太晚了吧?”
凌河眉心放射出的气焰直接逼得薛谦向后撤了两步,薛谦难得地表达了歉意:“经济案件确实是有内鬼滥用职权贪污违法,而刑事案件,如果受害人当时未成年,没有直接报案和做出详实口供的能力,我们警方也……”
“呵!”凌河不屑地喷了一声,鼻息重重喷到薛谦脸上,毫不留情地讥讽道,“如果受害人当初未成年,毫无反抗自保能力,那么他现在也该成年了,他现在有足够能力自保,也有足够的本事追讨当初被别人欠下的一桩桩债,并且连本带利地讨回来,还用得着你们出来多管闲事吗?……薛队长你多虑了,劝你还是把伸出去的手臂收一收,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吧!”
凌河发完了火,平静地又补充一句:“薛队长不用钻牛角尖,你想错了,我不是受害人,没人能害我。”
速冻饺子都不应该喂给这人。
凌河在内心默默吐槽,毫不给客人面子,满面阴郁扭头就走,将薛谦扔在洗手间门口。
薛大队长的臭硬脾气也是圈内闻名,今天假若换作面对另一个人,他早就发飙骂人了。然而薛谦这回却没有发火骂人,生生地忍了,盯着凌河倔强不肯妥协的背影,最终摇头叹了口气。
薛谦也是一切皆已了然,有了答案,此次就是专程前来旁敲侧击当事人,当面做一番求证……
严小刀从桌边站起来,因为喝了白酒,眼眶现出红润色泽,又因为手术后的脚踝尚未完全痊愈,走路时还摇摇晃晃出一身郎当劲儿。严小刀过来搂了薛队长肩膀,就像他平时搂他身边的兄弟,自带大哥气场:“走啊,继续喝。”
凌河想要赶人的话被堵回喉咙口,充满警告意味地瞪了薛谦一眼:有本事你在严小刀面前把事儿抖落出来?
薛谦也以摇晃的步态掩饰他此时头脑的清醒,对凌河横眉立目的警告视而不见,分明就是还赖着不想走,先是不请自来,然而就自请在凌宅过夜了!
凌河在厨房里,用一只砂锅给严小刀煎中药,懒得搭理楼上那两个糙人。
薛谦很不见外地进了严小刀的房间,两个大男人把酒瓶和酒盅搬到床头柜上,这就是准备喝酒夜聊。双方以前那些莫名其妙的误会,自命不凡的耍性子,现在也都自己打脸吃干抹净了。误会过后觉着还算臭味相投,都是性情中人,不妨往前再进一步,由神交变成深交,做朋友也不错。
薛谦在床上盘腿而坐,与严总再一次碰杯,推心置腹:“严总,你知道凌氏集团那个案子,我们是怎么找到的线索?”
严小刀:“怎么回事啊?”
薛谦打了个响指:“这还得有赖于陈瑾和他那个小朋友,就是他学校里那个对象,齐雁轩,你还记得吧?”
……
陈瑾一个背负着杀人犯儿子恶名的顽劣不堪的小子,本来就是硬脾气兼直肠子,没有七拐八弯那么多心眼,因此恶念来得快,解得也快。薛队长把他从少年时代阴影的泥沼里打捞上来,陈瑾就像从里到外涮肠子一般将怨气苦水都倒出来,轻松多了,好像一下子甩脱了卡在脖子上让他窒息多年的一副枷锁。
爹是爹,儿子是儿子,他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为上一辈的老人渣们背罪扛债呢?
陈瑾拉着齐雁轩,再次去了荣正街,这回是在傍晚天光尚存时,大大方方地穿街而过,没有在意周围是否有认出他的老熟人。陈瑾请齐雁轩吃了烤鱿鱼,两人各叼鱿鱼的一边,一口一口地咬,一直咬到中间,把鱿鱼吃光,让嘴唇碰上嘴唇。
两人这一晚是如鱼得水,齐雁轩这么些年也没尝过这样滋味,就没换过什么姿势,从未面对面地如此亲密,都感到有些意外。陈瑾竟然抱起他,让他骑在上面……
他们几乎把所有姿势试了一遍,顿时觉着从前那几年都白活了,折腾什么呢。
陈瑾好几次问齐雁轩:“喜欢吗?这样舒服吗?”
这还用回答?齐雁轩那一晚快活得不行,头一回尝到被宠爱的滋味……
两人估计是玩儿太累了,极度放松警惕,虽说是在齐雁轩自己的房间里,不是在齐家爸妈房里,可是不慎一觉睡到日上三竿结果被齐家老子推门而入堵在床上这种事,也是过度放纵之后意料之中迟早要发生的状况。
齐雁轩那位当官的父亲,名叫齐孝杰。
齐孝杰是白手起家的平民大学生,在官场上一丝不苟经营了大半辈子,谨慎地做人,低调精心地伺候上官,因出身不足缺乏靠山而上升空间有限,一步步向上爬也爬得不容易。这人平生以来遭遇的最大震惊和耻辱,就是看见自己亲儿子竟然被陈瑾搞在被窝里,两个孩子是那种见不得人的关系!
一顶乌云罩在齐孝杰人到中年蝇营狗苟日显疲惫的脸上,就像当场被那个死鬼陈九从坟包里爬出来,狠狠抽了他的面皮,让他蜡黄色的脸皮变成通红,额角抽出一道道血丝。一夜之间门风败坏,门下耻辱,这辈子指望能多么有出息的宝贝儿子算是被陈瑾毁了。
齐孝杰捶胸顿足怒不可遏,冲上去抽了陈瑾两个大耳光。
陈瑾硬着头皮给齐孝杰跪了,说他是真心喜欢小轩,将来想要跟小轩在一起生活。
齐孝杰吼:“不可能,你做梦,我不同意!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个杀人犯的儿子你就休想!
“忘恩负义狼心狗肺,我当初怎么会掏钱资助你上学!你这种人天生就是没良心、养不熟的贱种,就不是个东西!我掏的钱都喂了狗!!”
齐孝杰急火攻心之下把能骂的难听话都骂了,把自己儿子骂哭,把陈瑾骂得调头跑出他们家门。
这人最终颓然坐在沙发上,红着脸陷入愤怒和抽泣,上了年纪做父亲的人,最后竟然也哭了,翻来覆去地抽自己耳光:“报应,这就是我的报应……”
齐孝杰哭得很难看,随着肩膀抖动的节奏,鼻涕邋遢着流下来,这么些年饱受煎熬,亦是万般懊悔:“我是自作孽,我贪了钱,昧着良心做了坏事,这是活该啊……”
辗转反侧煎熬了三天,齐家老子一下子瘦掉十几斤,终于无法承受脆弱的心理防线在最后一根稻草面前崩塌,去警局自首了。这人交待出当年经济案件的许多线索,甚至拿出存有赃款的存折账目交给了警方。
齐孝杰在调往三江地之前,在邻省的海关做事,是海关里官职不太显眼但掌握进出贸易实权的小官。他在海关走私诈骗案中勾连协助某些人构陷了凌煌的公司,从中收了一笔大额贿赂。
齐孝杰后来参与三江民政局的所谓慈善工程,在“三市公务员帮扶失学少年赈济教育助学基金”里捐款,可不是碰巧抓阄抓到的陈瑾,他是特意选择了一对一帮扶陈家小崽子,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陈瑾是大劫案死鬼陈九的儿子,从一开始就隐约知情一部分的真相。他就是内心不安,为了积德行善,忙不迭地抛出一笔小钱,对他们家而言总之微不足道的数目,帮一帮那无家可归的倒霉孩子,赎回他原本也不值钱的良心。
没想到积德行善搞出了大麻烦,良心没赎回来,还把自家清清白白的好儿子搭进去了,果然苍天有眼,报应不爽。
……
这故事内情令人唏嘘,严小刀都替陈瑾和齐雁轩那俩孩子捏了一把担心。那两个年轻人,看起来家庭阻力不小,不知道以那二人羸弱的肩膀与涉世未深的人生经验能不能扛住这样的压力。相比起来,严小刀觉着自己和凌河面临的阻力都不算什么,他自认为骨头很硬,他扛得住。
严小刀酒喝到不多不少刚好,喉咙滋润舒服。
薛队长或许是喝高了,脑门和眼眶有大片红斑,深陷到床头柔软的靠垫里,翻看手机。好像就是无意地,薛谦呈给严小刀他随便翻到的几张手机照片。
薛谦道:“陈九的那一堆碎骨头,有一处肩膀位置被切开了,你都见过吧,咳!自作孽不可活,死得是真惨。”
严小刀只瞟了一眼,两道视线被手机屏幕上的图片吸住,呼吸停滞。
这张照片他没见过,看起来跟上回鲍局长给他看过的照片是一个套系,但确是一张堪称“漏网之鱼”的照片,清晰地显示某一根半腐烂骨骼的横截面。
薛谦:“被刀砍分尸了。”
严小刀:“对,所以骨骼断面是这样。”
薛谦:“你能看出来,这是一把什么刀砍的吗?”
严小刀:“……”
鲍局长一直想忽悠严小刀跟警局合作,判断凶手用的什么刀,而严小刀一直推脱没去,把这件事躲了,今天又被薛谦找上门来,捅开了这张照片。
严小刀面无表情,牙齿轻轻咬住嘴角,内心的波动瞬息万变。临湾港难测的风向在海面激起万丈风浪,拍击着他的心……这是什么刀?
“怎么的?”薛谦挑眉,“你还看不出来啊?”
严小刀喉结抖了一下,无奈笑道:“天底下那么多种类的刀,这怎么看?能看出什么来?”
严小刀都感觉自己笑得僵硬,面部陷入细微的痉挛,这时只寄希望薛队长是真喝高了,没看出他临时装上的矫饰的面具。
薛谦眯细了一双酒意醺然的眼,视线像刀剜着他的脸,又像是手持两把硬毛刷子,试图狠命刷掉他脸上糊的一层腻子,刷出面具下面那张柔软鲜活的面孔,刷出真相。
严小刀回避开薛队长带有审视意味的眼睛:“照片不清楚,我看不出来。”
薛谦不动声色地收回手机:“估计这是一把分量很重的钢刀!而且,挥刀人使的是左手吧?”
是,挥刀分尸人使的是左手,下刀专门选择拆骨的要害,心思缜密下手冷静。
这些线索,还是当初他自己大嘴巴似的毫无避忌地告诉给鲍局长。
严小刀有一瞬间的两眼发黑,如今回想当初,都觉得那位足智多谋的鲍青天从一开始就察觉到什么?鲍局长故意诳他帮忙看这个案子,就是试探他的反应、准备一锅端?
严小刀对薛谦饱含歉意地摇摇头:“薛队,我资质有限,真看不出来,您另请高明吧。”
薛队长也没打算纠缠强求,宽宏大量一笑置之:“是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事人估计也很纠结,悔不当初一时的冲动和恶念,不会想到有这么一天,死人的骨殖说出了真相,指认了凶手!”
薛谦不愧公门中人,是辨人审案对付各种牛鬼蛇神的老江湖了,这句话铿锵有力,头顶自带正义凛然的气场,逼得严小刀别过头去。薛谦的视线带有炙热的温度,盯得他面颊侧面滚烫……他实在无言以对。
严小刀也发觉,薛队长不是普通的出差途中“路过”,耽搁得太久了,完全不像薛谦风风火火日理万机的作风。
薛夜叉终于在凌晨时分告辞,赶大清早的航班回临湾市局了。严小刀从半靠床头的僵硬坐姿中直起腰,因为紧张而长久维持同一姿势熬了几个小时,肩膀和腰都酸了。
一线天光拨开罩在红瓦绿树上的黑色幕布,城市的美景在晨曦中露出真实的色彩。薛谦前脚刚离开这座楼,严小刀随即翻身下床,面目严峻,闪身摸进凌河睡觉的卧室。
他在鱼白天光中轻手轻脚,寻找他心存重大疑问的东西——他的刀。
他自从被凌河“捉”到这里软禁,身上有些东西被凌先生拿走了,凌河在别墅里保存着他的那把宽口钢制战刀。当然,也不算真的软禁,两人毕竟有情。
……
与此同时,薛谦在候机大厅里等候航班,掏出手机给他的上司打电话汇报工作。
“局座,按我们的原始想法,事儿都办完了!
“两个人都没有说实话,我觉得咱们的思路方向都是正确的。但是,很难说服这两个人同时愿意跟咱们合作。”
鲍正威说:“怎么,又给你脸色看啦?”
“脸色倒也没有,我吃了一肚子速冻饺子!”薛谦拍了一下大腿,“我说局座,以后这种事您别派我去,伪装低调打入内部这种事我真的不在行,我憋得也很难受,我还是擅长坐在审讯室里直接提审嫌疑人!”
薛谦酒量相当不错,不比严小刀酒量差,所以他敢找严总喝酒,酒酣耳热之际试图套出真话。薛谦道:“我觉得严总对刀痕有想法,但他目前守口如瓶不跟我们透露真相。他只要说一句,咱们能少走一大圈弯路!比如,凶器在哪?”
鲍正威在电话另一边点头:“对,我们现在有怀疑对象,但就是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而严逍是咱们撬开突破口最容易的角度,他毕竟是那位的干儿子。”
光凭直觉怀疑不成,现在办案已经不是二十年前那一套,现在讲究以证据链服人,没有硬性证据法院什么都判不了,一筹莫展。年代久远,摄像头和视频影像没有,血迹和DNA也没有,一场意在毁尸灭迹的大火还遇上当年派出所里一群不负责任的酒囊饭袋,全部痕迹都淹没在灰尘废墟中了,如今就剩下个精神不太正常的证人王崇亮。已经习惯利用DNA和摄像头等等高科技手段的新时代刑警们,感到这事着实棘手。
但是谁又能想到,公安局门口还保留了十几年前模糊的录像,让他们偶然发现,指证凌煌手脚不干净的化名报案人,竟然是戚宝山。
就是这么一条迂回的线索,就是这样冲动之下的一招不慎,让某个人露了相,让某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沿着必然的痕迹被连缀起来。
薛谦说:“局座,您这招敲山震虎,只怕会打草惊蛇啊?就看下一步严逍打算怎么办。”
鲍局长深沉地说:“我希望我没有看错严逍这个人,他别让我失望。”
薛谦又说:“还有那位凌先生,坚决不肯合作,但我认为我们的猜测很靠谱。第一,有人李代桃僵,让凌煌混出了监狱,凌煌就没有死。第二,凌河可能是猥亵案的受害人,但我们见过很多这类案件的受害人,成年之后都不愿让丑恶的事情曝光,宁愿隐瞒事实保存名誉而不愿与警方合作。凌煌一定有问题,很可能还有其他很多受害者,这是一个案中案!您信不信,这里面牵起藏污纳垢的一角,就能掀开狼狈为奸的一串人物。”
鲍正威冷静含蓄道:“嗯……有可能,会是非常棘手的大案,不能掉以轻心啊。”
薛谦直视窗外,视野开阔的停机坪上伸展开一副巨大的机翼。他的目光坚定不移:“经济案件不归我管,我也不感兴趣,但是,这个案中案涉及到刑事责任,不管当年受害人是否愿意指证,我不会放弃追查这个案子,一定让真相水落石出。”
薛队长对某些事神经敏感,并且经验丰富。他查到涉及凌氏的经济案件,拿起凌煌其人的档案照片,只看了一眼:“这个人是凌河的父亲?这两个人不是亲生父子,不用验DNA我都能确定这是隔壁老王的种,或者当初就是养子。”
鲍局长说,你这么肯定?DNA都不用验了?
薛谦笑出一脸玩世不恭:“局座,您离开一线有点久了,您整天开总结会表彰会开多了吧!我见的案例多了,从咱们刑侦画像学的角度,但凡血缘亲生,父子之间面部五官一定能找到相似之处。假若这两人就没有一丝一毫相像之处,您自己看这两张照片,相貌平凡的凌煌能生出凌河这样相貌的儿子?他有混血吗?他就生不出来。
“凌河会仅只满足于给凌煌的冤狱平凡?他到底想干什么?他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