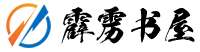笼罩在伏天热浪里的三江地, 这样的热度既能大炼钢铁, 也能烤焦那些暗怀叵测躁郁难耐的人心。荣正街各条低矮的巷子里,蝉鸣声震耳欲聋。吃苦耐劳的扁担掮客们在街巷间往来穿梭, 任由赤膊的肩膀与黑裤下裸露的小腿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互相碰撞。
陈瑾那时还叫陈芃, 是他刚出生不久, 他亲爹难得心情不错时,问对街一位有文化的老会计翻字典起的名字。草命之下的一个凡夫俗子, 陈九认为这名字很适合自家的种, 字体也挺好看。
陈瑾骨相硬朗但略微单薄,身子一路贴着墙根溜回家里, 回避着街坊邻里冷漠鄙夷的目光与喋喋不休的闲言碎语。对街一个大婶出来吼他一句, “你爹前几天从俺家抢走一辆板车, 回去问问那个无赖死鬼啥时候还给俺们?!”
在外面鬼混足足两个月都没回家的陈九,那天傍晚破天荒的回家露面了。
这人出现时穿着一件当时时髦款式的外贸T恤,晃着健硕身躯跨进家门,咧开的嘴角叼着一根万宝路烟。门边叮叮咣咣的桌凳翻倒声让陈瑾瑟缩着溜至墙角, 对他这个爹是一贯冷漠畏惧。陈九一掌削到他下巴:“忒么给老子喜兴点, 臭小子……”
陈九这十里八街出了名的人渣, 但凡在荣正街一露面,苦主债主们纷纷不约而至。
陈九那糙戾的嗓门一晚上就嗡嗡个不停,还带着一股邪性的笑:“甭来找我,老子不干了!从此以后老子都不用再挑这副破扁担了哈哈哈哈!”
陈瑾从破木头板子后面露出半张脸偷窥,前来向他爹讨债的人络绎不绝,打打嚷嚷, 其中还有一位最近时常雇佣陈九运货送货的主顾。那人是白净的脸,单薄匀长的身材,慢条斯理地讲道理:“陈九,给你活儿做你还不做?做人手脚勤快才能养家糊口,你这样人不挑扁担你难道去教书?”
陈九抄起门边那杆子扁担,横在自己大腿上,狠狠一下直接磕折,撅断了!
陈九那晚原本应该悄没生息地跑路,尽快远走高飞,就不该回自己家门口露脸嘚瑟,但他没文化他憋不住。
伪劣的人性就是这样,受人白眼鄙视、压抑憋屈了这么多年,可算是一朝鸡犬得道快要升天了,谁都摁不住内心膨胀的欲念和野心。在陈九那足够凶狠却并无多少城府与智慧的心思里,发了邪运外财一定得让家乡父老目睹他的富贵骄矜、艳羡个眼馋肚歪,不然这份大富大贵就来得不够痛快淋漓啊。
白净脸的主顾还想要说什么:“陈九,这份明早去螺江的运货单……”
陈九嚣张地挥开手,让那薄薄一张货单打着旋子飘到遍布灰尘蛛网的屋角:“算了吧你,甭跟老子脸前唧唧歪歪地废话!”
白净脸不满地低声道:“你以后不做也就不做,前两趟欠下的货单条目呢?我的货呢?你总要把事给我办完了。”
陈九冷笑:“对对~~~老子啥时候还欠你的货单?找别人去,滚蛋!”
白净脸眼底蓦地露出不善,眯细了双目:“陈九你个老小子,我也是做小本生意在三江地混得不容易,你不守生意规矩坑我的货你耍我玩吗?!”
陈九抖着嗓子:“操,你个不识相的对对,老子还怕你个外来的穷酸破落户?卖几双破鞋妈的以为自己能卖成大老板了!老子哪天碾死你个对对,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明、白、吗?”
威胁的话语祸从口出,甚至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面目张狂的人,未必真能做到心狠手辣不眨眼睛,而外表文弱无害的人物,也未必就做不出杀伐决断的凶残事。
陈九猖狂地动了手,撅成两半的扁担条打在那人后背上,将人赶走。
那位主顾临走时面色阴沉,淡淡地回敬了一句:“陈九,做人留点余地,不要太过分。”
躲在暗处偷窥的少年陈瑾,分明能从那白面书生模样的人神色间窥到戾色和凶相,那人眉心好像开了天眼,现出一束暗红色的血光。
……
在债主频繁的上门争吵与邻里间奚落声中长大的陈瑾,对这些场面习以为常,并没当回事。他从遍布罅隙的木头板子后面冷漠地移开眼球,很快又被更为骇人的声响吸引注意力。
又一轮债主砍砍杀杀上门来了,可不就是远近四方排场最大的高利贷放债团伙。那几人就在巷口和陈九还打了一架,让几户邻居门前都溅了血点,鸡飞狗跳。
陈九再踏回家门时臂膀上有一块新鲜伤口,口中骂骂咧咧:“妈X的,老子有的是钱,但一分都不还给你们!”
陈九正对上女人惊恐如鸟雀般的微弱眼神。
本就不太结实的床单撕裂揉烂的动静中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和哀求。那哀求声时响时息最终被男人粗暴的喘息吞没……门后偷窥的少年面对这样粗野暴虐的场面感到生理性的厌恶和作呕,他看到陈九狞笑着又一次扳过蔡红英遍布泪痕的脸,强迫对方面对床头那张岳丈岳母的合影。
这也是陈九的一块心病,混混人渣从一开始就让蔡家老人瞧不上眼,不知怎的花言巧语骗到了蔡红英下嫁。因此陈九每次在床上撒野,都要摆正那张照片,仿佛这样就是在他岳丈面前强暴了自己老婆,发泄胸中一口腌臜的恶气。
大恶人做完一切恶事,喝干两罐啤酒,没有收拾随身任何细软,再也瞧不上那些破烂家什。这人临走给女人留下几件新买的时装裙子,给儿子留了一个学期学费。
那个傍晚,陈九在荣正街家中只待了约摸一个小时,之后迅速离去不知所踪。这是这人最后一次在家门口视线中露面,从此了无踪迹。
但陈九并不知道,他家小子当晚跟踪了他。
陈瑾那时也不知哪里迸发的勇气,小小年纪胸中也攒了无边的怨恨怒气,从墙角拎了一根铁钩子,怀揣一把菜刀,在他母亲奄奄一息的啜泣声中冲出家门。
做娘的一生懦弱可怜,但儿子性情并不懦弱。
陈瑾那时心里想的,就是砍死大恶人,一了百了。
他循着陈九的行踪,打了一辆当时郊区很常见的三轮“蹦子”。蹦子载着他驶出樊江市地界,好像是沿着某一条乡村野岭土路,进入螺江市一片比较荒芜的地方。这里满目是低矮的民房,稀稀落落点缀在树林土包之间。
他记得几条重要的细节。
陈九从树林间转出来时蹬着一辆破旧宽大的板车,用油布覆盖一车见不得行迹的货箱。
陈九在乡间一条通行货车的大路边放肆地拦车,最终上的就是一辆厢式中型货车,车身白色,车尾有蓝色喷漆的公司图标。陈瑾甚至还能隐约描述出那块图标的款式。司机的声音顺风飘过空旷荒原上一片高高低低的枯黄色野草:“我这是凌老板公司的公车,你拦车干什么啊!”……
陈瑾应当庆幸自己很走运,他当时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假若真要跟他亲爹动起刀来,保不准陈九那个尿性,虎毒食子将他捏死省得他碍手碍脚。
陈瑾在公路边追车肯定是追不过的,最后跟丢了人,也就没能亲眼目睹陈九最终的下场。他饿着肚子在荒郊野岭晃荡了两天,只得拎着菜刀傻乎乎地又回家去了,因此保全一条小命,也与平生一笔巨富擦肩而过。
……
……
他们几人,此时就坐在医院一间大病房内,摒弃闲杂无关人等。受了伤的薛队长只让医护将伤口简单地止血包扎,斜靠在床头听取小陈同学的口供。
陈瑾讲述的往事在高潮处戛然而止,前半部令人揪心,后半部竟然来了个直接烂尾。
“然后怎样?”薛队长追问。
“然后就没了,我就回家了。”陈瑾眼神十分坦白。
薛谦:“之后你还听到什么消息?”
陈瑾:“之后……然后街坊就传闻他可能死在外面了,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就死了啊。”
这部烂尾剧情还烂得颇吊人胃口,在薛队长面前形成一个没填满的大坑令他抓心挠肝,留下一片影影绰绰的蛛丝马迹,但每一条痕迹都烧脑费神。
像个香饽饽一样被几人争来抢去的那只背包,打开来里面就是一堆相当有年份的古董破烂,是陈瑾保存在福山墓园他母亲的骨灰隔间内的遗物。遗物保存条件不佳,挑挑拣拣之后能分辨出这么几样东西。
几件现在看来款式已然过时的人造丝女式裙装,品味土里土气,散发陈年霉味,应是陈九临走买给蔡红英的衣物。
一堆扁担工签下的运货单。这种东西在荣正街十分常见,现在都还有人使用。当年的挑夫们是收取少量订金将货物从一地运往另一地,有时一半路程需要驱车,另半程是走路,走街串巷辗转两三天时间,运到目的地再收取剩余的劳务费。运货单上,有许多陈九本人歪歪扭扭其貌不扬的签名,也潦草记录了各位货主的名字,然而不是机打而是手写,这就给众人辨字认形留下许多暧昧空间。
几个人围着一张小桌,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哧辨认,最终也没认出几枚完整的姓名。
岁月的痕迹令那些纸张脆弱发黄,字迹浅淡渐消,饶是咱们严总这样眼神很好的把式,也感到捉襟见肘和无可奈何。也就是蔡红英母子这些年来还把这些垃圾当成宝贝似的保留着,准备一代传承一代呢,这也是长期受虐之后表现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
除此之外,还有陈九欠下的高利贷赌债清单,也依稀辨出几个债主的名字。
薛谦严肃说道:“几条重要信息咱们条分缕析一下。
“也就是说,当晚陈九离家临走前,至少见过两拨与他有经济债务纠纷的人,这两拨人可以说都是债主,都不爽陈九这个混子。陈九拍拍屁股想要趁夜远走高飞,债主一定会追,两拨人都有明确的作案动机。
“姓凌的老板的公车这个很容易查到,顺藤摸瓜或许可以找到当年这位开厢式货车的司机,看最后见到陈九的人是谁。
“最后见到陈九的地点也很微妙,三江地三市交界这么一处三不管地带,真是个绝好的案发现场,十五年前这里发生过什么全部搜一遍,能并案的都拎出来并案,事实也就差不多了!”薛谦脑补了小陈同学坐三轮蹦子经过的土路山路,沿着地图的虚拟路线一直追踪至郊外,最后利落地在地图上圈出一个他推测出的原始案发地。
薛队长心里已经有数了,顺着这些线索专业的侦查员很快就能捞出一筐一筐材料。他抬头饶有兴趣地瞭了凌河一眼。
凌河毫不躲闪,直视薛队长逼视的目光。这时候但凡有一丝畏首畏尾,好像自己心虚似的。
薛谦轻飘飘说了一句:“姓凌的老板?凌这个姓可没那么常见。这位凌先生,你别告诉我这是巧合,你今天是顺脚路过了樊江市火车站!”
“我不是碰巧路过,我是来协助薛队长您尽快破案。”凌河答得理直气壮,面对薛谦的质疑目光照单全收不置可否,剩下的话用眼神都说出来了,我不怕您薛队长沿着这些草蛇灰线一路追查到底,我还就怕您不去查,您尽管放手去查!
薛谦用录音笔将陈瑾的口供录下了,又重新听了两遍细细地琢磨。
薛谦突然问:“小陈,你说的‘对对’是谁?什么‘对对’?”
陈瑾回答:“我也不知道,我爸当时就是那样说的。”
薛谦:“这是陈九说话惯用的感叹词?还是称呼对方的名字?”
陈瑾:“不,他不用感叹词……我当时听着,就是叫的那人名字。”
薛谦:“那人当时多大年纪?”
陈瑾:“也就二十来岁吧,看着不老。”
薛谦自言自语:“还有名字叫‘对对’的?如果是身份证大号还容易查到当年的人,这要是个街上喊来喊去的绰号,事隔多年可就不太好查了。”
陈瑾讲话带有浓重本地口音,这个发音类似三声的“怼”。
薛队长在纸上描来划去,百思不得其解。“怼怼”?“对对”?这什么玩意儿?
陈瑾终于道出心头积压多年的梦魇,这时反而好像突然卸掉了重担轻松了许多,整个人眉头都舒展了,埋着头毫不客气吃掉了薛队长的那份病号饭。早知道说出实话竟然这样轻松自在,他早就招供了,以前的固执自卑多么愚蠢。
病房内最安静的反而是严小刀。
凌河旁听薛队长问案,眼光却一直笼罩在严小刀身上就没离开过。他已尖锐地察觉到,严小刀是自从陈瑾交代到某一个故事结点上,面色突然阴暗凝重下去,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凌河用力盯了小刀一眼。
严小刀移开视线,有意避开他的盯视。
凌河有一个瞬间几乎绷不住一步跨到薛队长面前,他可以轻松笃定地说出那个人的名字,让薛队长不用派侦查员出去挖线索了,纯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但他咬着下唇忍了,竟是顾及着严小刀在薛谦跟前的体面,顾及小刀当场的情绪,还是让薛队长自己去办吧……薛谦很快就会翻到真相最后一页。
巫山行云布雨的黑色暗潮压上严小刀的脸,瞳仁间隐约可见一道激流,在狭窄的航道中挤压着咆哮而过,惊涛拍岸,碎裂成浪花。那些浪花碎成星星点点,在严小刀的眼眸间留下复杂斑驳的光芒……
凌河与小刀离开病房时,薛队长又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部署当地专案组同事替他迅速追查几条线索,当年荣正街上欺行霸市的高利贷放债团伙都是何人,带有蓝色车标的姓凌老板的货车及司机,还有三江地交界处某几个村落的情况,需要实地走访,大量查询知情的旧人。
凌河在薛队长面前一脸波澜不惊,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自己与当年案子有任何关联。
但薛谦还是在他几乎迈出房间时喊住他:“凌河,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凌河转身答道:“凌煌。”
查询这些户籍人事信息并不难,薛谦都懒得在陈年档案故纸堆里兜圈子,干脆直截了当地问:“十五年前凌煌是公司老总?他公司注册名称叫什么?”
凌河答:“瀚潮华商集团。”
薛谦随口重复一遍这公司名字,眼神十分精明:“掩埋陈九尸骨的地点是一处发生化学品爆炸的厂房,恰巧当年在大约同一时间发生一场蹊跷的爆炸起火,还烧了人,集团法人和负责人承担了操作疏忽管理不善的责任。如果我没记错,这家厂房当时就属于瀚潮华商集团?”
凌河面露钦佩:“薛队长您没记错。”
薛谦气都没喘,紧逼问道:“陈九的尸骸在今年年初重见天日,是因为有这么个公司低价购买了这块被化学品污染的废弃荒地,打算重新开发,然后就‘碰巧’挖出一堆烂骨头,向警方报了案。如果我仍然没记错,这个注册两年的公司叫做瀚海集团。“
凌河嘴角微微擎起:“薛队记性真好使,佩服。”
薛谦觉着他已经都明白了,意味深长地点头:“成,谢了。”
剩下的废话不必问了,警方很快就能将相关人员分门别类查个底儿掉,一个也跑不掉。
凌河面带由衷之情:“薛队长有伤还辛苦办案,一定保重身体。我等您破案的好消息!”
凌河他们几人当晚在附近酒店下榻,这回酒店房间富余,不需要任何人抢沙发睡了。
然而凌河与严小刀各自心事重重,仿佛都还陷在薛队长刚才病房问案支支脉脉的细节里,站在酒店大厅眼光四散飘忽,不知在琢磨什么。
毛助理瞄了一眼那两位爷的迥异神情,上前一步对前台道:“来三间房……”
“不,两间。”凌河开口打断。
“三间吧。”这回反而是严总口吻轻飘。
“就两间!”来势汹汹的凌先生从前台经理手中捏走两只门卡。
凌河也不解释,一声不吭将其中一间房的门卡抛给毛致秀,旋即转身架起严小刀一条臂膀。他像劫持绑架一样,勒着严小刀的腰,快步上楼进到他两人的房间,用后脚跟将房门踹上,还特意上了两道安全锁,让外人绝对打不开门。
严小刀知道以凌河这人的精明善察,他的脸色哪怕瞒得过薛谦,都瞒不过凌河,今晚这场龃龉是势在必行躲不过去。
“你别闹。”严小刀沉着脸推开对方,正二八经地整理衣服领子,思忖今夜如何应付。
凌河就没有给他在周身建起防御堡垒全副武装到牙齿的机会。凌河被他甩开时,反掌重新摽住他的胳膊,竟然用了一招空手道的锁技和摔技套路,反关节扭着将他摔在了大床上!
严小刀也不至于瘸了一条腿就打不过,是不想跟这人动手动脚。但凌河的不依不饶让他心生几分恼火,低声道:“小河,有话咱俩好好说。”
难得一声亲昵的“小河”,严小刀已经心软心虚了。
凌河根本不理会他的示弱,将他推倒在床试图直接压上。
“你……没大没小,有完没完?”严小刀蹙眉撩起他结实有力的左腿,拱着凌河的臀部猛地将人掀开,试图脱身。凌河长手长脚纠缠起来毫不吃亏,竟然再次发力,来了一招锁臂擒拿术,从后面勒着他脖子将他勒回床上!
两人动作很大,力气刚猛,没几下额角都微微洇汗,喘息渐浓,再打下去就要激出火了!
严小刀还是心软,认命地松开胳膊,仰面躺在大床上:“你说吧,你今天想干吗?”
凌河顺势骑到他腰上,薅起他衣服领子:“小刀,陈瑾那个小祸害都坦白交待了实情,你还不向薛队长交待?”
严小刀:“我交待什么?”
“在我面前你还装?”凌河俊秀的脸上洇出一层由怒容拼凑的红潮,“小刀,你才是真正的知情者,你最清楚陈九最后一次出现在家门口那个前来催货的主顾是谁!”
严小刀说:“我当时就不在现场,又看不到监控和照片,我能确知什么?”
凌河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势汹汹,压住严小刀两侧锁骨低声吼道:“那个在三江本地方言里绰号‘对对’的人是谁?你为什么不直接向薛队长坦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