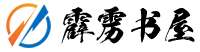周末正午时分的“优而思英语育才学校”大门口, 是家长们接送孩子上补习班的时刻, 上午的一拨学生往外走,下午的这一拨手里拎着包子酿皮汉堡之类各种简餐, 正在往大门里涌。片刻的交通堵塞, 在学校大门口呈现出由人流汇聚而成的一个大漩涡。一群望子成龙病急投医的家长和那些每日疲于奔命焦头烂额的孩子, 全部被卷进这个劳民伤财的大陷坑里。
大门口横七竖八趴满各色社会车辆,四个轮子的当仁不让堵住正门口显示傲慢骄矜, 其余两个轮子的电动和脚动款黑压压地堆在后面, 其实都在这座大陷坑里前仆后继地扑腾着,谁和谁也没有多少高低贵贱的分别。
英语学校的隔壁, 是一片荒草地, 市府林业部门正准备在此地搞些绿化, 以整齐划一的方形石板和侧柏树银杏树覆盖上这片狭长的荒地。这一小块地方已经废弃荒芜很久了,就像新老城区边缘三不管地带镶嵌的一块疤痕疖癣,垃圾和狗粪堆积成山。
毛致秀把防霾口罩都戴上了,皱得眉毛不是眉毛, 鼻子也不是鼻子, 面对眼前垃圾污秽遍地的景象, 喊道:“凌总,就不可能是这里!您还真要进去刨垃圾堆吗!”
您刨垃圾堆挖坟掘墓能掘出当年的证据?姐坚决不动手帮你刨!毛仙姑心里吐槽。
凌河竟都没有戴口罩,眉头紧锁出茫然和焦急,指尖捏着他们弄到的名单信息,沉甸甸的心思足以将周围销魂的气味摒除在他严密运转的思维意识之外。
严小刀蹒跚着脚走过来,望着前方:“按说就是这个位置, 当年的‘慈恩堂’福利院么。”
凌河郁闷道:“可是这个福利院早就拆掉了,房子原址都没了,荒废多年。”
如今再行施工盖上绿化,陈年的痕迹真是一丁点都找不见了。
福利院早都没了,假若当年里面住了一批孩子,姓甚名谁流落何方恐怕也很难找了。民政部门的官方留存信息七零八碎少得可怜,周围商铺频繁易主,街坊之间面孔冷漠陌生,什么都查不出来。
市府民政办公室科长跟他们说:“那个‘慈恩堂’?十年前早就查封处理了,你们还要找?”
严小刀问:“为什么查封处理了?”
科长秉承着面对人民群众时一贯“有求懒得应”的标准公务员态度,耷拉着眼皮与脸皮,翻看着桌上资料,绝对不抬眼看人:“查封肯定有查封它的道理,有违规的事情。”
凌河:“怎么违规?做什么了?”
科长当真不耐烦了:“它怎么违规是我们政府处理的事情,你就不要问!”
凌河眉头一蹙,眼峰吊上发迹边缘时已曝露出愠怒颜色,双臂往那办公桌上一撑,眼瞧着要往小科长脸上喷一口了。
严小刀眼明手快,悄悄从后面扥住凌河的裤腰,把人扥回来:别发火,这地儿可不是你这么粗暴办事的!
跟衙门里各类官僚主义和势利眼打交道,凌先生这位外来的和尚可就没经验了,你以为还能用在荣正街小巷子里对付鸡贼大婶那一套?还是游轮上对付渡边老人渣的那一套?但这种事是咱们严总的擅长,各种嘴脸他见多了,无论什么人他都能招呼。
严小刀掏兜摸烟,手指奇快,直接在衣服内兜里就搞了个小动作,然后连烟盒一齐客气地递给对方,爽快一笑:“您抽根烟,咱慢慢说。”
科长默不作声以眼皮余光一扫,烟盒里只有一根烟,塞了一卷钞票。
科长叼了那根烟顺手就收起烟盒,双方的你来我往是无缝衔接。办公室内顿时云开雾散四海清平,官民在轻松和谐鱼水之欢的氛围下交谈顺利,严总笑着给对方点烟。
“慈恩堂”福利院是一所官方登记在册的福利设施,每年吃官粮拨款,还时不时收受私家企业的捐物捐款。然而,这堂子在十几年前就遭查关闭,原因竟是贩卖人口!
严小刀一开始还以为就是虐待孩子,不曾想当年这所福利院的所谓院长领导见钱眼开,吃了熊心豹子胆,偷换了做人的良心,竟以身世可怜的孤儿们易财易物。
当然,这种贪赃枉法的行径仍是掩盖在某些合法交易的背后,做得并不算太丧心病狂。这社会上毕竟有许多人是想尽办法求子而不得,官方设置的领养渠道条件严苛且费时费钱,那么私下暗度陈仓的黑市渠道,可就全凭福利院长一人点头了。
福利院长名叫雷征,那时候也是当地小有名气和势力的人物,性格张扬,人送绰号“雷老虎”,被查之前曾经出手阔气地买了好几套房子。
钱就是这样赚到的,孩子悄悄出手,利润由个人中饱私囊,至于孩子最终瓜落谁家,将来命运是福是祸,谁还在意?自求多福吧!
“到底有哪些孩子被卖了?警方有试图解救吗?您这里能找到当年的记录名单吗?”严小刀忙问。
科长在桌上一摊手,耷拉着眼皮冷漠地摇头,他关心那些?这回塞钱也编不出情节。
凌河厉声问:“那卖孩子的人渣院长呢?”
科长以不耐烦的表情下了逐客令:“当时可能对雷征判了轻刑罚了钱,后来的都不知道!”
一直站在后面一言不发的毛致秀,临走时突然上前重重拍了那小科长的肩膀,拍得对方一愣几乎要发飙。毛仙姑两道秀眉一挑,视线将对方肥厚的面皮狠狠一剐,冷笑道:“赃烟抽多了您可别呛死!”
从楼道里出去,重新站在旷野的阳光下,毛致秀将那塞满人民币的烟盒抛回给严总。
严小刀俊朗地一笑,对毛姑娘的爽利脾气由衷地欣赏,忍不住一伸大拇指:“手很利索,我不如你!”
小刀、凌河、致秀三人,有那么片刻陷入集体沉默,彼此只用视线神交就能明了对方内心的愤慨和难受。今日在场的这三位,恰恰就是三个都没爹没娘的孤儿。
凌河父母早亡,都是在他知晓的情形下眼看着去世的。他清楚事实,却无能为力无法挽救父母双亲悲剧性的命运。
毛致秀出生即遭遗弃,而后被送至寄养家庭。这种所谓的寄养家庭,许多就是以寄养孤儿为缘由每月领取政府月供以及减税证明,毛致秀十几岁时用冰镐报复了屡次试图对她不轨的继父,离家出走逃跑再也没有回去,结识了凌公子。
而严小刀连亲爹亲妈究竟是谁都不知道,他完全不了解自己真正身世背景,也不愿深究细想。堂堂七尺男儿立于天地之间,何处不能安身立命。
毛致秀不爽地吐槽道:“如果陈九的儿子当真已经被卖掉,咱们上天入地也没处去找了!或许当年就没活下来,早就饿死啦!再者说,那小孩子就能知道当年凶手是谁?”
凌河轻声说:“假若真是这样,只能指望薛队长抱着那堆腐烂的尸骨研究出凶手了。”
严小刀心里憋着内情,抱着一团烂骨就研究出凶手是谁,当真不是一件容易事,不知道薛夜叉这回能不能开挂了。
几人沿着便道再次从旧址荒地旁走过,途径英语学校门口。一辆车子从校门开出来,自他们眼前经过,带孩子的家长隔着车窗向驾车人哈腰问好:“芦校长您出去啊!”
驾车人是一位约莫四十五岁中年男子,笑眯着眼挥挥手,挺有领导风范。
轿车被前面几辆三轮摩的暂时堵住去路,严小刀拄拐略不方便,可还是晃悠着上前,一手搭在车窗沿上,客气一点头:“您就是这家英文学校校长?”
车内中年男子身着西装,风度翩翩且面色坦然:“啊,嗯嗯,我是啊。”
严小刀忙问:“您在这地方开班办学也不少年吧?您知道您这学校的隔壁原来是什么地方?”
“隔壁?”中年男子眼神无甚波动,敷衍一笑,“不知道啊,隔壁不就是一块荒地嘛!”
毛致秀声音清脆爽快,像口里嚼着一只脆梨,扬声道:“校长,您听说过隔壁以前有一家‘慈恩堂’福利院吗?您认识他们以前什么人吗?”
中年男子眼皮下一双眼球明显地针缩了一下,眸底就如一汪褐色酒水遭遇猝不及防的一碰,在透明酒杯中瞬间晃动闪烁了一下,但经验老道地迅速恢复如常:“呵呵,真的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说过……”
毛姑娘手脚麻利儿帮忙搬开碍事的那辆摩的,中年男人正要踩油门赶快离开,这时候一杆湿哒哒的大墩布挥舞着满脑袋布条子,直不楞地捅在车前挡风玻璃上,女人泼辣的叫骂声灌入耳膜:“芦清扬你还躲!姓芦的你开骗子学校赚昧心的黑钱!你赔钱,赔钱,赔钱!……”
周围仿佛从人缝里突然冒出了七八人为一伙的闹事者,那些人唯独没有拉横幅之类,但其他家伙都齐全了,锅碗瓢盆似的全部往芦校长车上招呼,就闹起来了。
毛姑娘吓一激灵,迅速扶着严小刀跳开那一根大墩布的袭击范围。
凌河没有毛致秀上蹿下跳那样敏捷,意欲上前搀扶的两只手竟然都落了空。他眼瞧着小刀被裹进致秀的臂弯。虽说明知毛姑娘是丁点别的心思也没有,纯属善意好心,然而但凡瞧见小刀沾了旁人的皮肉,都不开心呢……
学校门口本就人多拥挤,攒动的人流在芦校长轿车周围“嗡”一声散开,唯恐受到波及,先避开数尺距离,却又都不走远,步伐整齐地自发组成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圈,将车子围住无法离开。这就是典型的天朝式当街看热闹,人人面露好奇兴奋但默不作声地品味这看热闹的销魂乐趣。
在学校门口闹事,可以称为“校闹”。几名校闹男女扒着芦校长的车窗玻璃,一大瓶蓝墨水直接泼了进去!芦清扬毫无抵抗还手之力,原本相貌堂堂的一张脸顿时被一层靛青色的水膜严严实实笼罩,如同抹了一张窦尔敦的蓝脸谱。
中年男子的仪表风度与那张赖以生存的面具顷刻间被扯碎、坍塌,芦清扬里面那层脸瓤子神情大变。
校闹们向学生家长一条一条地历数控诉这所骗子学校的不是。
芦清扬你个坑蒙拐骗凡事只认钱的大混混!
披个冒牌教育工作者的皮弄个坑爹的补习班和出国留学套餐,你一句英文都不会讲全都骗人的!
坑了家长十几万块钱,吹牛吹得天花乱坠能一键直通给我们家孩子办到澳洲留学,拿一堆看不懂的英文材料糊弄,最后办下来的是毛里求斯!我们家孩子要去澳洲,你他妈的坑十几万把我们送去毛里求斯看猴子吗?!……你给我们退钱退钱!!
小刀、致秀与凌河三人,并排挤在看热闹人群的最前排,默契地一齐维持双手抱胸姿势,看个目瞪口呆……
一场热闹最终被赶来的保安和警察劝散,解救了陷入重围中的芦校长。芦清扬那时极其狼狈,原本要出去约会,此时满脸满身肮脏的墩布水和蓝墨汁,靛青色已嵌入眉头眼角法令纹的一道道沟壑之间,这人原本温润的相貌褪去,表皮隐隐浮现出几分暴躁和狰狞之相。
一块白布手帕从车窗外递进来,芦清扬躁郁地一把抓过手帕,囫囵式的抹一把脸。
递手帕的人贴近车窗,细致入微的一双眼带着精光打量他:“芦校长,您真不知道您学校隔壁有一家福利院?”
“哪里有福利院?早就拆了!”芦清扬抬眼一看长发的俊脸,调开视线。
“确实拆了,十几年前拆了。”凌河莞尔一笑,“你学校门口挂着一枚十二年校庆的金字招牌,芦校长资历也挺久啊?”
芦清扬法令纹之上肌肉微微抖动:“都说了不知道!你是警察吗你凭什么问我?”
“你认识雷征么?”凌河突然盯住对方眼底闪烁乱跳的光芒,“还是你就是雷征?!”
“谁是雷征简直他妈的莫名其妙!”芦清扬恼羞成怒,竟爆粗口对凌河骂了一句,恶狠狠道,“我一个男人你看不见吗我怎么会是雷征?!”
芦清扬口不择言,飞快地发动车子,狂塞硬挤地将车开走。
这位教育工作者,说话可一丁点没有教书育人的气质风度,堂堂仪表外皮包裹的就是一副粗野村夫的本质,枉称校长头衔,看来也是个半路出家的冒牌货,从事私人补习班和留学业务圈钱。
毛致秀莫名琢磨着芦某人临走那句话:“他是男的怎么不可能是?雷征不是男的吗?”
凌河与小刀头碰头地翻阅名单资料,凌河嘴角划出一道充满妙趣心情的弧度,抬眼与严小刀会心对视:“跟上芦清扬的车。”
毛仙姑的长手长脚拥有最敏捷的一类灵长类动物的行动力,但眼神一般,能说流利普通话就很不错,读写就真不能指望,都没看清楚资料的标注。
人的名字有时只是具有迷惑性的一枚标签,充满威武阳刚气息的姓名背后可未必就站着一个威武阳刚的爷们。凌河笑出一丝表情:“芦校长撒谎,他知道这个雷征雷老虎是一头母老虎。”
芦清扬兜着一身靛青色汤汤水水在路上飞速驾驶。墨水的痕迹干燥凝结后,这些线条在他面皮上勾画出更为清晰真实的一张面孔。
哼,芦清扬嘴角抖出轻蔑的一声,老子知道你们几人想打听什么事!一堆陈年烂事鸡毛蒜皮,查什么查?不就是私底下给几个娃儿找了落脚的人家吗,不就是从中赚点外财吗,本来就是一群没爹没娘命若浮萍草芥的孤儿,当初没有老子喂他们一口吃的,早就是路边的饿殍,沦为狗食!他们还得感谢老子这辈子的积德行善,至于最后卖到什么样人家,日子过得好不好,那就全凭你自个儿在如来观音面前的运气造化了。
不是还有娃儿卖给了美利坚国过来买孩子的,不用考学您就出国了,你们家祖坟上插花儿了!
将来过得不好也甭来找老子晦气!
人活一世上,有的是捞钱机会,就看你胆儿肥不肥,看你敢不敢捞。
孤儿院被查封倒闭了又怎样?老子一家子不出三年就翻了身还是十里八乡最牛逼的好汉!
这芦校长年轻时大约也算个美男子,有些长袖善舞的社交魅力,赚钱全凭迷惑人的色相和忽悠人的嘴,年纪大了四十多岁仍是一位颇有魅力的中年男子。然而此时,淡青色的面孔仿佛从那下垂的嘴角处生出一对青色的细长獠牙,露出凶相……
哼哼,老子知道你们几个想打听谁,这几个月他妈的公安都来好几趟了,各种盘问,烦不烦?
昨天还刚来了一个,被我三言两语打太极拳哄骗着去城西北找福利院去了,让那个条子满城转悠消磨时间去吧!
芦校长急速飞驰回家,洗掉狼藉,重新换上一身料子西装,用发胶将发型侍弄得油亮水滑。打扮成一副业内精英的人模人样,这是要去约会。
中年男子身家体面而且有财有势,钱包鼓胀起来难免保暖思淫欲,此时不风流等到七老八十的还干得动么?活一辈子不能亏啊!芦清扬接上他在外面包养的老情人,驱车往公园偏僻地方行驶。他一路上单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志得意满地抚摸着裤腰带,咂摸着这些年的意气风发,老子在这三江地,无论干啥行当都是平趟!
这大中午的艳阳高照,公园角落背风无人处,一对中年野鸳鸯在车内解开裤子浪荡苟且,趁热打铁颠鸾倒凤,光天化日之下行毫无廉耻之事。
就在芦校长车子后面不远的隐蔽处,跟踪三人组全部憋在车内,正在抓阄决定谁上。
开车的毛仙姑把香肩一耸,伶俐的口齿毫不客气:“两位爷们,这种事不要为难姑娘家,您两位划个拳呗!”
凌河先下手为强手一指严小刀:“严总您去。”
严小刀煞有介事地一瞪眼:“不是你出的主意跟踪抓包?凌老板您请吧!”
凌河板着面孔:“我不想看那个,严总您最有经验。”
严小刀冷哼道:“老子有做的经验,没有偷窥捉奸的经验。”
毛致秀烦得拍了一下方向盘,差点不慎拍响喇叭,赶忙把手缩回,埋怨道:“你们俩这么墨迹?万一那姓芦的衣冠禽兽是个阳痿早泄呢?三分钟泄完了凌总您可就拍不到要挟他的证据了!”
“……”
这位姑娘家讲话如此口没遮拦荤素无忌,车后座上两位男士反而都不吭声了。
一看那两位没声,毛致秀再接再厉,回过头故作恍然醒悟状:“哎呀,老板我都忘了,您还没有交往过男朋友,您还是一位清纯少年!您还像当年我刚认识时一模一样都没变啊,早泄是什么您恐怕也不懂!”
凌河回敬道:“秀哥你懂,你交过男朋友吗?”
毛致秀以纤纤素手打了一枚响指,浑不吝地说:“姐都是看好莱坞电影学的!”
严小刀半握拳捂了半边脸,憋住笑意,生活在毛姑娘的各种调剂之下如此有滋有味。
凌河也不知被触到哪一处痛点,低声骂道:“肮脏。”
咱们凌总骂完这俩字,没有再叽歪墨迹,抄起手机推开车门就过去了!
严小刀他们这个位置监视角度很好,然而他一双眼早就不是监视姓芦的动静,全部视线都罩住凌河。凌河正在隔窗快速偷拍,脸却嫌恶地扭到一边,看起来确实忌讳车内人野战行房的苟且之事,很不情愿看到那两副半裸的不洁身躯以老汉推车的庸俗姿势发泄着文明人压抑在虚伪面皮下的原始冲动。凌河一定感到十分恶心……
然而凌先生做事一贯也荤素不忌,寻求最便捷省事的路径达到他的目的,不介意使用这类不上台面的手段。
凌河恰好不在眼前,这机会是很难得的,毛致秀点燃一根细长的香烟,从后视镜里与严小刀对视:“严先生,您也看出我老板有点奇怪吧。
“他有那方面心理障碍,身体上也有些障碍,这么漂亮的一个人,这不是暴殄天物么,当真可惜了。我劝他去看男性专科或者心理医生,他也拒绝。有一回我们一群人在别墅里看黄片,就是欧洲拍的那种情色片子,他都不能硬。”
严小刀骤然听到关于凌河的这种隐私,想刨根问底都不知问什么好、从哪个角度问……他内心五味杂陈,盯住后视镜里毛姑娘的眼。
毛致秀轻吐出一串带有忧郁灰白文艺色调的烟圈:“你知道他以前经历过什么。”
“什么?”严小刀脱口而出。这些日子他表面绷得全无所谓,过去的一段感情已不会回头,然而事实上他在意关于凌河的一切事情!
“我认识凌先生很多年了,他所有的变故遭遇我都一清二楚,所以我乐意帮他做事。”毛致秀口吻平静,“严先生您自己去问他吧。假若哪一天他对您坦白说实话了,那就是他‘愿意’了。”
毛致秀点到为止,随即闭口再不说出一个有用的字,就不停抽她的烟。
这一招确实成功戳到严小刀的软肋,简直就是抓心挠肝钓他的魂。
在之后许多天里,毛致秀的话都让他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琢磨。恰恰因为曾听说一些让凌河这个名字沾染尘垢的江湖艳闻和蛛丝马迹,面对正主他问不出口,说到底还是心疼在乎这个人。
凌河也只拍了一分多钟,用来敲诈勒索足够了。
一幕激情戏恰逢演绎到高潮,两位甘于奉献的色情片场演员激战正酣,骤然听到轻敲车窗的指音,芦清扬眼睑带汗,正待大展雄风,一回头瞥见面带讥讽嘲弄意味的凌先生……
芦清扬被这一惊吓,这一趟真的早泄了,立时就绵软下去,从未在情人面前如此丢脸,颜面扫地。
凌河嫌恶地往窗内一瞥,姓芦的那位情妇也不年轻,半老徐娘神色慌张地用衣服遮挡胸脯,一身白花花的肉混乱颤抖,指不定又是哪家出来偷腥解馋的如狼似虎的妇人。
“拍什么拍?!”芦清扬的衬衫西裤仍然凌乱,扣子都上下系错位了,发型被发胶和汗水混合着黏成一坨,愤怒地喘息道,“你到底要怎样?你不就是想打听‘慈恩堂’吗!”
凌河直截了当:“雷征你认识,她什么人?”
芦清扬瞪了一眼,还没来得及答话,他情妇全替他招了:“不就是你们家那只雷老虎么?哼,还说要拿菜刀砍死我的!”
芦清扬蓦地泄了气,无话可说。
“原来是这样。”凌河挑眉大悟,“原来芦校长您开的是一家夫妻黑店,做了大半辈子的人口贩子生意!只不过,您两口子以前是开福利院往外面倒卖孤儿,现在是开英文学校往三流四流国家倒卖学生?”
“福利院卖孤儿?”他情妇也惊诧了,“芦清扬我以为你这种怂货只敢卖假证、卖肾,你还卖过孩子?你、你这不是犯罪吗?”
凌河懒得多废口舌,晃了晃手机,一记无形的刀戳中芦校长心口:“发给您家母老虎呢,还是发给您二夫人家的公老虎?不然发双份给他们欣赏?
“这要是在古代,您两位是要被浸猪笼的,您就招了吧。”
“……”
芦清扬将西装穿上,做模做样地一捋发型,破罐破摔道:“你不就是想打听那个姓陈的儿子?我又没卖他,他死活关我个屁事?!
严小刀此时已拄拐站在凌河身后,问出他最关心的问题:“陈九的儿子现在人在哪,叫什么名字?”
芦清扬不屑哼了一声:“陈九一个杀人犯,杀人犯能养出什么好东西?
“他儿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初在‘慈恩堂’那两年就是个很难搞的刺头,早就想给他卖了都找不着买主,谁家乐意买他这样性情不讨喜的男孩!
“后来他跑了,吃我的穿我的一丁点恩情都不念,他就直接跑了,狼心狗肺的东西,没替我赚来一分钱!
“过了十多年我偶然当街遇见他,那小子长得很有特点,一脸戾相,过去这么多年我还能一眼认出来。”芦清扬说到此处突然猥琐地笑了,笑得很不善良,“我没想到他还敢在附近住,竟然还考上大学了,他是真怕遇见知晓他底细的老熟人啊,特意还改了名字。”
“他以前叫陈芃,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平凡人的凡,命若草芥一个贱种嘛,这名字最适合他!他自己不乐意,嫌弃这名字不吉,后来悄悄改了,可惜再怎么改也改不掉他卑贱的出身、被人唾弃的家庭!他改成个王字旁,还他妈的惦记想当上贵胄之士公子王孙呢,呵呵,做白日梦!”
凌河干脆利落地威胁道:“麻烦芦校长把关于陈芃这人以前所有资料交给我们,换我手里这个视频。不然明儿一早上,全城的人都会在优而思学校对面的广场大屏幕上欣赏到这段精彩短片声情并茂的现场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