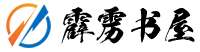一个人的当下
容姿
我与她虽是第一次见面,却知道她迄今为止的事业有多傲人。如今她年事已高,我一面与她泛泛而谈地寒暄,一面焦躁不已。心里很想问她某年或某时发生的事。问她写那本书时几岁,在烦恼什么,做过些什么……还有那件大事发生时,她有何感想……
直面活生生的历史见证人,我虽然情绪激动,说的话却浮于表面,无法触及核心。时间无情地流走,很快就到了我该告辞的时候。
唉,真是浪费了大好机会……我脑中这样想着,却见她露出沉静的笑容,温文尔雅地站在我面前。
这一刻,我领悟了。
她过去做了什么并不重要。正是经历了各种事件,克服了各种困难,才有了此时此地这位优雅的老妇人。她耐心从容的说话方式、眼角的皱纹、略带悲伤的笑容、稳重却不失辛辣的措辞……一切言行举止,都沉淀着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这一想,我又觉得与她共度的几个小时只顾着激动,没能以平常心享受对话,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浪费机会。
时间与经验创造了她的“当下”。既然如此,我应该认真对待的不是她的“过去”,而是她的“现在”。
曾经,我初遇另一位名人时,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在某个宴会会场,我发现一位小个子女性放松地站在一根大柱子背后。她一度绯闻缠身,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我也是通过新闻里的照片知道她的。而此刻,她站在离我仅有几米的地方,隐藏了存在感,摒除了周围的喧闹,显得娴静又超然。过去那么活跃的人,如今变化竟这么大吗……想起她以前有过的种种骚乱与风波,看着眼前这个脱俗又随性的人,我不禁对她心生好感。是那些坎坷的岁月塑造了如今的她吗?我感叹着,对她沉静的模样看得入了迷。
接着,我想起揭发过“老年歧视(Ageism)”现象的女性主义者芭芭拉·麦当娜的演讲。她在七十多岁的时候曾说:
不要以为“你跟其他老人不一样,精力充沛又有活力”这句话对老年女性是种夸奖。如果对方以为这是夸奖,你的话就助长了社会对老年女性的歧视。
不要对老年女性说“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多了”。这只是你的自以为是,你在贬低岁月加诸人的痕迹。
老年女性不是为了你们年轻女性而存在的,也别以为你们能帮到我们。
不要以为老年女性生来就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会如何,那都是崭新的、不断发现的过程。老年女性对此谈论得越多,就越是能给我们习以为常的、否定我们的这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这一点,我们迟早能有所体会。
这位银发的小个子女性在美国女性主义者的聚会上发表了如此激进的演讲。当时,三十多岁的我也坐在台下。因为心中感佩,我走到初次见面的她跟前请求:“可以让我把你的演讲介绍到日本吗?”其结果,就是后来翻译引进的《看着我的眼睛——女同性恋谈老年歧视》(芭芭拉·麦当娜、辛西娅·瑞琪合著,寺泽惠美子等人译,原柳舍,1994年)。
她还写了下面的内容:
年轻女性会跑到我这种老女人身边,请求我把过去的生活经历讲给她们听,却从不问我每天有何感想、做了什么。没错,她们只在乎我的“过去”,却对我的“现在”漠不关心。我明明不是“过去的人”,依然继续生活着,只不过是个年龄大些的女人。老年人不是过去的躯壳。非但不是,他们还正在无人走过的年龄段,积极探索日日崭新的现实。
在我时常拜访的老年社区里,大家做自我介绍时都不会提及过去的职业和经历,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因为每个人都已经退出了职场。“虽然不知道其他人在外面的世界是什么身份……”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无名之辈。
他们不提及个人背景,但会分享自己眼下沉迷的兴趣。比如,“我最近在画油画”“我加入了歌剧爱好者俱乐部,很期待一年一度的公演……”“我想学陶艺,所以来到这里”。
不过,随着彼此慢慢熟悉,会发现对方的爱好、特长也都不再重要。
有位年长的朋友告诉我:“上野啊,这只是世人所谓的兴趣。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个人做了些什么。”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做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本身。这不是头衔、地位所能衡量的,而是那个人的样子、举止、说话方式,以及做事的态度等呈现出来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容姿,是了解这个人最重要的窗口。我越来越认同这种观点。因为我想与之共处的,都是些容姿不凡的人;我想与之重逢的,也都是些让人神清气爽的人。
与人见面时,我们很容易以对方的过去为标准来衡量对方。我也常被人当作“传说中的上野女士”。但与人交往,接触的不是对方的过去,而是现在;不是对方的工作,而是人品。无论一个人的成就多么辉煌,要是毫无体谅之心,也不会有人搭理。过去的地位和成就不能成为此时此地傲慢无礼的免罪符。
一个人过去经历的战场也好,烦恼也罢,都会体现在这个人的容姿上。即使不细问,也能看出此人的“当下”正源于种种过去。然后你会心生感慨:幸好没在那时候认识她/他。经验与时间的磨砺,使眼前的人散发出旧皮革般的温润光泽。而我只需享受当下。
多么奢侈啊!
仪式
最近这一年,我不断地接到熟人朋友的讣告。
不久前,丧期明信片还是由朋友寄来,告知其父母或其伴侣父母去世的消息。到了最近,去世的却成了他们自己。没有直接往来的人过世尚还能接受,可有过亲密交往的朋友死去,却让我怅然若失。啊,那个人再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了吗?与之有关的记忆都归于过去,再也无法更新了吗……这种情绪令我沉痛不已。
我向来讨厌冠婚葬祭[1]的仪式。明明不欲庆贺,却要出席别人的婚礼;明明不了解对方的成长过程,却要在亲戚家小孩入学、升学时给红包。以某个时间为节点,我再也不参加婚礼了,因为一切婚礼都让我感觉徒劳。同时觉得,我连自己的婚礼都没参加过,干吗要参加别人的婚礼……
知道我不喜欢婚礼的学生、毕业生们,都不会给我发婚礼请帖。因为怕我不高兴,连告诉我结婚的消息也都是小心翼翼的。
我自己没有结婚的打算,也对婚礼毫无兴趣。但别人结婚,我还是会送上祝福。想要结婚的对象,就是你眼下决定与之共度余生的人。虽然在当今社会,婚姻关系随时都能作废,但决定结婚时肯定也是相当地激动。一生之中,能遇到让你做出这个决定的对象的次数,恐怕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如果真能幸运地碰上深入理解彼此的爱人,我自然不吝惜送上祝福。这话说得有些绕,总之,得知学生结婚的消息,我都会送上祝福。只是不会参加婚礼。
从某个时期开始,冠婚葬祭的“冠婚祭”我都不再参加。更不会参加别人的出版纪念派对。我从来没为自己的书搞过出版纪念派对。毕竟出了太多书,没精力每本都纪念一次,况且还保不准会惹人厌。
说实话,我也不想出席学生的毕业典礼。因为多少会觉得,我连自己的毕业典礼都没参加过。大学毕业,我在学校的事务窗口拿到了本该在毕业典礼上领取的毕业证书。当我出示身份证,领到毕业证书时,立刻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将其对折再对折,弄得对方目瞪口呆。我觉得这张纸对父母比对我更有意义,所以打算寄给他们,但因为尺寸太大塞不进信封,只好唰唰地折了两下。也因此,我的毕业证书到现在还有折痕。
不过我一直告诉自己,葬礼是截然不同的。
那是告别的仪式。要告别的人,已不在人世。
名人的父母或妻子先于他本人去世时,葬礼往往比较隆重。因为大家虽不认识他的配偶,却跟他本人有交情。反倒是他本人去世时,很多人觉得之前已经尽过人情义务,此番再来送行的人不多,葬礼也比较朴素。
我参加葬礼不是为了做人情。因为不认识遗属,跟他们也没有人情往来。我是为自己去的。
在某个时间点,我与某人的记忆就此中断。看着备忘录里的联系方式,心想:啊,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可要删除时又会犹豫。看着对方的手机号码,也曾想过要不要打一通试试。打给逝者的电话会被接通吗?或许接电话的是个陌生人。我每每犹豫,也就一直没有删去。每当听说有谁去世,我对那人的感受就会失去落点,郁积在心中。我认为,这是因为我没有好好跟对方道别,并由此重新意识到葬礼的必要,它是生者真正把死者送往另一个世界的仪式。
近来,接到某人去世的消息时,我总会问一句:“葬礼呢?”越来越多的遗属表示,家人已将其秘密下葬。虽然是遗属的决定,但我的悲伤也因此无处可去。我告诉对方:“如果有追思会,还请通知我。”但这类通知几乎都是在我即将放弃的时候才来。
或许是考虑到出席者的行程安排,无论死者周几去世,葬礼都定在周末举行的情况越发普遍。大概是因为干冰、防腐技术的进步,能让遗体保持完好无损。在这期间,与遗体共处一室的遗属会想些什么呢?
我的周末时间大都安排得很满,如果临时接到葬礼通知,很难抽空参加。所以大都是在远方独自悼念友人、祈祷冥福,但往往还是难以释怀。
某个周末,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年长女性的葬礼。巧的是那天我居然没有别的安排。虽然她去世的时间并不是为了配合我的行程,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天意,于是决定出席。
到了现场一看,宗派不明的和尚在敷衍地念经,陌生的死者亲戚们肿着眼睛在哭。到场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真是让人待不下去。
那天风很大。出席者的黑发黑衣都在强风中翻飞,我们目送工作人员将遗体搬上灵车,驶向火葬场。在此之前是告别仪式。盖棺前,会场工作人员示意“在场亲朋好友可以跟逝者道别了”,其他人依次上前,瞻仰故人遗容,与故人道别。
但我不想这么做。近年来,尸体防腐技术飞速发展,据说能让死者看起来跟活人一样。电影《入殓师》的成功也让很多人知道了遗体化妆师,死者能在他们的帮助下焕然一新。但那毫无防备的模样,比刚睡醒的脸更为私密,我不想看见,也不愿这样的自己被人看见。故人想必也跟我一样吧。我还记得她温和的笑脸。这就够了。不能让遗容替换我记忆里的笑脸。所以,唯有这个“告别式”,我没有参与。
遗体与遗容,无疑是死亡的物理证明。或许有人觉得,看过遗体遗容就算真正的告别,由此接受故人已去的事实。但对我来说,有葬礼就足够了。如果无法参加葬礼,我会在几周后,等遗属们心情平复、葬礼上的花被清理,才去对方灵前献花。如果我不认识遗属,也没法亲自到场献花,就自己买束花,举行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葬礼”。这是我为自己举行的仪式。若非如此,就没有送走对方的实感。
仪式也有仪式的作用吧。这样想,或许是因为我也老了。
* * *
[1]冠婚葬祭:分别指成年、结婚、丧葬、祭祀。
痴呆
比起“认知障碍”,“痴呆”的说法更显亲切。
用关西话说“你这呆子”,比关东话的“蠢货”听来更可爱,此外还有“痴迷美色”“痴迷欲望”等说法[1]。最值得一提的是有吉佐和子女士《恍惚的人》(新潮社,1972年),标题里的“恍惚”,包含了“痴呆”和“恍惚”两层意思。“装傻”与“吐槽”的配合,在漫才[2]里缺一不可。“装傻充愣”,则是人际关系里颇有难度的技巧。“认知障碍”怎么听怎么像病名,痴呆则像一种性格,更有人情味。
俗话说“一病消灾”[3],我身体本就不算好,一旦耗神过度,要么喉咙肿,要么流清涕,动辄感冒。这样一来,身体机能也会自动暂停。虽然穿暖和点、钻进被窝好好睡一觉就能恢复,但反过来也意味着,我没法强撑着工作。如果有人在我这个年纪还能熬夜,我会觉得对方是超人。
有时候工作到深夜,明明再坚持一个小时就能收尾,但我的眼睛已经睁不开,脑子也成了一团糨糊。那些突发脑梗或猝死的人,大概都是体力不错、总把自己逼到极限的人。可我做不到。
身体上的小毛病不少,一边调理,一边磨磨蹭蹭活了很久……这是我对自己老后的想象。如今的社会,要死也不那么容易了。毕竟营养、卫生、医疗、护理都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即使卧床不起也能活很久,这是文明的象征,没道理去诅咒。
只要活得够久,痴呆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不知为何,听说痴呆患者里,退休教师的数量颇多。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我觉得这是因为口齿伶俐的人即使痴呆,也会变成口齿伶俐的痴呆老人,因此有很强的存在感,在痴呆人群里特别显眼。
有一次,我带学生到外地城市参加护理事务所的调查。学生去日间护理机构找志愿患者做完采访,回来后告诉我,接受采访的老人说:
“我参加某个考试合格了,就被带到这里来工作了。”
这位老年人似乎把“护理必要性认定”测试合格,理解成了考试合格。把他往返日间护理机构,当成了“来工作”。但这家机构的职员、老人的家人对此十分重视,并没有否定他一厢情愿的理解。
“说是工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听其他人说说话。工资也没有,但他们会给我准备午饭,这就算工资了。”
这位老人的说法倒也逻辑自洽。当然,他的午饭是家人付过钱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才认为是给他的报酬。“我之所以愿意来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聊天,是想让你们知道,人就算老了,也可以像我一样积极乐观哪。”
我们事前跟这家机构沟通过,说想问患者一些问题,希望机构方面帮忙找一位能配合我们的人。刚才说的那位老人就是毛遂自荐,主动前来的。他的话从头到尾都条理分明,为人也很乐观。
他是位退休教师。
调查归来的学生忍不住笑着说:“就像看到了未来的上野老师!”
我走访过许多机构,也见到了许多老人。其中不乏动作迟缓、毫无生气、一整天都只是坐着发呆的老人。如果去全是老年认知障碍者的护理机构,还能看到一动不动、眼神空洞,仿佛只是在等死的老人。
有访问者问:“即使变成了这样,也非得活下去吗?”
面对这样的提问,一位护理专家回答说:
“你们看,一到吃饭时间,那位老人还是会好好地张嘴吃饭对吧?有食欲,就意味着还有活下去的能力。每个人都会死,在死亡来临之前,让他们好好地活下去,就是我们的工作。”
看过许多机构之后,我放下心来,觉得以后即使变得跟那些老人一样,能继续活着、在别人的帮助下活着也很好。不过,必须委托我信赖的人和护理机构。
即使痴呆,也不意味着丧失情感。我们已经知道,认知障碍只是认知上出现障碍,感情不会受到影响。依然会有喜怒哀乐,有食欲也有性欲,能分辨食物好吃还是难吃。即使已经认不出子女,但能感受到身边的人是否与自己亲近、对自己好不好。过得开心的时候会心情舒畅,反之则会难受。如果有个地方能让痴呆患者安享晚年也很好。要是我以后痴呆了,也想在那样的地方度过。日本的护理机构中,确实存在一小部分地方,让我相信这愿望有可能实现。
撰写《当事人主权》(上野千鹤子、中西正司合著,岩波新书,2003年)之际,我不止一次被问及:再怎么强调“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也得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如果得了认知障碍怎么办?
我心中已有主意,回答说:没错,我觉得自己很可能得老年痴呆,到时候就这么做。
我们国家有“成年监护”制度,但我不赞成这种制度。指定家庭成员成为监护人的策略太愚蠢。因为家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知该说幸或不幸,我作为单身人士,没有这种选择。因此可以指定某个我信任的朋友做我的成年监护人。不过,无论指定谁,只有一个监护人都不保险。当利害冲突出现,人很容易就会变。
既然如此,不如效仿医疗现场的团队护理,邀请各领域专家组成团队,针对委托人实施生活管理(life management),而非护理管理(care management)。这个团队里不仅有护理管理人[4],还有医生、理疗师、律师、税务师、咨询师,以及我的朋友,等等。召开护理会议(服务提供者会议)时,我这个委托人——无论有没有痴呆——当然也会出席。他们不能用“老太太”称呼我。如果问我“上野女士,这些选项还合您的心意吗”,即使听不懂,我也会大方地点头。因为我明白,他们热情善意的提议都是为了我。
这种团队护理的重点,就在于信息的共享与相互监督。让专家们彼此监视。我并不信奉“人性本恶”,只是觉得比起依赖一个人的善意,这种方式要好得多。
在我真的得痴呆以前,这样的体系能建成就好了。
* * *
[1]这里的“呆子”“痴迷”都读作“ぼけ”。
[2]漫才:类似中国的相声,分别负责“装傻”与“吐槽”的两人则类似相声里的逗哏与捧哏。
[3]一病消灾:比起一点病都没有的健康人士,有点小病的人会更注意保养身体,也更容易长寿。
[4]护理管理人:care manager,专门从事护理支援工作的人员。
梦想
法国文学研究者桑原武夫先生被授予文化勋章时,一位年轻的记者在庆功宴上采访他。那是1987年,桑原先生八十三岁的时候。
“祝贺老师。那么,您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桑原先生用温和又略带责备的语气回答了他,那句话我至今难以忘怀。
“你要知道,我是个老年人。这种问题,就不要拿来问八十多岁的老年人了。”
玉村丰男先生写过一本《明天不会比今天更好》(集英社新书,2009年),其中有篇文章甚合我意。
玉村先生在信州拥有自己的葡萄酒厂,还开发了自家公司的葡萄酒品牌。据他说,每当接受采访时有人问:“您的梦想实现了吧?”他都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位玉村先生讲了一件小事。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下村侑博士(当时八十一岁)接受采访时,记者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可以说说您的梦想吗?”下村博士一瞬间有些退缩,然后回答:“梦想……现在才来问我梦想……我可没有。”接着又说,“我都已经八十多岁了呀。”
看到这里,我立刻想起文章开头,桑原先生经历的小插曲。
玉村先生是这样说的:
“说起来,实现了一个梦想就要立刻拥有下一个梦想吗……为什么人非得要不断进取呢?如此逼迫人们马不停蹄地追逐下一个梦想、下一个目标,不正是拼命实现逐年增长的高度成长期[1]留下的恶果吗?”他还说自己没有梦想,“梦想之所以叫梦想,就是因为不知能否实现”。玉村先生已经六十有三,人生过去了大半。
此外,他还说:“大人们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非常清楚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所以就算没有梦想,也能充实地享受每一天。”
我和玉村先生一样,从来没有过梦想。
如果有人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那些坚信“只要朝着梦想努力,总有一天会实现”的人,都耀眼得让我无法直视。
有时会想,难道我没有“做梦的能力”吗?
我是个老于世故的现实主义者。
可以说这种性格适合研究社会学,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选择了社会学,我的职业才造就了我的性格。因为不闪不躲,直面赤裸裸的现实,就是社会学学者的工作。
一直以来,我的想法都比较悲观。很早就认识到社会的真面目,不会对他人有过多期待。每当发生什么事,我会立刻在脑中模拟各种可能性,推测最糟糕的结果。想着即使最后变成这样也没关系,但事态发展往往会比我推测的最坏情况好一些,也就比较容易解决。
因为我很务实,一眼就能明白一件事是否可行,如果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就会早早放弃。所以我很少失望,也没有太深的执念。
虽然三番两次陷入危机,但也能很快想出替代方案。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胜过最坏的情况,所以大都能平安无事地解决。只要不追求完美,就能获得适当的满足。我很庆幸自己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仅是对自己,我对别人也比较宽容。
见了抑郁症的人,我会猜想,他们是否对自己有过高的期待。因为理想的自己与现实的自己存在差距,差距越大,人就越是痛苦。想要不痛苦,就得降低对自己的期待值,道理虽然简单,但他们性格较真,大概很难做到吧。也许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期待不高,所以才不会患上抑郁症。
我这样的性格,确实是缺乏“做梦的能力”。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我都不会动摇,也很少吃惊。
转任到现在的学校之前,周围人都对我表示担心,有的人问:
“上野女士能胜任东京大学的工作吗……”
我泰然自若地回答:
“只要想成出国任教,去哪儿都没问题。”
好像确实不够讨喜。
外界对我的攻击都在我的预想范围之内,所以也有人说我承受能力强。若要问我是否因此沾沾自喜,那倒没有。
如果有人对我说:
“上野女士,你承受能力好强啊!”
我会回答:
“要知道,没人生下来就这样吧?”
我并不是出于喜欢才练就了强大的承受力。人的性格是由学习和经验塑造的。我只是在打击与被打击的环境里待久了才会如此。有人把学问的世界称为“竞技场”,常年置身于这个充满批判与反驳的竞技场里,性格确实会越来越差。
我并非毫不在意别人的恶意与讽刺,也没有乐观到对失败毫无感觉。很多人嘴上说的不是心里想的,这很正常,我也知道别人的话不可全信,表里如一的未必就是好人。比起无知的迟钝,故意的恶意更好应对。
自青春期以来,我在京都度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些想法或许也跟生活环境有关。某个晚上,我跟出身西阵的狂妄京都人、人类学学者梅棹忠夫先生一起聚餐。他不紧不慢地说:
“你呀,表里如一就不会被打倒。”
不过,正因我对他人、对世界没有过多期待,所以也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恩赐。每当有人对我表示出预料之外的善意,我都喜悦不已;每当世界慷慨地对我展示期待之外的美丽,我都充满感激。
世人似乎都以为我是个攻击性很强的“厌男”人士,其实恰恰相反。我对大多数男性都很宽容,也很少生气。当然,这是因为在我心里,男人不过如此,我对他们的期待值很低,所以反而会在不同的男性身上发现意想不到的美好品质。每到这时,我就会觉得世界比我想象的有趣,活在这种环境里也不那么难熬了。
拥有梦想的人似乎都倾向于拒绝现实;而相信只要活着就有无限可能的现实主义者,对现实的接纳程度更广也说不定。
* * *
[1]高度成长期:指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这是战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的时期。
年龄
经常听上了年纪的人说,“眼下是最好的时候”,但我并不是很同意。每个年龄段都有属于该年龄段的迷惘与懊悔,没人敢肯定地说自己从不后悔。
那些严格制订各阶段人生计划,在重要节点做出恰当选择的人,我无法理解。我不可能变成胜间(胜间和代[1]女士),也不羡慕像田中美津[2]女士那样,坚信一切人生选择都是“老天授意”的人。在我眼里,她们跟外星人没有两样。
从某个时期开始,我会有意识地结交比我年长十岁左右的人。虽然无法想象自己的将来,但通过他们,我多少能勾勒出十年后的自己。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则超出了我能想象的极限。四十岁之前,我问一位比我大十岁、我很尊敬的女性:“四十岁以后会比较轻松吗?”
她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说:
“这个嘛,完全不会变轻松哦。三十多岁有三十多岁的辛苦,四十多岁也有四十多岁的辛苦呀。”
我时常迷茫、后悔,丢过脸,也有想要抹掉的黑历史。好在我忘性大,才能一路走到现在。仔细想想,我也有过坐立难安的经历。
活着,就要学会忘记。
认知障碍的老年人罹患记忆障碍,或许也是一种上天的恩赐。
我眼下已经如此健忘,将来有很大可能性患上认知障碍。
但就算忘记,那些记忆和经验也无可置疑地塑造了现在的我。
虽然我不认为“眼下是最好的时候”,但也觉得眼下的自己至少胜过从前的自己。首先,我的耐性变好了,变得宽容了,对他人的想象力也比从前有深度了。我写过一句话:“所谓成熟,就是他人在自己心里的吃水线变高。”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有所成长。虽然没人过了花甲之年才觉得自己“有所成长”。
我曾经探访过安昙野的CHIHIRO美术馆。
虽然我本就喜欢CHIHIRO女士的作品,但访问美术馆以前,对她的生涯并不太了解。在名为“CHIHIRO的人生”的展示厅入口,有一篇介绍文章写道:
绘本作家岩崎知弘(CHIHIRO女士,1918—1974)在去世前两年的1972年(五十四岁)写过一篇文章。
“人们总说年轻的时候好,尤其是女人,十五六岁最为美丽。可我回顾自己的人生,完全不觉得少女时期有多好。”
CHIHIRO女士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说“那时的自己肤浅得好笑”,觉得“眼下的自己胜过从前”,并写道:
“我花了二十多年,日复一日地努力,才走到今天,能说出这句‘胜过从前’。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浑身冷汗,才终于渐渐地有所领悟。为什么要回到从前呢?”
充满迷惘、后悔的岁月与经验,塑造出如今的我。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要胜过从前。是啊,“为什么要回到从前呢”。
说年轻人柔软,这是谎言。再没有比年轻时更加固执、自以为是、受限于固有观念的时候了。随着年龄增长,那些僵硬、固执才会慢慢化解开来,变得柔软。既已至此,“为什么要回到从前呢”。
这么说来,我中年以后交到的朋友,大都经过岁月的淬炼,自带成熟的韵味。说起如果在更年轻的时候遇见,大家都相视一笑:“那我们一定不会变成朋友了。”
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一直维系到现在,也不只是因为我们认识得早。而是因为对方在每个人生阶段的选择、一路走来的人生轨迹令我尊敬、心生共鸣,我们的友情才得以延续。若非如此,我们也会像其他人一样,自然而然地疏远。我最不擅长应付那些自称是我“同学”的人。即使读过同一所学校,之后的人生也毫无交集,既然几十年都没见过面,事到如今还参加同学会做什么。
如果有人说:“年轻时的朋友是一辈子的朋友。要好好对待哦。”我会不自觉地想,这个人成年后就交不到朋友了啊,真可怜。还想告诉对方,朋友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想,就能交到的。
上了年纪以后交到的朋友,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象他们的过去。是什么样的经历和挫折造就了这个人的现在呢?这种想象非常有趣。有时候会觉得,“啊,原来你也受过这么多苦啊”,有时候也会想说,“你吃的苦还不够,别出现在我眼前了”。如果对方是男人,很容易就能看出他过去与异性的关系质量如何。
人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觉得自己“胜过从前”,是因为与人相处时更加游刃有余了。友情没有固定的形式,也不分男女。我想与那些历经沧桑、走到如今的同性和异性朋友分享余生,一起充实地变老。
* * *
[1]胜间和代(1968— ):日本经济评论家。高中时期就开始准备注册会计师的考试,十九岁第二次考试合格,成为旧制度下的最年轻合格者。先后就职于安达信会计事务所、麦肯锡咨询公司、摩根大通等企业,后成为独立评论家。2005年被《华尔街日报》评选为“世界最为人瞩目的50位女性”之一。此外,她还是一位职业麻将选手。
[2]田中美津(1943— ):日本哲学家,女性主义者,针灸师。20世纪7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个人
“上了年纪之后,比起有钱,不如有人脉”,我虽然写过这种话,但内心也有些忸怩。
我自己虽然难得地“有人脉”,不缺少能一起生活的伙伴,但心底也有个声音在反对:就算没有人脉又如何?如果我是这本书的读者……一定会大骂一句“多管闲事”。
人确实是群居动物。话虽如此,也不是全天二十四个小时都想跟别人待在一起。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我会松一口气。如果有谁旁若无人地播放吵闹的电视节目,我只会感到烦躁。我也不需要音乐无时无刻响在耳边。有人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我完全不懂那些离了电视不能活的人是什么心态。话说回来,我频繁与人会面基本只是出于工作性质,因为教师是种服务行业,事实上,我并不讨厌独处。
即使与人见面,我的话也不多。不管对方是谁,我总是会不知不觉地成为倾听者。因为我很少聊起自己,关系亲密的朋友还会因此而生气。不必说出口的话,我会选择不说,就算想找人倾吐和抱怨工作上的烦恼,但要解释来龙去脉太过麻烦,最终我还是会闭口不言。
想对丈夫倾诉的妻子、回家后累得不想听妻子抱怨的丈夫;或是在家从不谈工作的丈夫、对丈夫的工作一无所知的妻子。类似的夫妻状况时有耳闻,如果以此作比,我大概更接近丈夫的角色。
说了没用,或解释起来很费力的事情就不说。因为我明白,任何问题都只能靠自己去解决。所以到最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最多只会在尘埃落定后提一句:“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哦。”
女性朋友之间,往往会坦白恋爱、出轨之类的私密话题来拉近彼此的距离,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如临大敌,压力倍增。即使如此,我也很少深入谈论自己。虽然会倾听对方的话,自己却不会主动发起话题。
如此这般,听女性朋友们聊得多了,我惊讶地发现,人们其实并不关心他人。很少有人会在忙于谈论自己时,想起来问对方一句:“你呢?”每当有人对我说:“你不太爱说自己的事呢。”我就会在心里吐槽:“明明是你没问过吧?只要你问了,我就会回答。”如果对方是男人,就更别提了。男人在精力充沛的时候会自吹自擂,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则会抱怨不停。到头来,我还是充当了倾听者的角色。因为男人更习惯说,而不是听。极少数时候,我也会遇到善于倾听的男人,这种感觉就跟发现稀有动物似的。
我说自己不以独处为苦,就有人说,是因为独处之外的时间,你跟别人一起过得很充实。我说独处并不寂寞,对方又说,是因为你现在身体健康、工作稳定。不知道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会感到寂寞吗?
孩子离家、丈夫离世的女性感叹自己寂寞难耐,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呢?如果跟孩子住在一起,享受含饴弄孙的快乐,你的内心就不会寂寞了吗?从前跟丈夫一起度过的时光,真的一点也不寂寞吗?我该向她推荐多人同住的公共住宅吗?还是该劝她住进老人院里的多人大房间?
理疗师中的领军人物三好春树先生认为,不该让患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住单人间。因为他们的私人界限已然崩塌,需要与他人进行身心接触。这些老人里,有的即使住在机构里的单人间,也会跑去别人的房间睡觉。不过在我看来,这件事与患者生长的时代背景、身体感觉有关。过去的大家庭里,一家人都混住在同一个房间,下人们也是在一个大房间里并排打地铺睡觉。据说战前在东北长大的男性,寒冬里也会赤裸身体钻进被窝,跟自家兄弟挨着睡觉。在那时的人看来,人与人之间肌肤相贴,感受彼此的温暖与触感,大概是再正常不过了。我有个朋友家里虽然给孩子们安排了独立房间,但每晚睡觉的时候,全家人都会集中到同一个房间一起睡。我也曾受邀钻入其中,蚯蚓似的跟他们挤在一起,感受生物间彼此触碰的温度。但若是每天如此,还是会受不了吧。
如果有女性说自己一个人寂寞难耐,我想告诉她,你很快就会习惯啦!因为渴望他人气息也好,无惧独处也罢,只是生活习惯的不同。
另外还要加一句,如果真的那么寂寞,就去拥抱自然吧。感受风的吹拂、光线中的阴影、绿的鲜明、枯叶的幽静、树木的凛冽……春夏秋冬,无论哪个季节,自然都能抚慰人心。因为天空与流云从不停歇。它们包围在我的四周,从不吝惜给予。世界早在我出生以前就存在,即使我离开,也会继续运转,如果这都无法慰藉人心,还有什么可以呢?
不过,这样的回答或许并不能解决那位女性的问题吧……
做了这么久关于老年人的研究,我开始想着,要趁自己腿脚方便的时候做些对他人有益的事。就算没有护理福祉士或助手的资格证,我还可以成为日间护理机构的经营者。如今,全国各地都有优秀的实践者创立机构,为老人与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提供居所,类似一个“当地的茶室”。比如“集会”(よりあい)、“我的老家”(うちの実家)、“活力井边”(井戸端げんき)[1]等。或许我也可以加入其中……话是这么说,但我还是没有采取行动,因为觉得自己不适合扮演“胆大心细的老妈”或“旅馆女掌柜”的角色。我不想全天二十四个小时都生活在一堆人——家人也一样——之中,哪怕我以后需要被护理,也不想进入日间护理机构。
我应该会变成一个狷介的老女人,不愿任何人打扰我独处的静谧时光。
一位好心的护理管理人对我诉苦,说有个家里乱得像垃圾屋的老女人,“我去了好多次,她都不肯开门。”我一边听一边自我安慰:“就算她本人不需要,只要告诉她还有更多的选择,说不定她哪天就会意识到自己隐藏的需求。别着急,耐心去做吧。毕竟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实际上,我很理解那个老女人的心情,觉得对方“多管闲事”。
有位陪伴临终病人走过最后几个月的女性说:
“那人去世前几天对我说,很高兴最后的日子里有我陪在身边……我这样的人,也能给孤独的将死之人带去慰藉吗?”我的心情却倾向于临终者那边。没人能抚慰将死之人的孤独,对方那样说,只是出于善意。
一位女性说:“我妈说她虽然孤身一人,但有我陪着就不寂寞了。”我忍不住脱口而出:“你真以为有你陪着,就能治愈年迈母亲的孤独了吗?”……她哑口无言,我有点后悔。
所以,我的本意是,没有人脉也OK,不以孤独为苦的人,一个人生活也很好,只要能有技巧地度过一个人的时间,享受一个人的空间就行。不要把我那句“有人脉”,理解成一种强迫观点。
有人会说,你这些话只适用于身体健康的时候吧。一旦年迈体衰、生病或是变得怯懦,马上就会哭着请求朋友们:“快来看看我吧!”
——如果变成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 * *
[1]以上都是机构名称。